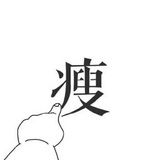梅贻琦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是梅贻琦振聋发聩的名言。
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大学。
他成功地奠定了清华的校格,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然而,身为一校之长、手握巨额庚子赔款,梅贻琦却一生清贫窘迫。
他穷到让妻子去卖糕摆摊,穷到独生子眼镜碎了也买不起新的,穷到妻子在美国以62岁高龄四处去打工,穷到自己住院时付不起医疗费,最后连丧葬费都是清华学子们合捐的……
但是,他的妻子韩咏华无怨无悔,始终默默地支持着丈夫的事业和理想。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梅贻琦和韩咏华细水流长的爱情故事,领略梅贻琦校长高风亮节的一生——

韩咏华
011919年,韩咏华和梅贻琦结婚。
好友急匆匆地跑来警告她:
“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
韩咏华笑笑:
“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就这样,韩咏华开始了和沉默寡言的梅贻琦43年的共同生活。
韩、梅二人虽然说不上青梅竹马,至少也称得上少友所钟——

梅贻琦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出生于天津一个盐务局职员的家庭。
他12岁那年,父亲不幸失业。
家庭的变故,令梅贻琦很早就担当起长子的责任,也造就了他沉默寡言的性格。
虽然家境一落千丈,但父亲咬定牙,坚持让孩子们读书。
1904年,15岁的梅贻琦进入严范孙创办的严氏家馆,认识了11岁的韩咏华。
韩家是天津的名门望族,韩咏华的曾祖父和祖父均是京官。
作为长女,她从小备受宠爱。
因此,她得以打扮成男孩子,进入严馆求学。
韩咏华常听母亲念叨,梅贻琦家连玉米面都只能吃得半饱,可他却是学堂里最用功、成绩最优异的学生。
这让她对这个大哥哥平添了几分敬佩。
1909年,梅贻琦以第6名的成绩考取庚子赔款首批留学生,入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专业。
期间,他节衣缩食,把本来就很少的生活费节省下来,五块、十块地寄给家中补贴日用。
而韩咏华16岁毕业后留在天津,成为严氏幼稚园最年轻的教师。
两人的命运看似失去了交集。

正中间为梅贻琦
02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1914年,梅贻琦留学归来,恰好与出国考察的恩师——严范孙同船回国。
韩咏华和很多严馆的学生,一同去大沽口码头迎接。
人群中,她一眼就认出了梅贻琦。
只见,梅贻琦一身中式长袍,一副圆形眼镜,面容清秀英俊,嘴角带着温和笑意。
就在那一瞬间,韩咏华想到了“温润如玉”这个词。
后来,在老师严范孙的撮合下,韩咏华与梅贻琦缔结婚约。
好友曾劝韩咏华好好斟酌,“梅贻琦太过沉默寡言”。
但那是从小就仰慕的大哥哥啊,韩咏华按捺住心里的欢喜,说:
“豁出去了。”

梅贻琦夫妇
1919年,26岁的韩咏华嫁给了30岁的梅贻琦。
婚后八年半的时间,两人生了4女1子。
韩咏华辞职当起了家庭主妇,“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孩子们带大。”
性格温和的梅贻琦,很喜欢孩子。
有时候,孩子太过调皮捣蛋,韩咏华气得打孩子几下,梅贻琦总是劝解妻子:
“你忘记自己是学幼儿教育的人了。”

梅贻琦全家福
一家七口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但梅贻琦每个月拿出薪水的三分之二赡养父母、供弟妹读书。
对此,韩咏华从不计较,也绝不干预:
“我作为他的妻子,一生没有财权。他给多少钱,我就过多少钱的日子。”
所以,家里一直比较节俭的生活。
而梅贻琦对生活要求很简单,从不为穿衣吃饭耗用精力,也不为这些事指责家人。

梅贻琦
031931年,历史的风云聚会将42岁的梅贻琦,推向了清华校长的位子。
梅贻琦廉洁奉公、以身作则,为学校节省每一分经费。
他一上任,就下令:
“废除一切校长特权和补贴!”
他主动放弃了过去校长享有的几项“特权”:
家里的佣工自己付工资;
电话费自己付;
不要学校每月无偿供应的两吨煤等……
他要求公私分清,私宅的一切自己掏钱。

梅贻琦身体力行一个“廉”字,赢到了大家的尊重。
与此同时,他的领导能力,得到了全校上下的拥护——
梅贻琦主张“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因此,在他掌校的17年里,清华大学延聘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执教。

左四为梅贻琦
以1936年为例,清华大学精英荟萃——
当时在职的教师就有潘光旦、冯友兰、朱自清、陈寅恪、闻一多、俞平伯、余冠英、吴宓、叶公超、金岳霖、贺麟、张岱年、吴晗、吴有训、叶企孙、赵中尧、任之恭、周培元、熊庆来……阵容不可以不说是豪华!
同时,梅贻琦在清华建立起“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
并且,他尽量少设办事机构,把必要的办事员减到最低限度。
“因事设人效率高,因人设事扯皮多。”
如是,在梅贻琦的领导下,清华大学渐渐声名鹊起,成为顶尖学府!
然而,当有人赞美梅贻琦治校有方,他总是谦逊地说:
“贻琦生长于斯,清华实犹吾庐。就是有一些成绩,也是各系主任领导有方。”
 04
04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清华南迁昆明,与北大、南开合并成为“西南联大”。
因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在重庆另有职务,梅贻琦成为西南联大实际上的执行校长。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梅贻琦表现出果断决绝。
他对师生发表了一番充满希望和信念的讲话:
“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敢向清华的同人校友说一句‘幸告无罪’。”
这位“船长”一言九鼎——西南联大在战火硝烟里历经8年,虽筚路蓝缕,但弦歌不辍。

梅贻琦
梅贻琦勉励联大师生正视严酷现实,处变不惊。
在跑警报的时候,他虽然也跟着学生们往后山去,但是他神态稳重,毫不慌张。
途中,他还帮助学生疏散,嘱咐大家不要拥挤。
看着梅校长安详的神态,学生们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你看老校长都不慌不忙,我们还慌什么?”

梅贻琦
到了1941年,物价飞涨,教授们的月薪只够半个月吃饭。
面对食不果腹的老师、饥肠辘辘的学生,梅贻琦总是把物质上的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
他把个人使用的小汽车让给联大公用,自己每天步行外出公务、办事。
一天,中山大学教授罗香林因公事来到昆明,顺道拜访梅贻琦。
他发现梅贻琦打包了一包冬天的衣服。
罗香林便问:
“这是做什么?”
梅贻琦回答说:
“联大最近的教职工薪水还没发,只好先自典当些物品以周转。”
罗香林听后非常感慨,多年后还回忆说:
“梅先生主持这么庞大的学校,还要以典当接济生活,这一方面固然显示时局的艰难,另一方面更显示梅先生的高风亮节。”
之后,身无长物的梅贻琦,终年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袍。
1941年7月,梅贻琦在重庆参加完会议,他放弃坐飞机而选择乘邮政汽车返回昆明,只为了给学校节省200块钱。
梅贻琦的恪尽职守与刚柔并济,身体力行一个“廉”字,宁可自己劳顿、也要为公家节约的精神,得到了师生们由衷的认可与敬佩!

韩咏华与子女
05为了多节省一分钱给学校,梅贻琦对自己和家人俭省到了几乎苛刻的地步。
儿子梅祖彦的近视眼镜镜片摔碎了,却没有钱再为他配一副新的。
一家人每天的基本食物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
虽然伙食日用拮据,但一家人知足常乐。
这不,韩咏华后来回忆说:
“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

定胜糕
为了补贴家用,韩咏华自制了一种叫做“定胜糕”的糕点。
糕是粉红色的,形状像银锭。
取名定胜糕,是表达对抗战胜利的希望和信念。
她每天挎着篮子,将定胜糕送去“冠生园”寄卖,来回要走1个半小时。
她舍不得穿袜子,总是光脚穿一双破旧的皮鞋。
有一天,她让石子刮破了脚,脚底生脓溃烂起来!
梅贻琦看见妻子这么狼狈,这才知道自己家已经吃不上饭了!

梅贻琦夫妇
又有一回,韩咏华参加女青年会的活动,大家要轮流备饭。
轮到韩咏华的时候,她拿不出钱。
于是,韩咏华跑去摆地摊。
她将孩子们长大后穿不上的衣服、自己的衣服摆上卖。
一个早上卖了10元钱,总算勉强把这顿饭备上了。
即使自己家里生活这么清苦,梅贻琦也绝不利用职权、不准家属去占任何一点好处。
教育部曾发给联大一笔学生补助金,梅家有4个孩子在联大读书,按规定有资格领到补助金,他却从不让自家孩子去领。
1943年,梅贻琦的一儿一女,先后从联大应征入伍。
女儿梅祖彤加入国际救护组织;
儿子梅祖彦加入空军当了一名普通翻译员。
梅贻琦尊重并支持子女的选择,并为他们感到自豪。

梅贻琦
06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梅贻琦回到北平,花了3年时间筹备清华复校的工作。
然而,1948年底,梅贻琦离开大陆,离开了他所挚爱的清华园。
人们都非常震惊,不理解为什么!
事实上,梅贻琦有他自己的考虑。
据清华教务长吴泽霖回忆——
梅贻琦临走的时候,他问道:
“怎么样?听说你是不是要走?”
梅贻琦回答说:
“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
当时,清华大学基金都是来于庚子赔款,这笔钱是由美国的“华美协进社”来保管。
如果负责与“华美协进会”接洽的梅贻琦不走,这笔基金就可能会流失。
因此,为了保护好清华的基金,他选择了离开清华园。

梅贻琦
1949年,梅贻琦飞抵美国纽约。
1950年,梅贻琦进入“华美协进社”,掌控了清华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
他专门辟出一间办公室负责保管清华基金,自己为自己支付薪水。
其自定生活费甚低,几乎无法维持生活。
1955年,梅贻琦离美赴台。
据说,如果他不去台湾,专项清华退还庚款就会被美国人扣下了。
不久,他用清华的基金,在新竹创办了“清华原子能科学研究所”。
不过,梅贻琦一直不愿意把“研究所”升格为“大学”。
他说:
“真正的清华仍应在北平清华园!”
并且,他谢绝为官,只是为教育事业奔走。
“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
可是人事推排,他最终担任了教育部长,屡次推辞不准,便认真地干了起来。
与此同时,一些政客常常找上门来把梅贻琦团团围住,态度刁蛮地当面提出要求,想要从清华基金中捞一把油水。
每次,梅贻琦都要捺着性子历述基金保存与使用计划,直折腾得口干舌燥,血压呼呼上蹿,几欲吐血晕倒方休。
每天斗智斗勇、繁巨的工作量,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

病床上的梅贻琦
071960年5月,梅贻琦因腰痛、发热与肺炎并发症,住进了医院。
紧接着,他被查出骨癌。
韩咏华得到消息,立刻收拾行装,抵达台北陪护丈夫。
在这之前,她留在纽约,随长女梅祖彬和三女梅祖衫居住。
她的二女儿梅祖彤定居英国;
小女儿梅祖芬留在大陆,供职于大连铁道学院;
儿子梅祖彦于1954年通过亲友的帮助,也从美国回到祖国大陆,并被分配到清华大学任助教。
在美国的两个女儿并不富裕,梅贻琦又薪水微薄,且领的是台币,无法维持韩咏华在纽约的生活开销。
62岁的韩咏华为了不增加丈夫和女儿们的负担,便跑出去打工——
她在衣帽工厂里做过工,在首饰商店卖过货,还在医院里做过代班,最后到一个盲童学校照料盲童。
跟梅贻琦团聚后,韩咏华每天都去病房陪护。
这样,她陪伴丈夫走完了人生最后的两年时光。
梅贻琦治疗费和住院费都很高,因为家无积蓄,清华学子为其募捐68万新台币。
梅贻琦看到募捐记录后,久久无言而热泪盈眶。
当时,胡适跟梅贻琦是病友,两人住对面。
胡适让韩咏华劝梅贻琦留个遗嘱,以为将来后继者遵循办理。
但是梅贻琦不吭声。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享年73岁。
临终之前,他的病床下一直放着一个加了锁的手提包。
没有人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珍贵东西,也不方便问。
梅贻琦去世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由专门人员启封。
当包打开时,所有的人目瞪口呆——
里面装的全是清华基金账目,上面一笔笔钱款记得清清楚楚!
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此时,妻子韩咏华顿悟:
“他没有个人财产,所以也无须写什么遗嘱。”
梅贻琦去世后,“清华原子能科学研究所”始改称“台湾新竹清华大学”。
梅贻琦一直服务于清华(大陆的清华大学和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可谓鞠躬尽瘁,因此被人们称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他这一生两袖清风、高风亮节,被誉为时代圣贤和社会斯文的象征。
正如北大、西南联大教授毛子水所说:
“我尝独居深念,觉得要使我们在文化上能够和世界文明的民族并驾齐驱,唯一的方法只有努力于教育。所谓努力,并不是虚张声势的宣传,亦不是自欺欺人的表面工作,乃是遵循正直的大道切切实实,一丝不苟地做去。能够这样做的教育家,半世纪来,我们国家里为数极少;而月涵先生则是这个极少数人中的一个。”
 08
081977年,韩咏华回到大陆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
宴请她时,邓颖超还特意请了天津狗不理的名厨做了一桌天津菜。
政府给予她优厚待遇,安排她为全国政协第四届特邀委员。
对此,韩咏华非常感激:
“几年来住在英、美的几个女儿女婿们,也曾先后回来探望,和我团聚。我的晚年生活可以说是很美满的。只因年纪过高,未能对国家有所贡献,总是深觉遗憾。”
在北京安度晚年的韩咏华,每当暮色四合的时候,就会静静凝望清华园的方向。
她想起梅贻琦,想起他们第一次相遇的严馆,想起在大沽口码头的重逢,想起他们在西南联大清苦却知足的那些日子……
她很欣慰,她回到了清华,为丈夫圆了一生中最后的梦。
1993年8月26日,韩咏华在北京去世,享年100岁。
参考书籍:
【1】《家人眼中的梅贻琦》——韩咏华 梅贻宝 梅祖彦等
【2】《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黄延复 钟秀斌
【3】《岳南趣讲大师》——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