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清代学者赵翼得出如此结论,遥想权臣曹操,奋战三十多年,才为儿子曹丕立下称帝建国的雄厚资本,保证曹丕废汉建魏;遥想权臣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苦心经营三十多年,才为子孙司马炎积攒到足够改朝换代的深厚实力,确保司马炎废魏建晋。
为什么前人称帝建国如此艰难耗时,而杨坚却能如此迅捷高效呢?代周建隋,杨坚称帝为何如此简单?北周皇位的丧失又与什么有关?

其实北周皇室肯定是不可能愿意把皇位禅让给杨坚的,历代皆是如此,但如果如果是北周权要的话,也可以说“北周”把皇位通过禅让的形式给了杨坚。
也就是说,北周皇位的丧失,不仅仅是杨坚巧取豪夺所致,更是北周皇权本身“威德”不足的重大隐患所致,这种隐患使得绝大多数的北周中央官僚群体或助力、或默认杨坚从掌权到禅代,最终完成代周建隋的进程。
换言之,北周皇室是在宗室勋贵挣扎无望、中枢官僚助力或默认杨坚掌权的前提下,被迫禅代的,这是宇文家族不得“臣心”、统治基础狭窄化的恶果,而这一恶果的形成纵贯整个西魏北周历史。
宇文周王朝的奠定者宇文泰本人因贺拔岳之死而意外成为武川豪帅之领袖,在掌握贺拔岳余部主导权之始,他的权力并未来自军事征服,而是来自诸将权宜,这就使得宇文泰日后在以军事为主导的西魏政权中,必须首先给予贺拔岳部将以极大的政治特权。
而对这部分勋贵的拉拢、排异乃至斗争,则构成了整个西魏时期的内部矛盾主线,这一条线甚至最终影响了日后的北周兴亡,也就是说,贺拔岳余部北镇勋贵始终可以利用当年的军头关系来借机搞事情,这就为北周埋下了一个潜在而可大可小的政治隐患。

西魏政权可以说混杂着武川勋贵、关西土豪、投奔魏帝之魏室宗亲、各方胡汉士人各方势力,为对抗强大的东魏政权,宇文泰一方面大规模援引关中土豪进入自身军政体系(初期为大行台,后期为中外府),建立府兵将关中乡兵国家化以补充衰落后的武川镇兵,另一方面不得不在行政和中央部门给予魏室一定的权限,以笼络各方投奔而来的胡汉势力,由此逐步形成了华州霸府-长安朝廷的二元体制。
可以说宇文周王朝的篡代建立,存在“威德”不足的潜在危机。虽然宇文泰本身的“威德”在西魏大统十六年以后的诸次军政成就中大幅度提升,但宇文泰本身的“威德”并不等于宇文氏家族的“威德”。
宇文泰唯有在自己生前就完成称帝篡代,方能至少取得来自其个人功勋威望的“势”(形势、威势)的压力,进而转化成其家族的皇室威望,进而实现彻底的“化家为国”。
但宇文泰本人的仓促病逝无疑打断了其计划,这既造成了宇文泰终生未能称帝的事实,也造成了宇文周皇室成立伊始的威德弱势。

宇文泰死后,辅政的宇文护与即位的宇文泰诸子在资历上难以压服前辈诸公。而宇文觉之所以能称天王,全赖堂兄宇文护的支持;宇文护之所以能够稳定局面,全赖勋贵于谨的鼎力支持;而宇文觉之称天王,本身就是为了弥补自己实际威德的不足,而从名分上借“机”找补。
这就使得宇文周的立国仍旧无法摆脱权臣庇护、勋贵支持、名实二元权力分峙的局面:权臣宇文护为了维持宇文家族的地位,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异己势力,这是其代表宇文家族与亲魏帝人士、武川镇等夷勋贵所产生的政治矛盾;但宇文护所加强的中央集权,又不可避免地集中到自己身上,这就又与北周天王产生了政治矛盾,并且使得北周官僚体系中划分为亲周王派与亲晋公派。
所以,北周晋公宇文护统治时期,无论是赵贵、独孤信事件还是三次废立,都将严重冲击宇文周的统治基础:夹杂了武川镇将、关陇豪族、河南河东豪族的不同事件中处于不同立场的军头与官僚群体。
宇文护只能以较为血腥的手段维系宇文氏的统治,赵贵等前代勋贵也因政治斗争被杀,宇文护与宇文泰类似的,借助中外和天官两府掌握大权,而为加强统治,宇文护开始大规模提拔宗室诸王或外戚姻亲充任军事职位,实现对军权的掌握。

然而,宇文护对外武功是毫无重大突破可言的。尤其是在第二次邙山之战中,三路出军而自己坐镇相对后方的弘农,这就不仅仅是武功不足了,更是胆略不足。武功与胆略的不足,对于以军事为核心要务的十六国北朝主君而言,是致命缺陷,使得宇文护的勇武形象远逊于同时期的高齐主君。
对外武略不足,对内则又不得不推行两面不讨好的专权,宇文周皇室虽然保持了主君名分,却未能在能够服人的“威德”层面,有任何进步;反而,宇文周政权为了在前述三点所致缺陷下保持宇文氏家族的地位,便不得不通过政治斗争的手段,排除异己,这种举动只能暂时保持宇文周皇室的名分,却长远地削弱了宇文周的统治基础。
北周武帝宇文邕上位后,通过强化御正、内史、纳言等近侍官员的权力成功以自身亲信掌握中央行政权力,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说,武帝时期可能是最为平和的,除了卫王叛乱,武帝基本没有对勋贵团体有大规模的打压,可以说北周已经形成了中央对各方力量的控制。
但是灭齐所致武功赫赫的代价是巨大的,虽然北周各项制度为隋唐帝国提供了蓝本,但制度本身也需要一个稳定的统治基础(人望、民心)方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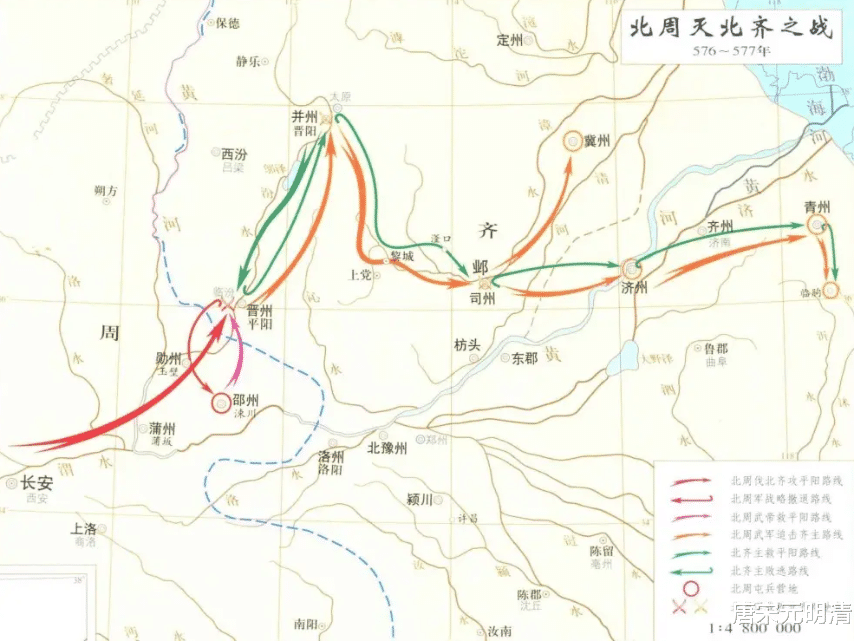
宇文邕为了弥补宇文泰去世以来宇文家族的武功不足以压服勋贵的尴尬窘状,便不得不顾勋贵反对、发动举国之力来灭齐(例:韦孝宽等大多数权要对宇文邕伐齐的反对,以及伐齐主力皆是宇文邕的同辈亲信)。
再加上,宇文邕为了耕战强国的政策而灭佛充实耕地、人口与赋税,对于南北朝时期普遍信仰佛教的中下层民心乃至上层信众而言,是相当不得人心的。
也就是说,宇文邕在军政方面为后人称道的精神抖擞、整文经武与雄才大略,背后的代价是统治基础的进一步丧失。
如果周武帝之后的北周皇帝,能够是一个昭帝式的怀柔仁德之君,北周尚可在吞灭北齐后争取到一点扩大统治基础的“消化”时间。

可惜,北周宣帝本人在威望上更无法与前代相比,不仅打压了宇文神举、宇文孝伯、王谊等一干有军政才能的周武帝亲信托孤班底乃至于宗室长老宇文宪,任用的还是一些寒微无用的恩倖之徒,进一步加强了集权程度,这就不可能不令逐渐掌握北周主导权且吸收武川镇勋贵的关陇豪族,以及新近归降的河北豪族寒心了,这就彻底恶化了宇文周的统治基础,威德扫地。
而杨坚作为外戚和四辅官中唯一一位长期在朝的重臣以及与宣帝亲信的旧识关系得以在宣帝暴毙后成功掌握了中央政权。
最终,宇文赟的短命暴毙,使得本来就没有什么威望的宇文皇族失去了最后一个强势领袖,换言之,宇文皇族在宇文阐时期,不仅“威德”已经全面恶化,而且那么依赖于主君名分与魄力的“势”也荡然无存,遑论忠孝之“义”(篡魏与宗室内耗),独独剩下了一个空无根基的“名”。权柄自然而然地会被所谓有“德”(人望民心)者,轻而易举地拿到手。

杨坚代周,固然可以从制度史层面,分析府兵制成熟运转之后,杨坚通过对主要集结于关陇的府军的调动便可逐个瓦解三总管之乱,进而稳固地掌握局势。
但,传统史观视角下对于“威德”乃至“出身”的强调,或者说,对于“人望”因素的强调,配合制度史视角,或许更能剖析出历史的原貌。
也就是说,杨坚之所以能代周,是制度上府兵制成熟以供中央权柄执掌者驱动,人望上杨坚通过出身与机缘成为关陇豪族乃至佛教徒的代言人,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
也是杨坚方面的两点原因,与宇文周皇族逐步丧失人望综合所致,这两方面的原因背后的一得一失,推动力既不在宇文周、也不再杨坚,而在于构成北周中坚的关陇豪族之抉择。
其实,杨坚本人上台后也是大规模引入亲属、故旧,实际上继承了武帝、宣帝以来的惯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