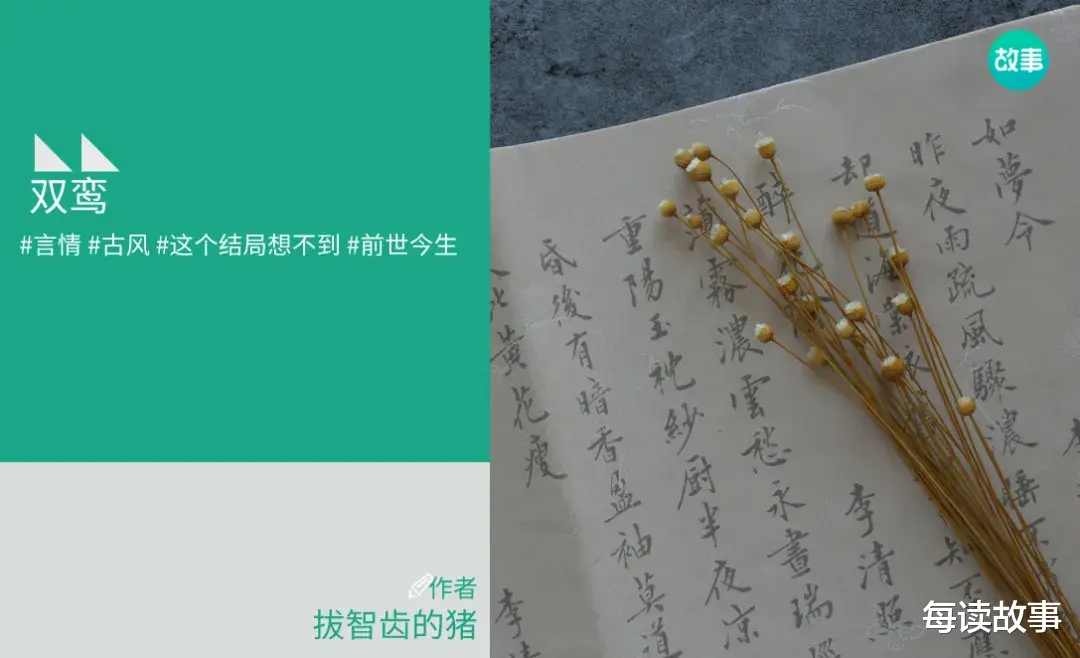
太子于民间微服私访,带回一妙龄少女,竟是相府六年前走失的嫡小姐:姜云柔。
二人情意深重。
一时间,往日被我吊打的贵女们都在等着看我这个相府养女的笑话。
可她们不知道。
姜云柔,是我让太子去寻的。

太子回京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绣大婚之日的盖头。
大红丝线勾勒出交颈缠卧的鸳鸯,将羞怯与爱意尽数藏于其中。
可一个月后,这块倾尽我无数心血的盖头,却覆住了另一人的面容。
我静坐于窗前,细细听着屋外的喜乐。
真热闹啊。
今日是个难得的好日子,大吉,宜嫁娶。
这本该是我与太子的大婚之日。
只是,如今踏入喜轿的,受着宾客们一声叠一声恭贺的,是姜云柔,不是我。
我不由想起一月前初见她的模样。
细眉凤眼凝脂,娇怯又柔弱。
其实细看,她与父亲、母亲长得并不太像。
可当她掏出那块自姜云柔出生之日起便贴身佩戴的玉佩,当她翻转手腕露出那处仿若梅花的胎记时,在场再无一人置喙她的身份。
母亲凄厉地哭叫一声,跌跌撞撞朝她跑去,将人搂入怀中不住道:“我儿,我儿,你受苦了……”
连一向不形于色的父亲也罕见地红了眼,摩挲着手中的玉佩喃喃:“就是这块玉佩,这里有个细小的豁口,是你幼时调皮,一不小心磕到的,你是我们的柔儿。”
至亲重逢,多么感人的场面。
在场之人无不垂泪。
除了我。
只因我是在姜云柔走失后,被姜夫人捡回来的,一个替代品。
我不仅占了她姜家大小姐的位置,还占了她顶好的,与太子殿下的姻缘。
如今正主回归,我的处境自然变得尴尬起来。
我朝不远处的太子看去,他眼里噙了温柔的笑意,目光浅浅落在布衣荆钗的少女身上,那少女腮存粉泪,我见犹怜。
他二人隔空对视。
我心里潜藏的不安呼之欲出。
那落泪的美人终于发现我的存在,小鹿般的眼里满是迷惘与无措。
“她是……”
父亲沉默,母亲不语,谁也不愿开口道出我的身份。
太子清泠泠的嗓音响起:“柔儿,她是姜云娇,是这些年里,相府的养女。”
姜云柔尚且来不及反应,他又贴心地添上一句:“不过,如今你既回来了,一切自然该回到正轨,你大可不必忧心。”
自始至终,他不曾分我半丝眼风,轻飘飘便决定了我的命运。
父亲听了他的话,猛一皱眉,“殿下所谓的‘回到正轨’是指?”
“姜相,一个月后,孤要迎的新娘,该是柔儿。”
“不可!”
父亲双目圆睁,疾言呼出这一句,方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失态,他整了整脸色,斟酌道:“柔儿长于乡间,行为礼仪皆不曾受过教导,何堪入主东宫?”
姜云柔的脸色白了一分。
太子却不以为然,“无碍,嫁去东宫后,自有嬷嬷教导。”
“殿下,老臣这般年岁,将将寻回女儿,尚不及享天伦,便要送其出嫁,老臣实在不舍。”他悄悄同姜云柔使了使眼色,继续道:“想必柔儿也愿在家多伴父母几年。”
可惜,血亲到底隔不过岁月的搓磨。
他的暗示我看懂了,姜云柔却没看懂。
姜云柔绞了绞衣摆,脸覆红霜,半晌来了句:“我愿意……嫁给殿下。”
无视父亲难看至极的神情,太子一锤定音:“孤随后便进宫,同父皇言明此事,姜相便等着接旨吧。”
于是今日,姜云柔着凤冠霞帔,享十里红妆,嫁予了我的心上人。

大户人家的下人们最会审时度势。
昨日你受宠,便拿你做攀云梯,捧你护你。
今日你跌势,就当你是脚下泥,厌你避你。
不过一个月,我这院子里,竟连个能使唤的仆役都寻不着了。
母亲倒是来过一次,欲言又止,末了也只留下一句“娇娇儿,娘定会为你再寻一门好亲事”,之后便匆匆离去。
真真是难为她了,姜云柔婚期在即,她竟还能记得我这号人物。
我突然想起她捡到我时,带我回府的那一日,她紧握着我的手,满目温柔。
那时她怎么说来着?
“以后这便是你的家了,你就是我的娇娇儿。”
十岁,我入姜府。
十二岁,过祠堂,进族谱。
十五岁及笄,姜云柔遍寻无果,姜家与皇室的婚约便落到了我身上。
十六岁,朝夕之间,零落成泥。
我捏紧拳,指甲嵌入掌心,痛意翻涌,连带着心中的恨意与不甘也沸腾叫嚣。
如今之势,出路须得我自己来谋。
……
三日后,回门宴。
我在姜府的后花园堵到了太子。
这院中有棵百年银杏树,是父亲花了大心思从别处运来的,太子极爱,每次来必定欣赏一番。
此次亦然。
他见着我,似是大吃一惊。
毕竟从前,我为了哄得父母高兴,诗书礼节,事事拔尖,堪为京都贵女典范,与如今这行容素朴的模样大相径庭。
“姜小姐?”
“殿下素来唤我娇娇儿。”
“今时不同往日。”
“有何不同?”
“处处皆是不同。孤中意你,是因你姜家女的身份,可孤中意柔儿,无关其他,只因她是她。”
银杏树下的公子有无双容貌,偏偏所言句句伤人肺腑。
无力感似一双无情铁手,压向我的脊背,叫嚣着压垮它,折断它。
我几番提气,方能忍住发抖的嗓音:“殿下此举,难保父亲不会多想。”
“孤问心无愧。”
他望向我的目光一派坦荡,“回京前,孤早与柔儿许下海誓山盟,若非前不久,她无意间露出那块儿玉来,恐怕孤至今都不知晓她的身份。”
“或许,这便是命中注定。”
好!
好一个命中注定!
我心中酸涩翻涌,一如咬下颗未熟的梅子,又好似饮了壶陈酿老酒,辣得我眼泪奔呛而出。
太子眼里闪过一丝厌恶,负手踱开几步,“姜小姐一向知礼,此番纠缠倒叫人大跌眼镜,你不妨直说,寻孤到底所为何事?”
我仅剩的自尊被他击了个粉碎,那句“你能否带我离开姜府”,无论如何也问不出口了。
于是绷紧了背一言不发。
太子终于耐心耗尽,冷冷落下一语:“过往种种,还请姜小姐忘了吧。孤同柔儿已结同心,望你克己复礼,休要做出令姜家蒙羞、带毁柔儿名誉之事。”
从前与三两好友闺房密语时,她们总说太子气势威严,不假辞色,见之则两股战战。
我不以为然。
只因他对我,始终温柔,始终言笑晏晏。
如今,我终于得见他这天家人冷酷的一面。
可我盯着他愈行愈远的背影时,还是很想问一问:“何谓过往种种?”
是我刚进姜府不久,在宴会上被人欺负,你替我解围后说的那句“别怕,我保护你。”
还是及笄时你送我的那只,亲手雕琢的翠玉碧簪。
抑或是,你微服离京前,给我留的那一纸信笺:“等我回来娶你!”
这些,我都该忘了吗?
心头遽痛,连气力也被剥夺,我失魂落魄地转身,却发现,父亲与姜云柔正站在不远处,不知看了多久,听了几时。

我在这庄子已住了三月有余。
那一日姜府花园,姜云柔同父亲说:“女儿不愿再看见她了。”
于是一驾马车,一个包裹,我便被远远儿的打发了。
庄子里自有一套规矩,管事嬷嬷堆着笑送走了押解之人,再转向我时,那张刻薄的脸上就只余下不怀好意。
此后我过的日子,便是连她豢养的那只狗都比不上。
也是,人性本恶。
曾经位高之人如今却被自己牢牢踩在脚下,除了苟延残喘别无他法,这般滋味,只是想想都觉得舒爽。
是夜。
我挑完最后一桶水,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屋内,甫一坐下,心头便传来异样。
“谁?”
床尾阴暗处缓缓走出一人,白玉发冠,一双似笑非笑狐狸眼,手拿一把折扇,正不紧不慢地摇着。
我眯了眯眼,不确定道:“三殿下?”
“姜小姐果然敏锐,你如何察觉到我在此?”
我瞥了眼他腰间,言简意赅:“香。”
这位三皇子殿下行事向来招摇,就好比此刻,他在这月黑风高夜,跑到这穷僻之地寻我,必然无甚好事。
可他偏偏着一身雪白袍服,腰间配的香囊里还散出若有似无的龙脑香。
他抚了抚掌,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有趣,你果真是个妙人。”
我不欲与他绕圈子,自顾自倒了杯茶,抄起桌上的绿豆糕狼吞虎咽起来。
他施施然落座,“你不好奇我来找你,所为何事?”
我嘴上不答,心里却暗自揣度。
三皇子与太子素来不和,皇后虽为陛下发妻,但娘家势弱,以至于这些年太子举步维艰。
而三皇子之母陈贵妃宠冠后宫,陈氏亦是军功累累。
自几年前陛下醉心求道,不问朝事后,太子与三皇子的争斗便逐渐浮于明面,及至今日,已成水火之势。
若是放在从前,我是决计不会同他说一句话的。
只是,太子有句话说得对:“今时不同往日。”
他见我许久未吱声,脸上那副得意洋洋等着别人追问的表情终于维持不住,殷勤地往我这儿凑近,“喂,跟你说话呢。”
我将那盘绿豆糕朝身前拖了拖,“口水别溅到。”
他一滞,随后皱着眉捏起一块放进嘴里,须臾又吐了出来,嫌恶道:“都馊了你还吃?”
我木然,“要饭之人,何嫌饭馊。”
他牛饮半壶茶,压下口中的酸味,方才开口:“姜家弃你,皇兄负你,你就甘愿任他们欺凌,在这鬼地方自生自灭?”
“殿下何意?”
“你我不妨联手,各取所需。”
我不紧不慢看了他一眼,笑道:“三殿下如今的日子,恐怕也并不好过吧。”
他收敛起笑意,一声不吭。
我兀自分析:“过去,姜家虽与东宫定下了婚约,可在你与太子之间,父亲的态度一直暧昧不清。
“因我不过是个养女,我入东宫,纵使太子在这权力之争中身败,父亲只需将我当作弃子,丢了便是。
“可姜云柔回来了,一切自然就不一样了。
“那是他放在心尖上的独女,姜云柔固执地嫁给太子,便是将姜家与东宫牢牢绑在了一处,这下,父亲便是再不愿意,也不得不站到太子那边。
“我想这几个月,他应该给你使了不少绊子吧?”
三皇子又挂上那副似笑非笑的面具,动作轻佻,目光却犀利。
两片薄唇一开一合:“我早说过,皇兄负了你,是他有眼无珠。”
他一面说着,一面伸手摸向我发顶,一路顺着发丝向下,指尖微凉,引得肌肤一阵寒栗。
眼见他那只手就要滑到胸口,我终于忍无可忍,一把拍开,却被他顺势抓住,用力拖至身前,那张脸顿时无限放大。
“早看你平日那副假正经的样子不顺眼了,只有皇兄才会喜欢这么无趣的女人。”
“哦?那三殿下喜欢什么样的?”
“你现如今这样,便很得我心意。”
“哼,巧言。我帮你,有何好处?”
“你想要什么好处?”
“太子妃之位。”
他轻轻挑眉。
我贴近一步,与他脚尖对脚尖,远看好似交颈相拥的爱人。
“那本该就是我的!”
与我对视半晌,他嘴角蓦地扬起一抹邪笑,“助我登上这太子之位,我必迎子归!”
击掌为誓后,言归正传。
“说吧,到底要我帮你做什么事?”
他从怀里抽出一封书信递向我,“我要你将这封书信放入姜相的书房。”
“我连姜府都回不去,更遑论进他的书房?”
“下月初姜相大寿,父皇定会降下赏赐,届时我也会为你求一份,姜相必会召你回府,你只需寻得机会,将它放进去即可。”
“这里面,是什么?”
“可以要他命的东西。”
这话让我生了些犹豫,他嗤笑一声,“怎么,怕了?”
“他毕竟对我有养育之恩。”
“不过是利用罢了,姜夫人思念成疾,若非是你,她早就抑郁而终了。”
他循循善诱:“没了姜相相助,太子便不成气候,那姜云柔以后也再不能于你面前耀武扬威了,你想要的太子妃之位……”
我抿了抿唇,不发一言。
“此处人多眼杂,我绝不会踏足第二次,今日是你仅有的机会,你可要想好了。”
我心里如走马灯一般飘过许多场景,父亲的漠然,母亲的无情,太子对我的弃如敝屣,情绪堆叠到最后,只化作三个字:“我帮你。”
……
姜府的寿宴办得极为盛大,可结束后不久,朝中便因一事炸开了锅。
都察院接到密报,称姜相与漠北有所勾结,同日又在姜府书房搜到了其与漠北往来的书信。
姜相当即被下诏狱。
而未待提审,第二日他便被狱卒发现自缢于狱中,只留下四字遗言:罪臣有愧。

“罪人姜云娇,以上所言,你可认?”
我匍匐于金銮大殿之上,以头抢地,只落下一字:“认!”
前面这番自白,自我自首之日起,便已说了不下百次。
此事牵扯颇广。
害的是一朝之相,门生众多。
告的是当朝皇子,背后是虎视眈眈的陈家。
多方夹击下,都察院不敢怠慢,亦不敢轻下结论。
左右为难之际,突然收到殿审的消息,虽说这法子旷古未闻,却着实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于是便有了今日这番局面。
三皇子面上凛然,一派浩荡,对我的指控似是全不在意。听完眉头也不皱,只道:“通篇荒谬,儿臣从未行过此事!”
高座之上不时传来压抑的咳声,我跪伏在地看不真切陛下神情,隔了许久才听到他低沉的嗓音:“既如此,姜相寿辰之际,你为何提醒朕,赏赐别忘了姜家养女一份?”
三皇子做出一副痛心模样:“父皇容禀,儿臣此前颇为中意此女,只是碍于皇兄与其关系,不曾言明。彼时听闻她处境艰难,儿臣便动了怜花惜玉之心,想着拉她一把。谁曾想此女蛇蝎心肠,竟因私怨犯下滔天大罪,儿臣实在是看错她了。”
我心中冷笑不止。
好好好!他怕是早想好了措辞,来拉我做这替死鬼。
三皇子仍在辩解:“更何况,此女所言之日,儿臣压根未出皇城。白日去了马场驯马,夜时在府里宴了几位好友,皆有人证,根本无法抽身去往那姜府乡庄。”
陈氏一派的朝臣皆出声应和。
“三殿下!”我轻轻朝他投去一眼,“你说了这么多,我只问你一句,那日后半夜,你是否腹痛难忍,请了医正?”
他脸上终于现出一丝裂痕。
我俯首拜倒,高呼:“陛下只需派人去医正所,查看一下当日记录,便可一清二楚。”
“父皇,儿臣那日确实腹痛,不过是因为吃坏了肚子,此女不知从何处知晓,妄图……”
“你撒谎!那日你在我那处饮的凉茶,食的豆糕,皆是性寒之物,再配上你常年戴的龙脑香,这才是你腹痛之源。”
“你!!!”
陈靖上前一步,赶在三皇子口不择言前拦住了他。
他是陈贵妃亲弟,亦是陈氏当前的掌事人。
“陛下,断不能轻信此女的随意攀咬,医正所的记录,有心之人一查便知。依臣之见,定是有人将此消息递与她,作为污蔑三殿下的借口。”
“没错,父皇,儿臣与姜相无怨无仇,有何理由要去害他?”
“你或许没有,可陈氏有!”清音朗朗,太子终于露面。
他身后还跟了一跛脚老汉,面容黢黑,眉尾至嘴角处一道长疤。
朝中众人神色各异。
太子不疾不徐,朝皇帝行了一礼:“父皇,三弟之事暂可搁下,儿臣这里还有一桩陈年旧案,搞清楚后,或能一并解了今日之迷雾。”
得了准允后,他面向陈靖,指了指那老汉:“陈将军,不知你还认得此人?”
陈靖辨认片刻,倏地大惊失色。
那老汉上前一步,结结实实叩了三个响头。
他粗粝的嗓音在大殿回响:“陛下,小人乃是关城守将宁远军中斥候,名唤宁七。”
“关城”“宁远”这四个字一出,殿内霎时鸦雀无声。
只因关城一战之惨烈,耳不忍闻。
八年前,漠北突袭关城,时任守将宁远,携军士百姓奋勇抵抗,最终却惨遭屠城,待援军抵达时,城中已无活口。
而那时前去驰援的,便是陈靖领的陈家军。
在场之人的目光不由在他二人之间逡巡。
宁七梗着脖子,继续道:“八年前,陈靖受命押送粮草至关城援战,可不知何故,却比原定时日足足迟了五日。
“关城将士誓死护城,连百姓亦挥刀上阵。粮草迟迟未至,众人只能饿着肚子拼杀,战至最后,城中仅余百人。
“宁将军直言,必会将此事上报天听,告他陈靖懈怠不力之罪。殊不知陈靖竟因此起了杀意,将我关城屠至殆尽,兵士百姓无一幸免,事后又伪造成漠北人的手笔。”
他的视线如刀光剑影,寸寸杀向陈靖,大喝道:“陈靖狗贼,天理昭昭,留我宁七一条薄命,今日,我便要你还我关城血债!!”
宁七的话,在场有许多人一时没有听懂。
什么意思?
关城,竟是陈靖屠的么?
可再看陈靖此刻,方才的失态似乎只是一时错觉,他面阴如沟,沉着声音道:“一派胡言,八年前我赶至关城时,那里已无生机,大殓祭丧一事还是由我来操办的,陈家军麾下皆可为证。”
宁七冷哼,从怀中掏出一份卷轴,高声道:“是真是假,自有可辨!此乃宁将军绝笔,内书当年关城之战始末,小人幸不辱命,终完成将军临终所托,请陛下明鉴!”
那卷轴纸面泛黄,看起来有些年头,虽沾有零星血迹,却无一丝破损,可见此人保管之用心。
殿内落针可闻。
三皇子脸上带了茫然,事情的走向已远超他预料。
陈靖身如磐岩,“可笑!拿这区区一张纸,便说是宁将军手书,谁人能辨?”
他话音刚落,一人阔步而出。
“我能辨!”
是太仆寺卿,秦简。
“陛下,臣与宁将军为至交好友,常有书信往来,是否为宁将军笔迹,臣一看便知。”
太子挥了挥手,立时有人将东西呈了过去。
不消多久。
他抬起臂朝皇帝深深作了一揖,再起身时,满脸肃穆:“陛下,确为宁将军笔迹!”
陈靖以眼神威之,“秦大人,你可得看仔细了。”
“秦某可以性命担保。”
此话一出,众人看向陈靖的目光瞬时变了味。
陈靖面藏阴鸷:“未尝不是有人模仿所作,我听闻漠北多异人,说不准这扮作宁七之人,便是漠北派来的,该好好查查才对!”
宁七神色不动,只从袖口又掏出一物。
而这一次,陈靖再也维持不了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