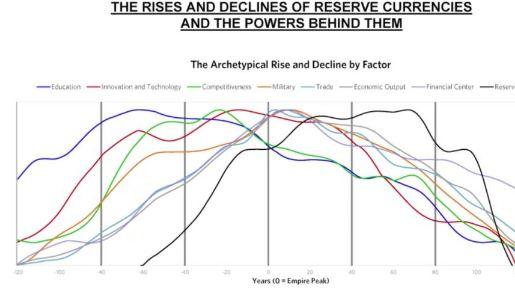一个历史人物的一生,很难用“忠奸正邪”简单定论。好与坏真的真的很难说,不能因为一件负面或者是一件正面的事情,将其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或者将其送上神坛,只能说,历史人物要在具体事物具体分析。
比如说马士英这个人就很难界定,马士英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以南京户部主事步入仕途,在巡抚宣府的时候。因擅取公帑行贿被御史弹劾,坐遣戌,流寓南京。崇祯十五年复起,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州、凤阳等地军务。

1644年三月十九日,崇祯自缢而亡。
在这种情况下,在南京的衮衮诸公在对于立何人为帝的问题上争论不休,都想让自己拥立的宗室为帝,当时最有资格登基的有三人:福王、桂王和惠王,而在东林党人看来,谁当皇帝都行,唯独福王不行,因为当年的“国本之争”,东林士人与老福王结怨太深,南明也就此陷入内讧。南明这伙东林士人为了一己之私,当年用“立长不立贤”对抗万历。如今,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又玩起了“立君当立贤”。反正都是他们有理。在拥立福王和潞王的问题上,南京吵得不可开交。
当时的兵部尚书史可法在此情况下找凤阳军务总督马士英参与拥立新君。应该说,如果不是最后战死扬州,就个人能力而言,史可法实在太差,比马士英差的太远,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南明史大家顾诚认为,史可法的一生只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廉洁勤慎,二是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至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值得过分夸张。

对于当时的这对马士英来说,老朱家谁来当皇帝,他并不在意,关键要押对宝,自己要有拥立之功,自己将来才有机会当首辅,由于当时见潞王势大,马士英毫不犹豫站队潞王。但此时史可法临时变卦,拥护改立桂王。见史可法变卦,马士英也摇身一变支持桂王。由于此时各方意见一致,史可法当即派人到广西迎立桂王。
但万万让人预料不到是 ,马士英去了一趟凤阳当即就变卦了,他得知江南四镇总兵正在密谋拥立福王。江南四镇还答应马士英,只要他拥立福王,他们一致拥护他当内阁首辅,于是马士英当即挑头,接上福王,带着太监卢九德,在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掩护下,赶到南京,武装进城,通电大明,福王朱由崧登基,年号“弘光”。一顿操作。史可法和东林士人全傻眼了。身处乱世,就是武将说的算,东林党这下彻底完了,而马士英也迎来了权倾朝野的首辅。

南明弘光政权仅仅存在一年,马士英作为内阁首辅自然要为南明弘光政权的覆灭承担主要责任,从具体历史情境分析,其责任需结合明末结构性矛盾综合评判。在史书里,说马士英担任首辅的时候,十恶不赦,党同伐异,卖官鬻爵。史载:“为人贪鄙无远略,复引用大铖,日事报复,招权罔利,以迄于亡”。这显然是构陷,马士英到底贪不贪还真不好说,并没有确凿证据,史书里也难以证实。
但有一点马士英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推卸的责任,就是他提出的“联虏平寇”策略。这一策略直接导致后金声势壮大,加快了南明灭亡,也就是内耗优先于外防,但这一策略得到了史可法的鼎力支持,所以这一点是他与史可法共同承担。“联虏平寇”堪称是最为愚蠢的策略。

再就是马士英的为了巩固首辅之位不断内斗,南明当时什么都缺,唯独不缺内斗。而马士英作为头号权臣,给这个内斗做了最好表率。后来,1645年左良玉以“清君侧”名义东犯时,马士英选择抽调黄得功西征,导致江淮防御空虚,清军乘虚而入,马士英虽然名义上节制对江北四镇,但高杰、刘泽清等人并不听他的,甚至彼此内讧,这也极大地消耗了抗清实力。朱由崧作为傀儡皇帝,话语权把控在东林党手上,更没有军权,自身难有作为。
弘光政权存续仅1年,且财政已经崩溃、军队军阀化,时间与资源都不在南明,在这种情境下,又重启“逆案”,朝堂陷入“拥福王”与“拥潞王”的路线之争。这样的的烂摊子。即便朱元璋复生,短期内亦难扭转乾坤。

至于南明士大夫,也以为东晋和南宋的历史可以重演,甚至对方也是女真人,国号也是金,只要能保住江南,谁当皇帝,他们都可以保住自己富贵。偏偏历史没有重演,最后江南地区之所以抵抗,却是因为剃发,但大势已去。另外,南宋赵构皇帝身份无人质疑,即使他跑到海上,依然是宋朝领导核心,这一点南明没法比。如果崇祯当年跑到江南,或者让太子到江南,也就不存在那么多纷争了。
但历史总是充满讽刺。这位南明第一个奸佞,在清军攻打南京,弘光灭亡在即,拼尽全力把邹太后等人送到浙江后,再次返回前线,继续抗清。清军进攻南京时,马士英的二儿子马锡留守城内。被清军杀害,首级挂起来示众。这个事实也说明,马士英派另一个儿子掩护弘光撤离的同时,还试图在南京组织起抵抗。马士英的堂妹夫杨文龙,坚持抗清,一家三十六口全部被清军所害。说马家满门忠烈并不为过。

最终,马士英太湖兵败被俘。宁死不肯降清,“剥皮,实草”壮烈殉国,对比钱谦益的水太凉,讽刺不。拥立福王是国家内部问题,联掳平寇是策略水平问题,但是在民族大义上一点儿也不含糊,英勇抵抗异族最后落得个剥皮实草。
马士英蠢,东林党同样蠢,他们的出发点都一样:搞权、搞钱、搞小集国利益,都有历史和人性的局限性。而马士英确实忠君,但他能力有限,可起码比史可法强,很多历史都是以结果做导向评价,到他身上时因为是得罪了另一个集团,所以变成了以另一个人定结果做导向评价。

南明史的时候就感觉人性复杂,心情也很复杂,你觉得这个人是个祸乱朝纲的奸臣吧,他最后又宁死不降以身殉国。你觉得这人是个忠臣吧,他转眼又剃了大辫子。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