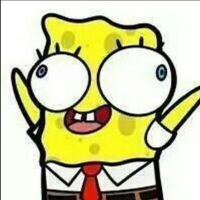1976年,短短9个月的时间里,党和国家的三位杰出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和毛主席相继逝世。
全党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也深深地忧思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好在10月时,一个好消息传出。特殊年代的结束,使我国的社会秩序得到了恢复。
我国领导人也为了将过去浪费的时间抢回来,把过去的经济损失夺回来,表现出了加快经济建设的急迫心情。
这个时候,为激发经济活力,“准备借鉴何种经济模式及其经验”就成了领导人首先需要确定的重点问题。
因为一些原因,我国想要借鉴西欧的经验,于是就有了1978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队赴西欧五国考察之行。
归来时,谷牧感叹:“差距太大了,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

1967年至1976年,总计10年间,据国内学者陈东林的说法,“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并不算太慢”。
他列举出了一些数据,表示这10年间,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社会总产值以及国民收入的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7.1%、6.8%和4.9%,其实超过了其他亚洲大国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只是这样的统计数据让很多人存有疑问。毕竟,这10年间我国确实出现了“经济的萧条和饥荒”。1977年国家计委提供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

据估计,我国在10年间出现的经济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
用1978年2月《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具体表现在,1978年时,在全国范围内,至少有2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农民甚至处在赤贫状况。
这种境况,让许多直接接触农民的官员都深感愧疚和焦虑,中央领导集体里,也多有人认为国家太穷,农民太穷,是他们对不起人民。更有人担忧,这些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恐会引发“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的糟糕情况。
这些都让高层急迫地加快了酝酿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

在编制长期规划时,最高领导层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国外,主要是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
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古今中外,历来改革都是“先睁开眼睛看世界,从对比中找差距”。

只有自由地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才能针对性地吸收先进文化和技术,在改革中谋求进步。可以说,只有打开国门,改革的步子才能真正迈开。
其次,我国当时已经具备了对外开放的政治平台。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毛主席和周恩来就已经通过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同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全面建交、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努力,很大程度“开通了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
1978年时,邓公又促成了中日缔约,中美建交,我国对外开放的政治平台也就完全形成,获得了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

再来,我国想要在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宏大目标,几乎唯一可行的选择是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这一现实需要,使我国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国外。
要知道,1978年时,我国大多数技术设备还是以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项目为基础,这些技术和设备在50年代并不是最先进的,20年间又逐步老化,我国在封闭的环境下只能不断“复制古董”,落后就成了必然。
更让人惊心的是,这20年间,世界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却是突飞猛进,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就以超出想象的速度“迅速拉大”。

实行“拿来主义”,以引进外国设备、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为起点,就是我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一个大政策”,有助我国更快实现现代化。
最后,我国谋求进步,也在当时得到了美国、日本和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
当时,美国、西欧受苏联威胁,从遏制苏联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出发,它们都希望我国成为世界的稳定力量,也就乐见我国走向强大,愿意支持我国朝向现代化的努力。
再加上,20世纪70年代,正是资本主义国家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出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趋势的时期。如日本和西欧国家都争相想要借钱给我国,争相同我国谈贸易。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确定了1978年5月派遣考察团赴西欧五国,也即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的行程。

这趟西欧五国之行,中央很是重视。
因此,在确定考察西欧五国代表团的人员名单时,中央考虑了很多,不仅指定了分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担任团长,起带队统筹作用,在安排其余成员时,也多安排了“大有来头”的人员。
比如,代表团中有7、8人均为部级干部,包括时任水电部部长的钱正英,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张根生,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等人,另外20余人也都是来自中央和地方、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负责人。
按照计划,这一考察代表团会在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总计36天的时间里访问西欧五国的25个城市和80多家单位。

他们需要会见有关政界人士和企业家,需要参观的项目以工业交通为主,范围涵盖电力、冶金、机械、公路、机场、港口等。
这也使得他们要在36天的时间里尽可能地多参观一些“角落”,如工厂、农场、城市设施、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等都不能落下。
这样的行程,是谷牧和邓公协商确定的,期间其他代表们也都贡献了他们的意见。
当时,所有人都做好了在西欧五国受到思想冲击的准备,但现实是,他们受到的思想冲击远远超出了想象。
用谷牧的话来说,就是:“差距太大了,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

其实,考察西欧五国的代表团组成时,20多位主管经济的高干碰头,才惊觉里边只有2人出过国。一个是水利部长钱正英,过去他曾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访问,另一个人则是外交部给配的工作人员。
这也意味着,这趟西欧之行,是代表团中绝大多数人“第一次走出国门”。当他们第一次“身临其境”,在西欧五国观察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当代发展情况时,他们就如乡下人进城,除格格不入之外,还因为他们的发现,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以谷牧为首的20多位出访者,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没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如此程度,没想到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会如此之大”。
他们在考察中发现,以西德为代表的西欧五国,在工业生产中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高度自动化,在农业生产中机械化程度很高,甚至整个西欧高速公路也形成了一个网络。对比下来,西欧五国的劳动生产率要高出我国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举例说明,工业生产方面,我国想要年产5000万吨煤,需要用16万名工人,但在西德,生产相同数量的煤只需要2000名工人。
农业生产方面,以我国安徽省为例,4000万农村人口中,就有3500万以上的人吃不饱肚子。丹麦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6.7%,生产的粮食、牛奶、猪肉和牛肉却可供3个丹麦全国人口的需要。
如此巨大的对比,让谷牧等人产生十分强烈的差距感和落后感。
此外,他们第二个强烈印象就是西欧五国有“许多好的东西”。
他们发现的大多是一些先进的制度和理念,如中央和地方适当分权,办事机动灵活,如强调优胜劣汰,十分注重企业管理,如重视培养科技人才,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学研究等等。
这些都在归国10天内,被他们写入《访问西欧五国的的情况报告》里,上报给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甚至,他们还上报了西欧五国的民生现象,和我国形成了强大的反差。
比如,我国城市职工20多年没涨工资,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仍多数难以拥有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农村情况更加糟糕,有2亿人口未解决温饱。但在西欧,工人的工资都相当高,人均住房达到20至30平方米,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家家都有,就连汽车也很常见,就是在农村,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同工人相差无几,社会保持着稳定。
正是因为有这些发现,有这些对比,谷牧才会更坚定“非改革不可”的想法,才会生出了更为强烈的急迫感。
参考文献:
樊超,王珂. 考察出访与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1978—1979)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03): 37-46.

萧冬连. 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 [J]. 中共党史研究, 2017, (12): 26-41.

清苑党校 1978年以后中国人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