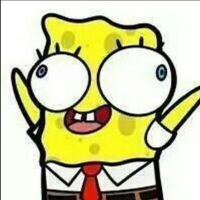1949年,国民党已经走到了尽头,绝大多数国民党将领在此时都面临两个选择:
跟随蒋介石,对抗到底。
弃暗投明,带队起义投奔我党。
但是在这其中,有一个人走出了第三条路,他就是张治中将军的女婿——周嘉彬。

作为国民党军将领,能够进入黄埔军校深造的,都不是一般人。
孙中山先生创办,蒋介石担任校长,周总理担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在当时简直就是将军的摇篮,只要进了黄埔军校,就相当于已经在历史书上预定了一个席位。
周嘉彬就是黄埔军校第五期的优秀毕业生。

1900年,周嘉彬出生在云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商人家庭,7岁上没了父亲,在姐姐和母亲的拉扯下艰难长大的周嘉彬,还没等成年就又没了最后两个亲人。
成了孤儿的周嘉彬早早就学会了自立,在当时的小学校长的教导下,他看到了旧中国的积弊甚多,虽然革命革了很多年,但是中国仍旧在苦苦挣扎,寻不到出路。
列强环伺,军阀林立,中国风雨飘摇的现状让周嘉彬毅然决定投军。
20岁的周嘉彬,连路费都是借的,孤身一人从云南去广州,考进了黄埔军校,并在那里结识了此后对他人生影响深远的一个人——未来岳父张治中将军。

张治中非常赏识这个纯粹的年轻人,在那个年代,虽然很多人都在革命,但是在条件好,待遇好,大多数人出身也很不错的国民党军队里,像他一样单纯地心系国家命运的,仍旧很少见。
于是毕业后,周嘉彬先是担任了黄埔军校第五期上尉区队长,后来直接被调到张治中身边当了少校副官。

1932淞沪会战,周嘉彬担任国民革命军八十八师五七二团的上校代理团长,在这次战斗中,周嘉彬身负重伤,但却因祸得福,得到了蒋介石南京警卫师师长俞济时的赏识。
1934年,周嘉彬得到了去德国柏林学习的机会,跟他同去的,还有蒋介石的二子蒋纬国。

周嘉彬从小就在母亲的影响下,把知识的重要性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得到这次去柏林学习的机会,他简直如获至宝,恨不得把德国人所有的先进军事知识全都学会,好搬回国内,“师夷长技以制夷”。

但是在德国的日子里,周嘉彬学到了远比知识更加宝贵的,就是德国军人端正的姿态,以及时刻饱满的精神。
因此在他学成归国后,担任军校的教育工作的期间,他对手下的学员的精神面貌要求非常严格,无论是仪容仪表,还是训练的动作规范标准,他都像当年在德国求学时的自我要求一样严苛。

正是因为他的严格要求,从他手下出去的军官一个比一个优秀,总带着别人没有的精气神,让人一看就觉得打胜仗不在话下。
于是在此后多年里,周嘉彬更多的还是在从事军事教育工作,亲自上战场的机会反而不是很多。

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后,国共两党维持了短暂的和平,内战很快爆发。
共产党军虽然背后没有强大的资金以及军事支持,仅靠小米加步枪也在短短四年内,就把国民党军打得溃不成军。
蒋介石逃往台湾,大陆的国民党军也是各寻出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看不惯当下的国民党人腐败风气,干脆弃暗投明。

但张治中周嘉彬这翁婿俩则不同,这二人都是非常纯粹的爱国人士。
在抗战结束后,他们本就不愿参与进同胞相残的内战中,但是无奈蒋介石率先撕毁条约,作为国军将领,他们也是十分的为难。
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张治中将军既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又不能跟蒋介石马上翻脸,于是在起义条件成熟前,便一直绕开解放军的行进路线。
解放军电台对此进行了广播,时常收听的周嘉彬听到消息,对岳丈的做法心领神会,也有样学样,他手下的兵,连一枪都没向解放军开过。

1949年,驻扎在酒泉的周将军正在准备起义事宜,可家人却被胁迫前往重庆。
被掐住命脉的周嘉彬只能跟蒋介石虚与委蛇,蒋介石虽然心知肚明,这人已经跟他不是一条心了,但是在这时候被俞济时从旁一劝,也给了周嘉彬转圜的余地。
就是俞济时给他争取来的这短短几天的时间,周嘉彬当机立断,迅速调动所有能调动的人脉,搞到了去往香港的机票。

周嘉彬偷偷先送走了家人,而自己却留在蒋介石身边拖延时间,他知道,只要家人能先平安到达香港,那自己一个人,想跑也是很容易的。
毕竟当时的国民党乱成一锅粥,蒋介石焦头烂额,全国范围内国民党简直是四处灭火都灭不过来,根本没那个精力一个一个地看住像他一样,早就想离开国民党的人。
于是他给自己弄了一张台湾的证件,以及一张需要转机的机票,让蒋介石误以为他要从香港转机去台湾,可万万没想到,周嘉彬到了香港就不走了。

香港又不是国民党的地方,那时候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蒋介石再怎么强横,也不可能跑到香港来抓他。
于是周嘉彬带着全家人在香港避难,整整一年后,他才终于得以回到北京,但是此时的北京,早已是另一番天地。

北京此时已经是新中国的首都,可跟周嘉彬印象里的不太一样,新中国没有民国的官僚主义作风,也不再有奢华的上流人士和贫苦百姓的强烈对比。
在这里,周嘉彬真正看到了人人平等的样子,新中国虽然朴素,但是每个人却都活得像太阳花一样,喜气洋洋的。
周嘉彬喜欢这样的中国,他虽然当了半辈子的军人,但是经过革大的学习,党中央的决议,他不再领兵打仗,而是在水电部领了个参事的职位。

这样的生活跟他过去的都不一样,但是他却适应得很快。
曾经有的小洋楼,小汽车,说一句话,拍一拍手就能来端茶倒水的佣人通通都没了,可周嘉彬却更加自在了。
在过去将近三十年的国军高官的岁月里,他从来没有一天忘记过自己的初心,他最初投身革命为的不是个人的荣辱,直到三十年后,也一样不是。

过去的中国,是人吃人的中国,上层人士躺在金山银山上,过着奢靡且浑噩的日子,底层百姓挣扎求生,但求生空间却越来越小。
国民党革命革了几十年,说到底,不过是换了群压榨人的人来,用了些听起来好听些的借口。
本质上,底层百姓仍旧在受苦,民主到最后,变成了一句空话,一句喊出去就没有回音的口号。

但是作为手里有“权力”的人,周嘉彬回到北京后,发现自己一点特权都没有了,反倒为此高兴不已,因为这代表着他的梦想真的实现了。
他在家里养了花,养了金鱼,甚至学会了做饭,整天也像别人一样骑个自行车上下班,出去买菜,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中年人。
但是像三十年前刚刚进入黄浦军校的他一样,他仍旧勤奋好学,仍旧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兼容并包。

在这个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岗位上,他像一个年轻人一样认真钻研,保持了曾经在德国学到的,那种严谨到近乎刻板的状态。
因此这个国民党军“降将”,还获得了第四届政协委员的荣誉,直到1976年,周嘉彬在北京去世,享年76岁。
参考资料:
我的父亲周嘉彬——《黄埔杂志》周元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