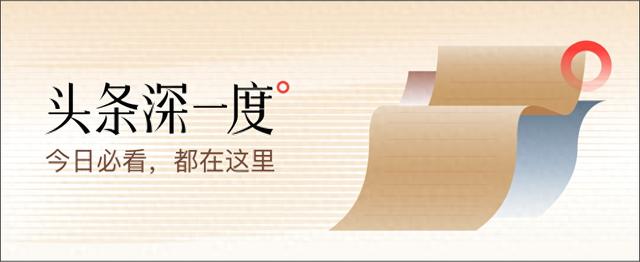
“清退令”的政策在建筑行业引发争议。
这项规定明确要求60岁以上男性、55岁以上女性农民工不得从事高强度、高风险的劳动,尤其是建筑工地的体力活。
政策表面上看是为安全考量,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一大批高龄农民工可能因此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没有社会保障,没有退休金,仅靠微薄的土地收益,他们如何养家?

我们先来看这项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初衷。
从2020年开始,国家对建筑行业的安全要求逐步提高,高龄农民工因体力和反应能力下降,被认为是潜在的安全隐患。数据显示,工地上因年龄相关问题引发的安全事故逐年增加,尤其在高空作业、搬运重物等环节,超龄工人的受伤概率明显高于年轻人。
此外,这些老年劳动力通常未接受过系统的安全培训,自我保护意识较弱,进一步加剧了风险。
因此,“清退令”的出台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希望通过限制用工年龄,降低施工现场的事故率,同时推动行业用工规范化。
政策的出发点虽好,但忽视了这些被清退的高龄劳动者背后的巨大生存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正视一个基本事实:高龄农民工群体在城市打工,绝不仅仅是为了多赚些钱,而是为了“活着”。
据202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现有农民工中有30%以上的劳动者年龄超过50岁,他们大多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缺乏一技之长。
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体力劳动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途径。一旦被迫退出建筑行业,直接意味着收入来源的枯竭。他们的生活状况本就捉襟见肘,很多人没有养老保险,甚至连基本的医疗保障都未覆盖。
当失业后,随之而来的医疗费用、生活支出将给整个家庭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换句话说,这些人“退无可退”,城市关上了门,农村却没留一条路。

政策的实施还引发了另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用工市场的矛盾。
2025年的建筑行业正面临严峻的劳动力短缺,年轻一代对建筑工地的高强度工作普遍敬而远之。数据显示,30岁以下进入建筑行业的农民工数量大幅减少,而每年新涌入城市的年轻劳动力更倾向于快递、外卖等“灵活就业”形式。
与此同时,超龄工人因政策被强行清退,直接导致建筑行业陷入“无人可用”的窘境。
更有甚者,一些企业为了节约成本和完成工期,不得不通过隐性用工的方式继续雇佣高龄农民工,甚至冒险伪造年龄信息。
如此一来,政策表面的严格执行,实际上催生了更多管理漏洞,安全问题反而难以彻底解决。

那么,失业后的高龄农民工又该何去何从呢?
部分地方政府尝试通过技能培训的方式帮助他们再就业,比如安排保洁、保安等低强度岗位。这些岗位的工资通常较低,仅能勉强维持生活。更多的高龄农民工可能只能回到农村,希望依靠土地补贴或农业活动养活自己。
现实并不乐观,现代农业早已无法满足一个家庭的基本需求,土地的收益微乎其微。很多农民工常年在外务工,对农业生产早已生疏,返乡后也难以迅速适应。
即便有地方政府推动乡村振兴项目,种植经济作物或发展乡村旅游,但这些计划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对广大的欠发达地区来说仍然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如果说技能培训和返乡农业是短期内的“权宜之计”,那么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长远之策。高龄农民工之所以在60岁后依然奔波在工地,是因为他们缺乏养老金、医疗保险等基本保障。
据2024年发布的养老保险覆盖率报告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档次低、金额少,大部分农民工即便参保,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也仅能覆盖基本生活支出的一小部分。
这就导致很多高龄劳动者只能靠“卖力气”补贴家用。
政府若能降低养老保险缴费门槛,提高养老金标准,并推动全国范围的养老保险统筹,则可以让更多高龄农民工体面退休,而不是被迫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生计挣扎。

除此之外,还需加强对高龄劳动者的立法保护。当前的劳动法在年龄限制、工作强度等方面,对高龄农民工群体的保护较为薄弱。
未来政策可以根据劳动岗位的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的用工标准,比如允许身体条件较好的高龄工人在低风险岗位继续工作,而不是简单地“一刀切”清退。这不仅有助于缓解用工市场的压力,也能保障高龄农民工的就业权利,避免他们被社会彻底边缘化。
我们必须认识到,“清退令”不仅是一个行业规范问题,更是一个社会责任问题。
这些超龄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无名英雄,是社会发展的底层支柱。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不该忘记他们的贡献,更不能让他们在年老体衰时被抛弃。
政策的制定需要兼顾安全和公平,既要保障行业发展的健康运行,也要为弱势群体提供有尊严的退路。

总之,“清退令”的出台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高龄农民工的困境需要被更多人看见。
政府、企业和社会需要携手,通过完善社会保障、灵活调整政策和加大技能培训力度,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有退有靠,不至于在年老时陷入无路可走的绝境。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安全与人性化管理的平衡,推动社会向更公平、更有温度的方向发展。
参考资料:
维护好“超龄”农民工的权益——光明日报2023-03-27 0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