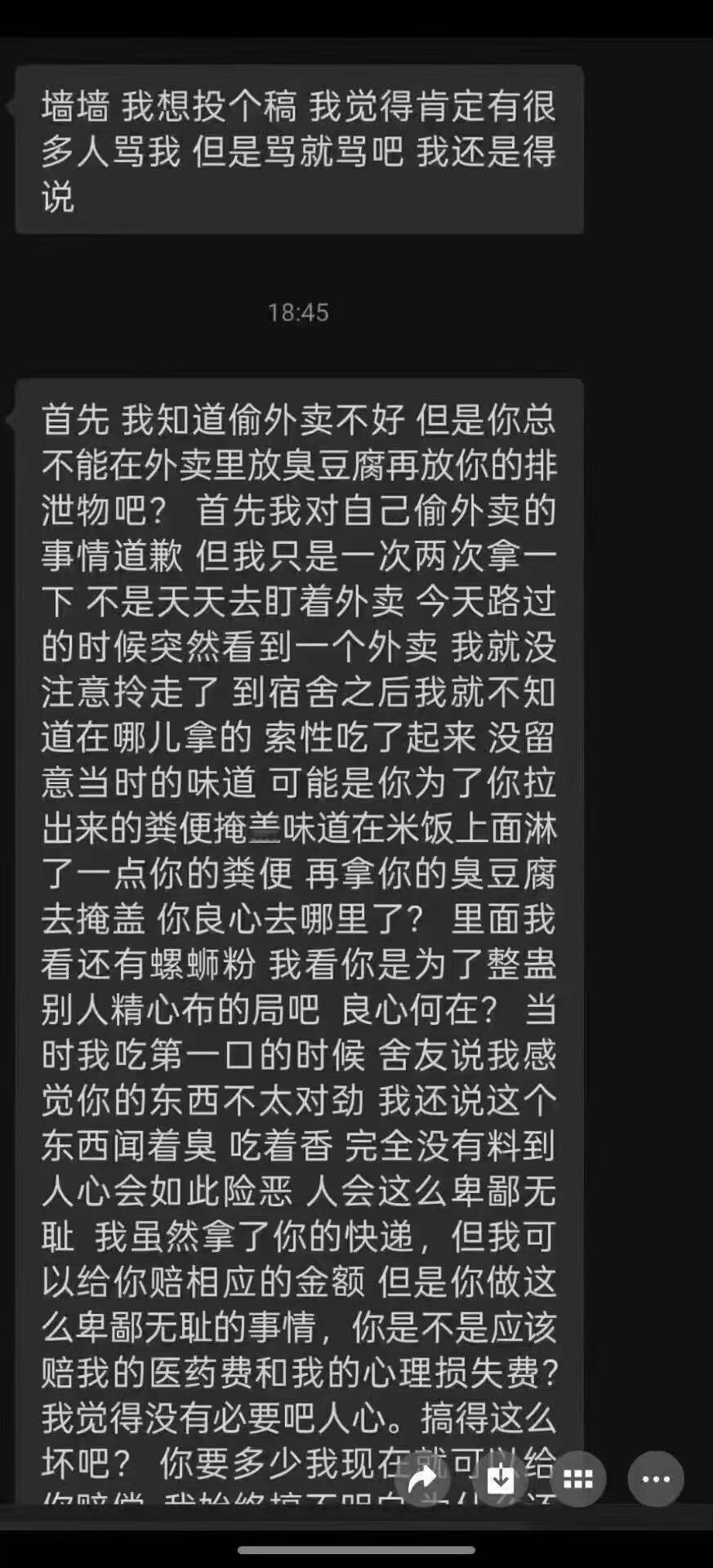我们单位那个大姐,一夜白头了。就因为她儿子,没了。大姐叫李娟,在行政部管后勤,平时总爱扎个马尾,穿件亮色外套,说话嗓门大,笑起来眼角会堆起细纹,是单位里出了名的“热心肠”。谁要是忘带饭卡,她准会把自己的递过去;谁要是加班晚了,她会煮好鸡蛋羹端过来,说“垫垫肚子,别饿坏了”。 我们单位行政部有个大姐,叫李娟。 不是那种精致的大姐,就是你上班路上会遇见的、拎着布袋装着饭盒、马尾辫梢沾着点碎发的普通女人。 她工位在茶水间旁边,桌上总摆着个搪瓷缸,印着“劳动模范”四个红漆字,缸子底沉着半块没化的冰糖——说是泡柠檬水喝,润嗓子。 嗓门是真的大,接电话时能穿透三排格子间:“知道了知道了!打印机下午就来修!” 同事们私下打趣,说娟姐的嗓子是单位的“闹钟”,听见她说话,就知道今天后勤准保出不了岔子。 她总爱帮人。 谁忘带饭卡,她准从布袋里掏出自己的递过来——那饭卡边角磨得发亮,贴着手写的名字“李娟”,旁边还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 谁加班晚了,她会从微波炉端出碗鸡蛋羹,嫩得能晃悠,上面撒一小撮葱花,“垫垫肚子,别饿坏了”,语气像叮嘱自家孩子。 有次我问她:“娟姐你天天这么操心,不累啊?” 她正擦着微波炉,闻言抬头笑,眼角细纹挤成一团:“累啥?大家在一块儿上班,不就跟一家人似的?” 变故是上个月来的。 那天早上我刚到单位,就看见行政部的人都低着头,茶水间没开,搪瓷缸子孤零零地在桌上倒扣着。 有人扯我袖子,声音压得极低:“娟姐儿子……没了,昨晚的事。”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想起上周还见她给儿子打电话,嗓门亮堂:“妈周末给你包你最爱吃的韭菜鸡蛋馅饺子,记得早点回家!” 再见到她,是三天后。 她还是扎着马尾,可头发全白了,不是染的那种灰白,是根根分明的、像落满了霜的白,顺着发梢垂下来,扫过那件她常穿的亮黄色外套——颜色没褪,人却像被抽走了魂。 她走进办公室,没像往常那样打招呼,径直走到工位,坐下,从布袋里拿出饭盒,打开,里面是两个冷馒头,她拿起一个,小口小口啃,不说话,也不哭。 没人敢提“儿子”两个字。 平时总找她借饭卡的小张,把自己的饭卡悄悄塞进她布袋; 总吃她鸡蛋羹的实习生,端来一杯热牛奶,放在她手边,手指抖得厉害; 连平时嫌她嗓门大的王姐,都红着眼圈说:“娟儿,打印机要换墨盒,你教教我呗?”——她知道,娟姐最怕没事做,一闲下来,眼泪就该掉了。 以前总觉得她吵,觉得她爱管闲事,现在才懂,那亮堂堂的嗓门、热腾腾的鸡蛋羹,不过是一个母亲在用力撑着生活啊。 她对我们好,或许是因为她总把同事当家人,或许是因为她想把对儿子的那份爱,多分给身边人一点——谁能想到呢?那个总说“别饿坏了”的人,自己先被掏空了。 现在她的搪瓷缸还摆在桌上,冰糖化了又添,添了又化,只是再也没人用它泡柠檬水了。 茶水间的微波炉,下午三点会空着,没人再端着鸡蛋羹出来,说“垫垫肚子”。 小张的饭卡一直放在自己兜里,他说:“娟姐的饭卡,该留给她儿子用——要是他回来,找不着妈,至少能凭着那张画着笑脸的饭卡,知道妈在这儿等过他。” 前天下班,我路过她工位,看见她对着电脑屏幕发呆,屏幕上是个文档,标题写着:“儿子房间整理清单”。 我没敢打扰,悄悄退了出来。 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风把她的白发吹得轻轻晃,像极了她儿子小时候,她牵着他在公园放风筝,风筝线断了,她追着跑,头发也是这样飘着的。 人啊,有时候真脆弱,一句话、一个名字、一张旧饭卡,就能把心戳个窟窿; 可有时候又真韧,明明碎成了渣,还想着把剩下的光,分给路过的人。 现在我们都默契地不去问她“还好吗”,只是在她加班时,默默给她的搪瓷缸续上热水,在她起身接水时,帮她把椅子往桌前推一推——就像她以前对我们那样,什么也不说,却什么都懂。 只是偶尔,茶水间飘来葱花味,我会猛地回头,以为是她端着鸡蛋羹来了。 然后才想起,那个总怕我们饿坏的大姐,自己心里的那个“饿”,这辈子都填不上了。
我们单位那个大姐,一夜白头了。就因为她儿子,没了。大姐叫李娟,在行政部管后勤,平
小杰水滴
2025-12-13 23:26:32
0
阅读: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