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梁元帝萧绎可能会有些陌生,但说起那庄半老徐娘的风流韵事,一定有所耳闻。故事中的徐娘,正是萧绎奈不住寂寞,与和尚、侍从私通的王妃,萧绎还在《金楼子》《荡妇秋思赋》中,将徐娘虽老风韵犹存的艳史传遍天下。

萧绎,萧梁开国之君萧衍第七个儿子,萧绎儿时生病,导致左眼失明,生理缺陷使他免不了被歧视,这反倒促成了他埋头书海勤于学习。《金楼子》一书中说他五岁诵《曲礼》,六岁可作诗,艺术方面更是无所不通。
长大后的萧绎被萧衍安排镇守荆州,如果老爹萧衍没有昏招频出,琴棋书画样样顶级的萧绎,估计会在他的封地只闻风月、不问世事,吟诗作画、舞文弄墨,快活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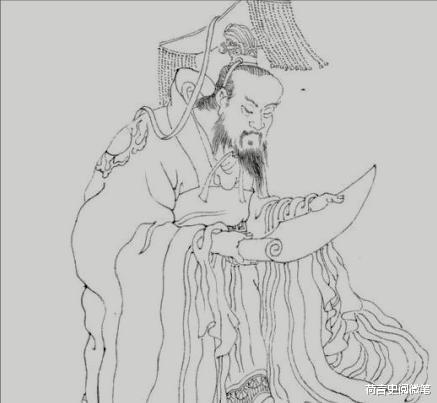
萧绎像
萧绎的原配王妃名唤徐昭佩,这女子本就好酒放荡,又因不得宠,总画半面妆容来嘲讽萧绎是个独眼龙,还背着萧绎与庙里和尚及萧绎侍从私通,才引出那句徐娘虽老,犹尚多情,后来隐忍多年的萧绎,将她的污秽之事公之于众,逼其投井自杀,并作诗文描述其淫行。

531年,南梁原太子萧统病逝,老迈的萧衍没有以嫡长孙萧欢为继承人,反立了庶出的三子萧纲,这可就引得朝廷内外人心惶惶。
嫡长子继承制都可以这样随便吗,那是不是意味着,庶出的这些皇子都有机会了呢?还是说谁的拳头硬就是谁的了呢?此事一出有理由推测,即便是没有侯景之乱,一旦“和尚皇帝”萧衍百年之后,萧梁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

547年,在东西魏间反复横跳,骁勇善战的侯景以十三州之地向南梁投诚,打着如意算盘的萧衍高兴不已,立马为其封王拜爵。
如果说萧衍真得到了侯景所说的领地也行,实际上的情况是:侯景嘴里所谓的土地都被东魏发兵拿了回去,萧衍得到的除了反骨仔侯景这颗定时炸弹,再就只有侯景那战败的八百残兵了。萧衍引狼入室的操作,实打实的当了一回“冤种”。

之后南梁与东魏停战和解,顿感不妙的侯景就仿冒高澄写了一封信,提出以被东魏俘虏的萧渊明换侯景,萧衍同意,侯大将军当即暴怒举兵倒戈。
起初侯景反叛老萧衍不以为然,直到侯景兵困都城建康,这才慌了手脚,连忙诏令天下,让各路藩王前来勤王,其中老七萧绎被委以重任代行皇帝之权。

结果萧梁这些狼崽子隔岸观火,出兵不出力,等着都城那边的情况变化相机而行,都想着有竞争皇位实力的死掉,自己起再兵拿下侯景。他们稳如泰山,老迈的萧衍如何扛得住。

很快,八十六岁的萧衍被侯景饿死台城的消息传来,萧绎终于誓师起兵,结果他攻打的是率军抵御侯景的萧誉(萧统次子)和萧纶,也就是他的侄子和六哥,而不是饿死老爹的乱臣贼子侯景。
这景象着实出人意料,至于为什么,侯景也好,张景李景随便哪个景也罢,对萧绎来说都无所谓,反倒是这些能影响他当皇帝的萧家宗室才是最大的障碍。

萧纶、萧誉自不是兵强马壮的萧绎对手,很快败下阵来,在将六哥萧纶被逼走,侄子萧誉斩杀后,萧绎又将大哥萧统的另一个儿子萧詧(chá)战败,迫使其向强大的西魏称藩。
眼见萧梁混乱如此,早就想分一杯羹了的西魏权臣宇文泰,派出大将杨忠尽夺萧梁汉东之地,这个杨忠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儿子:杨坚。

隋文帝杨坚
说回老七萧绎,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萧绎基本摆平了萧氏内部势力,这才想起来讨伐饿死老爹、杀死三哥又自立称帝,奸淫公主无恶不作的侯景。
552年,自称宇宙大将军的侯景,多次被萧绎派出的猛人陈霸先、王僧辩击败,在企图逃亡之际被部下所杀,尸身被大卸八块,挫骨扬灰,子孙悉数遭屠。

历时近四年的侯景之乱虽被平定,却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一时间南梁是千里绝烟,人口锐减,农业瘫痪,商业中断,可以说侯景之乱直接导致了萧梁的灭亡,更改变了南北朝的历史。

这时候挡在萧绎称帝道路上最强大的力量,是经营益州多年的萧衍八子萧纪。当初侯景之乱爆发,深受萧衍喜爱的老八萧纪是打算在益州起兵救父的,结果萧绎担心八弟抢功,就写信劝阻萧纪,将其挡在了蜀地。

不久后得知天下大乱至此,萧纪在成都称帝并东出攻打萧绎。萧绎这边刚消灭侯景,自己还没来得及享受平定叛乱之功,萧纪就先称了帝。于是萧绎不顾众大臣回师建康(今南京)以图后路的建议,执意在自己的地盘江陵(今荆州)登基。一山不容二虎,那就开打吧。

萧纪经营天府蜀地多年兵精粮足,萧绎深知靠自己是难以斗得赢老八,于是萧绎一方面封锁萧纪东出的江面,使其大船难以通行,一方面勾结萧纪身后的西魏,让其趁势偷袭成都。魏人再度看到染指南梁的机会。
急于争夺正统的萧纪,不管身后大本营暴露给西魏,挥师直取江陵。结果两下夹击之下,萧纪战败,在写信向七哥求和不成后被斩杀,南梁的益州也被西魏所得。

一年后,杨坚之父杨忠,与后来的北周八柱国之一的于谨等人,奉宇文泰之命挥师数万进逼江陵,早前向西魏称藩的萧绎之侄萧詧,同时出兵会同西魏进攻萧绎,江陵旋即告破,致力于“攘外必先安内”,死磕萧氏本家的萧绎就这样被杀了,甚至还没等到南梁的各路援军。

城破前,梁元帝萧绎站在他收集的典籍之前,大喊着读书万卷犹有今日,一把火将这十四万卷文明瑰宝尽数焚毁,冲天大火,数日不灭。什么概念呢?秦汉以来80%的珍贵孤本文献付之一炬!萧绎江陵焚书,可谓是文化的一场浩劫,让人叹息不止痛心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