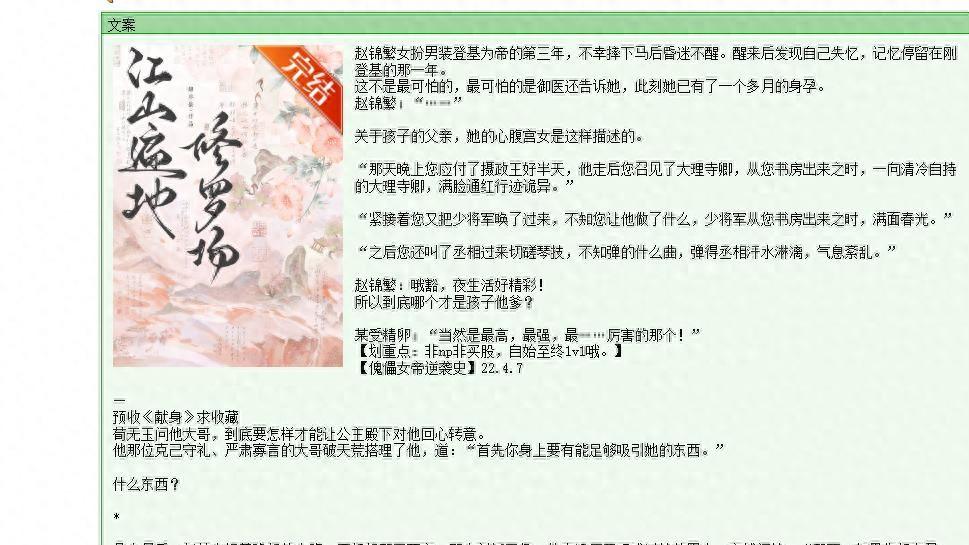简介:女主是女帝,登基三年,失忆之后记忆停留在刚登基的那一年,她对于怀着的孩子的父亲脑子里都是疑问!
之后她寻找腹中孩子父亲,便引出了科举舞弊,男主刚开始出现的不多,但是一出现就极其精彩,男女主之间的政治立场并不相同,两个人起初是对立的,之后两人由于某种原因两人便惺惺相惜,亦师亦友,彼此尊重。两人之间的拉扯很好磕,男主其实长嘴且直球,而且还又争又抢!
【文章片段】
入夜,赵锦繁与乌连王和先行到京的各国使团饮宴完回到紫宸殿。
福贵匆匆走进内殿书房。
赵锦繁屏退左右,低声问:“事情都办妥了吗?”
福贵点头应道:“硫磺、雄黄和硝石都按先前您吩咐的准备好了。”
“那便好。”赵锦繁抬头望向无边夜色。
算算日子,信王应当已到了云州渡口。她的仲父大概还不知道,她精心为他准备了一份大礼。
夜色沉沉,殿顶飞檐在月光下折射出清冷幽光。
如意提着灯,走到书房雕花侧窗前,见里头还亮着蜡烛。
她轻推门进去,看赵锦繁坐在书案前,握着笔用端正小楷在黄纸上写着什么。
“夜深了,您还不去歇息吗?”
赵锦繁写字的手稍停片刻,抬头看向她:“抄完这则往生经便睡。”
“往生经?”如意疑惑道,“可是先帝的忌日还未到,您抄这些做什么?”
“回头烧给一位未见面的故人。愿他早日安息,快登极乐。”赵锦繁如是说道。
如意未再多问,给她留了春夜御寒的披风,轻手轻脚退出房门。
赵锦繁继续低头抄经。
烛火摇颤,恍惚间脑海又浮上那晚的记忆。
那个男人抱她在书案上摆弄,没过多久,书案上的纸张沾染了粘乎的水渍,纸张上的字晕成一团模糊的墨迹。
见此,那个男人非要让她睁开眼看清那团糊墨。
“你看,明明是你喜欢,这是证据。”
当然他不会满足于这点证据,以至于到最后,把最难以抹去的那点证据留在了她腹内。
赵锦繁揉了揉眉心,从回忆里醒神。
她抬手按住小腹。
这里从那天起就多了个小人在蓬勃萌芽。
也是奇怪,最近怎么总梦到那个男人。她越是想看清那个人的脸,眼前的一切越是模糊。
*
大朝会一切事宜都在有序进行中。
次日早朝后,薛太傅和几位保皇派的官员在紫宸殿同赵锦繁议事。
期间薛太傅提到:“臣方才得了消息,东瀛和北狄的使团昨日已入关,不日就要抵京。”
赵锦繁道:“朕听闻东瀛人擅机辩、好斗智,每回来我大周,都会出些刁钻的难题为难我大周。去岁他们来大周时,出的难题很是不简单呐。”
虽然她半点也不记得了,但很是淡定地抬手指了指坐在薛太傅身旁的礼部侍郎:“对吧,柳侍郎。”
柳侍郎是保皇派中公认的老好人,性情温和且学识不俗,精通各家经典。
“正是。”柳侍郎忙道,“我大周佛学道学源远流长,去岁,东瀛人非要与我大周辩佛理,还专找那些偏门深奥的佛学典故出辩题。”
赵锦繁:佛理……
“东瀛人早有准备,本来胜券在握,不过他们也是惨。”
赵锦繁:惨?
“摄政王只用了几句话便将来使驳得无地自容,据说是因为他幼年在西南浅修过佛法,对佛理略知一二。”
“……”赵锦繁第一次知道略知一二这个词还能这么用。
“去岁东瀛在众国面前丢了大脸,今年或许会消停点也说不定。倒是北狄……”
薛太傅欲言又止。
“北狄自身资源贫瘠,靠掠夺他人得以生存,一直觊觎我大周领地。这几年一直在边关兴风作浪,试探我大周底线,恐怕此次来者不善。”
殿内气氛陡然有些低迷。
赵锦繁朝如意看了眼,不一会儿如意便同宫人们一起端上来一盘盘精致的糕点。
“先不说这个了,诸位先用些点心茶水。”
殿中臣子齐声谢过赵锦繁,气氛缓和下来,只薛太傅依然愁眉不展。
老人家一生忠君,为国为民,华发早生。为了她这个“不争气”的学生操碎了心。
赵锦繁心有不忍,宽慰他道:“先生莫太忧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大周也非那等任人欺凌的小国。”
薛太傅道:“是。”
用完茶点后,几位大臣又同赵锦繁谈了些如今的朝堂形势,骂了几句沈谏以及权臣派,临近黄昏才各自散去。
临去前,薛太傅叮嘱赵锦繁:“陛下现如今忙于大朝会之事,多有操劳,但臣还是不得不提醒陛下一句。”
“记得多多留意定国公。”
赵锦繁应下了。
如果说权臣派之首是沈谏,那么与之对应的保皇派领袖便是定国公。
保皇派如今士气低迷与定国公脱不开关系。
当初储位之争朝野内乱,信王来势汹汹,赵氏中人还能有机会坐在这帝位之上,定国公出力不小。
按理说定国公忠于赵氏,是支撑赵氏走下去的坚实力量,不过……
自她继位伊始,定国公上朝的次数屈指可数,三天撒网两天打渔,不是称病就是外出。并不像传闻中那般看好赵氏。
赵锦繁对定国公的了解和认知多半都来自于楚昂。
因为他是楚昂的父亲。
*
却说另一头。
掌灯时分,丞相府内,围廊前挂着的琉璃灯一盏接一盏亮起,璀璨生辉,如点点星河。
沈谏惬意地坐在水榭亭中,吹着风,闭目养神。
礼部尚书张永来访,在他耳边叨叨着:“听说下朝后,保皇派那几个老头就去了紫宸殿议事,一直议到黄昏,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沈谏懒得睁眼:“还能是什么,不就是那点事。”
他就是闭着眼也能猜到。
“无非是说点大朝会的事,顺便骂骂你,骂骂我。”
张永谄媚道:“他们骂我倒不打紧,可您为大周那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们怎么能……”
“得了,这些话就不必说了。”沈谏打断他道。
张永又道:“说起来上回宫宴那些没眼色的使臣和举子竟敢对您不敬,是否要微臣替您处理了?给那群人一点教训。”
沈谏睁开眼:“倒是不必。”
“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爱怎么说是他们的事,与我何干?”他抬手敲了敲张永的脑袋,“你啊还是省点力吧,凡事都放心上,会短命。”
张永:“……”
“您真是大人有大量!”
沈谏朝他笑了笑,继续闭目养神。
张永见他如此,也不欲再打扰,转身离开了丞相府。
少了张永在耳边叽叽喳喳,周遭顿时安静了下来。
沈谏本以为能好好休息一会儿,谁知张永刚走没多久,府里刘管事匆匆走进水榭。
“相爷,有您的八百里飞鸽急书。”
是谁这么不合时宜扰人清休?
沈谏骂骂咧咧接过刘管事递来的纸条,打开一看,上头只写了四个字。
只这四个字,让他原本和煦淡然的脸色一瞬沉了下来。
信上头写着——
“君上遇险。”
次日早朝之上,素以勤勉著称,为官数载从未缺席过朝会的丞相沈谏,未见人影。
执掌官吏日常考绩的吏部方侍郎执笏上前一步道:“启奏陛下,户部尚书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沈谏今日称病告假。”
礼部尚书张永纳闷。
昨夜他去丞相府时,姓沈的明明还生龙活虎好的很,怎么忽然就病到连早朝都上不了了?
丞相府书房密室内,墙面上挂着几盏蜡烛,烛火昏黄,气氛沉凝。
沈谏目光阴沉,看向来人:“如何,有消息了么?到底怎么回事?”
来人禀道:“君上回京途中,意外偶遇山石滑坡。”
沈谏敛眸深思。
意外……
*
千里之外,云州。
阴雨连绵,镇日不见天光,山里弥漫着浓重湿气,令人难以喘息。
信王的随行怀刃灰头土脸地从废墟堆里爬出来,呸呸吐了几口飞进嘴里的泥,满心愤懑无处发泄,只想仰天长啸一句——
意外个鬼啊!
事情要从两天前说起。
他们的队伍自千都山平叛归往京城,途径云州,恰逢云州积雨成灾,官道被雨水所淹,泥泞不堪,车马难行。
本打算改道走水路,从云州渡口乘船前往济州,再从济州出发回京,谁知偏就这么不巧,朝廷下令从济州往云州调粮救急。
连通云州和济州的宜水河上,所有能容人的大船和官船皆被调去运送粮食和救急所需物品以及受灾伤员。
剩下零星小船,虽可载人,但云州持续降雨,船身过小恐难抵水上风浪,稍有不慎便会葬身水底,因此没有船家愿意出船。
短时间内难以找到可行的船只。只能等官道积水消散,或是等大船和官船空闲下来,再行回京。
如此一来他们便需在云州逗留十数日。
不过君上似乎急欲回京,等不了十数日。
怀刃不知到底为何他那么着急回京,但云州地处盆地,四面环山,在官道不通,水路不行的情况下,只能改走山道。
山道路窄险陡,不易大队人马行进,为了不耽误时辰,怀刃和其他人暂且留在云州,君上独自先行上路。
谁曾想君上刚上路,未过多久便传来消息,说苍行山中路突发山石滑坡,整条山道的通路塌了个彻底。
苍行山中路,正是君上回程走的那条道。
身为信王长随,怀刃身经百战,遇事沉着,得了消息,并未声张,连同长风和几个可信的兄弟,先行进山查探。
他们在废墟里翻查了整整一天一夜,人是没找到,却意外在一处石缝中发现了些奇怪的草木灰。
一些混着硝石、硫磺和雄黄的草木灰。
这些东西单看没什么问题,加在一起却成了要命的东西——
火药。
恐怕是有人提前在这条山道设伏,引燃了火药,意图伪造成山石滑坡,杀了君上。
设局之人实在心思缜密。
一则,这一带恰逢雨灾,偶有山石滑坡不足为奇,不易被人察觉有怪。
二则,寻常很少有人接触过火药这玩意,除非常年行军作战,否则换个文官来查,未必能查出端倪。
三则,连日阴雨,雨水将残留的火药几乎都冲刷干净,证据消失殆尽。
若不是他们刚巧找到这些奇怪的草木灰,险些也被骗了过去。
怀刃深吸一口气。
真是好久没遇到这么狠,这么准,这么大胆的对手了。
不过有一点他始终没想明白。
他抬头望向连绵群山。
通往京城的山道不止这一条,君上行踪隐秘,从苍行山中路回京一事,除了他和长风之外,根本无人知晓。
那个人怎么就确定君上一定会从苍行山中路走呢?
*
京城,紫宸殿。
春日艳阳透过窗纱,照在书房青石地砖上。
赵锦繁静坐在书案前,手里摁着前几日信王托沈谏送来的信。
她的目光落在信上写着的两个字上——
十七。
如无意外,指的是他的归期,他将会在这封信送到的第十七天回到京城。
从拿到这封信的那一刻,她就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这么明目张胆的将自己的归期日程告诉给自己的对手。
这个人必然很强,强大到自负,随心所欲且极度任性。
以他的性情,宣告了自己的归期,无论怎样,都会在这个日子回到京城。
云州地处低洼,雨水一多,官道必然积水难行。
他想在十七日内归京,便会想到走水路从济州绕行。
只要将水路堵上,为了能尽快回京,他便不得不走山道。
山道路面狭窄又多陡坡,带大队人马回京,无疑会拖慢脚程。
他若要在归期抵京,必然会选择自己先行上路。
苍行山中路人迹罕至。
如此一来,她在山道设伏,便不会伤及无辜。
云州山道繁多,苍行山中路山道最短,却也最陡最险峻。
换做其他人未必会选。
但信王这样强到自负之人,八成会选这一条通路。
此人一生通达,平生未尝败绩,越是难以征服的险境,他越有兴趣。
事实证明,她赌对了。
今日早朝,户部上报云州赈灾的情况,提及苍行山一带山石滑坡引得山道崩塌一事。
加之,沈谏忽然“称病不朝”。
什么样的事能让沈谏连早朝也顾不上。
恐怕是信王遇险。
赵锦繁合上信封,松了口气,唤了如意进来,将手边的心经交给她。
“劳你替我去后院佛龛前将这叠往生经烧了。”
如意应是,接过抄满经文的黄纸,转身欲走,赵锦繁忽出声叫住她:“等等。”
“还是我亲自去。”赵锦繁道。
当是替她这位素未谋面的仲父送行了。
*
丞相府书房密室之内。
权臣派几位中流砥柱齐聚一堂。
礼部尚书张永:“怎么就这么巧,回京路上偏偏遇到山石滑坡。”
巧?
沈谏笑了。
他这辈子最不信的就是巧合。
就如当年科考,高中榜首的永安侯世子被先帝看上的那篇文章,同他从前写过的策论相差无几。
所有人都告诉他,那是巧合。
但那是吗?
荀某人怎么就好死不死偏偏就走了那条根本没多少人走的偏僻山道。
这其中没鬼才怪。
朱翰林忧心忡忡:“如今君上生死未卜,下落不明,我们该怎么办?”
沈谏坐在上首,抬眼:“能怎么办?他死了你还打算殉主吗?”
朱翰林:“……”
沈谏:“他死了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吗?”
他看向底下坐着的几人,沉声道:“一切照旧,云州那边一天没新消息,你等便当做没有此事,莫要自乱阵脚。”
次日,晨曦微露,京城迎来了东瀛及北狄的使团。
两国来使一前一后入含元殿朝见。
先进殿的是来自东瀛的使臣。
站在首位的来使走入殿中,第一眼看见的便是坐在高台之上的小皇帝。
瘦削轻薄的身材,瓷白的脸,唇小而精致,秀美的鼻子,上扬的凤眼,若为女子必定是位妩媚勾人的大美人,可他偏是个男子。
这样的容貌让他少了几分男子气概,看上去比传闻中更加软弱不中用。
“东瀛来使清原参见大周陛下。”
赵锦繁朝他抬手:“使君免礼。”
不仅容貌如此,连说话声音听上去也有些绵软阴柔。
这是清原第一次来使大周,从前出使大周的都是他的兄长。
不过他那个没用的兄长,去岁在大周与人辨佛理,结果被人几句话堵到哑口无言,在众国面前失了脸面。
兄长深觉无地自容,今年无论如何也不肯再来,只好由他出使大周。
他来大周前,兄长多次出言提醒——
大周人不好惹,切莫自寻没脸。
清原知道去年让他兄长在众国面前丢进脸面的是那位摄政王。
那位摄政王才是大周真正的话事人。
正如他们清原氏在东瀛一样,拥有凌驾于君主之上的绝对权力。
而眼前这位小皇帝便如同一件美丽的摆设,好看却无用。
清原曾见过那位摄政王的画像,他微抬眼扫了眼四周,见群臣之中,并未看到有类似的人物在殿内,遂起了几分轻慢之心。
他想起去岁兄长在大周受挫一事,心中不快,今年多少想找回些场子。
那位摄政王他惹不起,找他们小皇帝出出气也不是不行。
于是他故意道:“我曾闻贵国摄政王有过人之智,还以为大周尽是如他这般杰出的人才,特意代替兄长来使大周,想要好好会一会,却不巧今日并未见到一个想见的人。”
底下群臣一瞬愤然。
这是在骂他们在场的都是蠢蛋。
薛太傅出声道:“使君请慎言。”
清原立刻回击:“怎么你们陛下还未说话,底下臣子就能先开口,未免太过尊卑不分了吧?”
他将矛头指向坐在高台之上的赵锦繁。
殿内诸臣有口难言,其中难免有人牢骚。
东瀛人欺软怕硬,倘若此刻摄政王在,他们哪里敢如此出言不逊。
沈相和定国公皆称病告假。
如今坐在上头那位哪里压得住场子。
今日一早便闹了这一出,传出去让大周颜面何存。
在场的东瀛使臣们脸上显见有一雪前耻的得意
清原抬眼见高台之上的赵锦繁一副懵懂茫然的样子,心中更加不屑。
兄长说大周人不好惹,那也得分人。
比如眼前这位就软弱可欺得很。
正如是想着,他口中软弱可欺的小皇帝,忽然摇着头叹了一声。
清原微微皱眉:“陛下何以叹气?”
赵锦繁眨了眨眼:“朕只是在想一个问题,不知使君可否替朕解惑?”
清原笑道:“那是自然,东瀛人耳通目达,不至于连陛下一个小小的问题也解答不了。”
赵锦繁作不解状,道:“我大周乃礼仪之邦,对待外宾向来礼数分明,不同的外宾有不同的对待方式。接见通达贤明外宾的皆是优秀之人,卑劣无耻之国自然也不必由贤能之人接见。我大周自问以诚对待东瀛,今日来的皆是贤臣,可使君却觉在场没什么像样的人。”
“那么敢问使君,是自觉贵国卑劣下作吗?”
清原嘴角的笑僵在脸上,半天答不上来。
赵锦繁:“使君这是怎么了?怎么连这一个小小的问题都答不上来?”
她又叹了一声:“哎,那完了我还有一问要问使君呢。”
“不如这样,诸位在场的东瀛使者都来帮帮朕。”
被她叫到的东瀛使团无人应答,不过赵锦繁的问题还是照问。
“爱国护国之心,人皆有之,何分尊卑?在我大周即便是升斗小民也不曾有一刻将其忘之。方才使君出言辱我大周,太傅驳之,何错之有?”
“难道说在你东瀛,有人当众对东瀛出言不逊,你等也能坐视不理,一言不发?东瀛人都如此大度的吗?”
清原脸色由红润转成惨白。
方才心中牢骚的臣子听了这话脸上也是一阵臊意。
他国人挑衅自己国家,他们不想着反驳和解决问题,反而先看轻自己人,实在惭愧。
清原一行人站在大殿中间,只觉来自四面八方的每一道眼神,都另他们浑身难受。
他忽有一点体会到了去岁兄长无地自容时的心情。
尤其是再抬眼时,看见“软弱可欺”的小皇帝正朝他温和地笑,心里莫名瘆得慌。
当下也不再多留,低头告辞。
赵锦繁吩咐鸿胪寺的官员送他们一行人出殿,紧接着又迎来了北狄的使者。
北狄王和几个随同的北狄官员走进殿来。
这位北狄王长了双锐利的长眼,面向略凶,气势凌人。
几人并未向赵锦繁行礼。
北狄人觊觎大周领土已久,这几年在边关频频试探,意图撕毁从前签下的议和条约。
他们既想毁约,又不愿背上毁约失信的骂名,于是想尽办法来逼大周先行毁约。
此次出使大周,恐来者不善。
站在北狄王左边那位使臣出列,道:“吾乃北狄国师慕真,我等此次前来大周,有件东西想请陛下见见。”
国师一职在北狄是百官之首,等同于如今沈谏在大周的职位。
赵锦繁:“哦?是何物?”
慕真朝身后比了个手势,很快便有人押着只大木箱子上来。
站在高台前的两名侍卫对视一眼,上前查验箱子。
他们谨慎地打开箱锁,抬起箱盖。箱盖开启的一瞬间,两名侍卫脸上皆是震惊之色。
其中一名侍卫上前禀道:“陛下,箱子里……竟然是个人!”
且箱子里的人被刑拘铐着,像是个有罪之人。
赵锦繁看向慕真:“国师这是何意?这就是国师所谓的‘东西’?”
慕真回道:“回陛下,吾之所以称他为东西,只因他实在不配为人。”
他向身后人使了个眼色,身后两名北狄官员上前将箱子里的人拉了出来,扔在地上。
慕真对周围一众大周臣子道:“在场诸位,难道没有人认得此人是谁吗?”
礼部尚书张永拧着眉,盯着那人看了好一阵子后,惊出了声:“难道是……”
张永走上前回禀:“陛下,此人名为王盛,原是我礼部之人。十余年前大周与北狄议和,派遣使者前往北狄传扬大周文化,派去的正是王盛。”
“正是。”慕真道,“这位来自贵国的使者,在我北狄与人妇私通,被当场捉奸在床,犯有通奸罪。”
张永平日里是油滑惯了的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上阵没他影,装死第一名。此刻闻言却忍不住忿忿不平。
“陛下明鉴,那王盛是出了名刻板的老顽固,家中只有妻室一名,连通房也不曾有过,当年听说大周需要人远离故土,出使千里之外的异国,王盛毅然决然受命前往,这一去十余年未归过家了,是个令人敬佩的忠正之人。这样的人如何能做出国师口中之事?”
恐怕是有人刻意陷害。
慕真却道:“他在北狄犯下的事,人证物证俱在,不容狡辩。吾可管不得此人从前如何,只想问问陛下,何以你们大周要派这样的人来我北狄?”
从方才开始就站在一边不声不响的北狄王顺势出声:“还是说你们大周都是些同他一样的败类,找不出一个良人来?”
底下群臣哗然,一时声讨之声四起。
赵锦繁静默片刻,忽然笑了。
慕真不解:“陛下笑什么?”
赵锦繁回道:“不知北狄王与国师可否听过,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生在淮南的橘子甜香可口,生在淮北就变得酸涩难咽了。明明是一样的东西,偏偏味道一好一坏,天差地别,皆因其所处之地水土不同也。”
“朕比你们还疑惑,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王盛在大周是个忠良之辈,怎么到了北狄就莫名其妙成了作奸犯科之人,莫不是你北狄水土太差所致?”
慕真:“你……”
那位不怎么多话的北狄王怒目而视。
赵锦繁不欲再与他们多辨,瞥了眼殿外天色,道:“天色不早,鸿胪寺卿先安排几位来使安顿下来,稍后朕会在麟德殿设宴款待诸位来使。”
鸿胪寺郑寺卿领命,自群臣中//出列,对站在殿中央的北狄使团做了个请的手势:“诸位来使这边请。”
北狄王冷哼了一声,看了一眼慕真,甩了甩衣袖,朝殿外走去。
送走两国使臣,朝会终于散去。
礼部柳侍郎与薛太傅并排走出大殿。
柳侍郎想起今日朝会上一幕幕,道:“我总觉得咱们陛下似乎和从前有些不一样了。”
薛太傅问:“哪不一样?”
柳侍郎:“方才陛下在大殿上,很是能言善辩,灵敏机警。没有沈相和定国公在,却把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稳而不乱。”
薛太傅挑眉,捋着胡子笑道:“老夫的学生,就没有笨的!”
他忍不住提醒了句:“你呀你,仔细想想咱们陛下自登基以来,看似处处受人掣肘,可哪次真的吃过亏?”
柳侍郎一怔,张着嘴好久没闭上。
*
午后,赵锦繁坐在书案前翻着奏折。
鸿胪寺郑寺卿忽来求见。
“陛下,北狄王嫌弃鸿胪寺安排的住所太小配不上他的身份,是否另做安排?”
赵锦繁道:“在宫中寻处大的宫殿给他暂住。”
“是。”郑寺卿应下走人,可没过多久,又回来了。
赵锦繁道:“又怎么了?”
郑寺卿开口:“这位北狄王对花粉不耐,如今正是春花盛放的时节,宫中各大宫殿都种了各种名品花卉,只剩下一处大殿没种。”
赵锦繁:“那便安排他住那。”
郑寺卿:“这恐怕不行。”
赵锦繁:“为何?”
郑寺卿犹豫着道:“那处是摄政王留宿宫中时常住的,因其不喜欢颜色鲜艳,芬芳浓郁的东西,所以他住的地方不种花卉。”
赵锦繁:“……”
这人臭毛病还真多。
赵锦繁同他刚好相反,就喜欢色彩鲜艳,香气浓郁的东西。
她身上惯用意可香。
那天晚上那个男人,似乎也很喜欢意可香缠绵浓郁的味道,她的每一寸皮肤都不放过,全要吻啃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