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称得上是人世间最会描写爱情故事的作家之一。这位天才的艺术大师不拘一格写精灵,他借助于奇异怪诞的花妖狐魅,把人类社会小男小女的种种爱路历程表现得淋漓尽致、如闻似见。特别是在《莲香》、《娇娜》、《小谢》这样一些“双女”的篇章里,更是写得缠绵绝绝、韵味悠长。它像磁铁一样,以爱的磁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芸芸众生,令无数读者为之如醉如痴、唏嘘连声。

在人们的想象中,蒲松龄无疑应当是一位风流才子、一位情种,他的爱情生活也一定丰富曲折、充满情趣。可当人们找来《蒲松龄传》、《蒲松龄年谱》等一类书籍,打开一看,却不能不感到傻了眼:原来他的经历是如此地单调,单调得让人意外;他的爱情也十分平淡,平淡得让人乏味。
蒲松龄的确是位才子,但绝不风流。他家道中落,结婚时只分得不蔽风雨的老屋三间,还借了亲戚的一块白木板聊隔内外。荆妻刘氏是一位“文战有声”、但无功名的教书先生的女儿,亲事是由双方父母给定的。
婚后,刘氏生儿育女,默默地操持家务,与蒲松龄相伴始终,蒲松龄爱她、敬她,她是一位符合封建道德规范、性情温谨贞静的善良女性。她的行为,与《聊斋》许多篇章中充满野性和叛逆精神的狐妻鬼妾,没有一丝一毫可以联系得上的。甚至连他们的几个孩子,在她亲手调教下,也都一个个“内行修谨,不苟尺寸”。

生活的艰难与贫困,多子和灾荒的折磨,尤其是科举的屡屡受挫,蒲松龄的日子过得十分沉重,为了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他不得不常年在外,去为大乡绅人家当私塾先生。在当时人们的眼里,他是一位“口呐呐似不能言”的骏学究。
大乡绅家的规矩多。教书先生要为人师表,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言”,这铁箍一样的刻板生活,加上经济的拮据,哪里能够给他提供什么发生风流韵事的客观条件呢?
另一方面,作家打心眼里还没生出这份“邪念”,他认定自身是“病瘠瞿昙”转世,今世合当“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不难想象,一个以出家人胎骨自许的三家村冬烘先生,还能萌生什么艳遇之想呢?!
真是太扫兴了!依据文学和社会生活的鱼水关系,人们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位“妙笔遍生艳情花”的聊斋主人,竟会没有一点发人情致的罗曼史。这十分矛盾的现象,该怎么解释才符合真实?可真是一个难参的谜啊!
有人推测是传奇小说的影响,有人分析是民间传闻的作用,也有人归结为作家想象力,等等说法,不一而足,可似乎都没有触及谜底,难以令人诚心信服。

这个谜一直猜到后来一个新的说法出现了。有位北方学者从《蒲松龄集》中找到了一篇题为《陈淑卿小像题辞》的骈体奇文,并读出了“个中奥妙”。
这篇骈文显然出自蒲松龄的手笔,文章用第一人称的写法,描述了“我”的一段特殊经历:因为家乡发生了战事,村人纷纷外出逃难,途中,“我”与家里人失散了,只好孤身一人惶惶而行,并躲进山里,为了找水暍,偶然遇见同样无亲无靠、来此避难的妙龄美女陈淑卿。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刻,人性、人情的力量,比较容易地战胜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两个孤男寡女,决定结伴而行。由于相依为命的关系,他们产生了爱情,并结成了夫妻。
半年之后,战事平息,他们双双回到了家乡。因为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的结合被视为“野合”,被斥为“非礼”。公婆不敢承认这位送上门来的媳妇,社会也拒不接受他们的婚姻。在强大的封建意识的压力下,他们无可奈何,一对患难夫妻就这样被活活拆散了。
可是,“芭蕉虽死心不焦”,他们俩相互爱慕的心并没有因此而冷却,各自都还在苦苦思念着对方,私下里依然还在继续往来着。后来,陈淑卿生下了他俩的爱情之果,因为名不正、言不顺,不可能公开抚养,只得把这可爱的小生命忍痛送给别人。
又过了几年,这篇奇文中的“我”,说服了后来父母给他娶回来的妻子,答应把陈淑卿接到家里来。这位妻子愿意学着娥皇、女英的样子,要和陈淑卿共侍一夫。可惜陈淑卿刚接进府中,就不幸染病在身,没过多久,竟自撒手尘寰,一命归西去了。留下的仅有一幅薄命美人的小画像。

为了表达相思不已的感情,作者写下了这篇题词。
《陈淑卿小像题辞》的确颇似蒲松龄的自述罗曼史。作品中所说的那场战事,也确曾发生。经专家考证,那便是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元年发生在山东栖霞的于七起义。只是栖霞距蒲松龄出家乡淄川还有好大一段路,虽说陈淑卿也有可能从那个方向逃难或者移民来到淄川一带,然而蒲松龄却没有留下逃难的记录呀!要么就是蒲松龄故意把事情写得扑朔迷离以便让人难以指实。
此后不久,蒲松龄因为心情不佳,决定出门远游。正巧,他的同乡好友孙树百要到江苏宝应县赴任,邀请蒲松龄去那里做他的幕友,于是,两人很快便一同南下了。

大家不禁要问:蒲松龄的心情因何而不佳,且非出门远游而不能排解?更何况行迹又是如此匆匆?会不会因为不能和陈淑卿相厮守而苦恼烦闷,又会不会借远游来避睽睽众目,以实现携佳人而同居的目的?
这位发现蒲松龄“罗曼史”的学者,细心地给我们引述了作者南游期间的一首诗:我到红桥日已曛,回舟画桨泊如云。饱帆夜下扬州路,昧爽归来寿细君。
诗题是《元宵后与树百赴扬州》,记载着与孙树百同往扬州出差,心里却记挂着要在次日清晨赶回来为“细君”做寿。按说,这个“细君”自然是陈淑卿了,电视片《蒲松龄》就把这段艳情编了进去,播放出来则颇见情趣。可是,其中并不是没有疑点的,别的暂且不论,就说这“细君”一词,当时一般都用来恭维人家的小妾,是一种含有尊重主人意味的称呼,而不兴拿来指自己的小老婆。人所共知,蒲松龄的文字功夫很深,他恐怕还不至于闹出这样的笑话来吧!
那么,《陈淑卿小像题辞》的写作究竟缘何而起呢?
翻开《蒲松龄集》,人们便不难发现里面有不少作品是代人之作,其中仅《聊斋文集》中代孙树百的文字就达八十一篇之多,因为他当时身为幕友,代人捉笔正是职责之所在。于是有人提出:《陈淑卿小像题辞》是一篇代友人哀悼亡妻的作品。

可蒲松龄又偏偏十分细心,凡代人之作必在题中或题下明白标示,《陈淑卿小像题辞》却没有任何这类标示。这话怎么说呢?
而除此篇之外,又找不出别的证据来判别虚实真伪,可真把人弄得如同丈二和尚,竟自摸不着头脑了。
问题回到了开头:蒲松龄究竟有没有“罗曼史”呢?我们不可能“起古人于地下而问之”,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尽管学界对“罗曼史”之说难于首肯,但每个人仍然不妨用自己的感受去辨析。
试想:如果从蒲松龄为人方正来看,似乎不可能做出什么掩人耳目的“苟且”之事,退一步说,即使真有一段隐秘艳情,像他那样迂朴的文人,似也未必肯白纸黑字写了出来收在自己的文集里,让后人来指指戳戳。即在当时,也会因之有损声名而不利于他汲汲追求的功名大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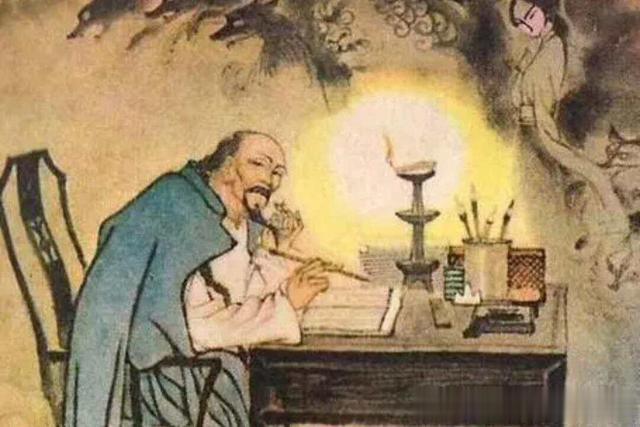
但是,如果再从《聊斋志异》本身来看,假使抽掉书中的全部爱情故事,它还能剩下多大的魅力呢?
也就是说,蒲松龄毫无恋爱体验,却同时又是一位描写恋爱的专家。这到底为什么呢?至今还是一个谜,一个尚未真正解开的奇特的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