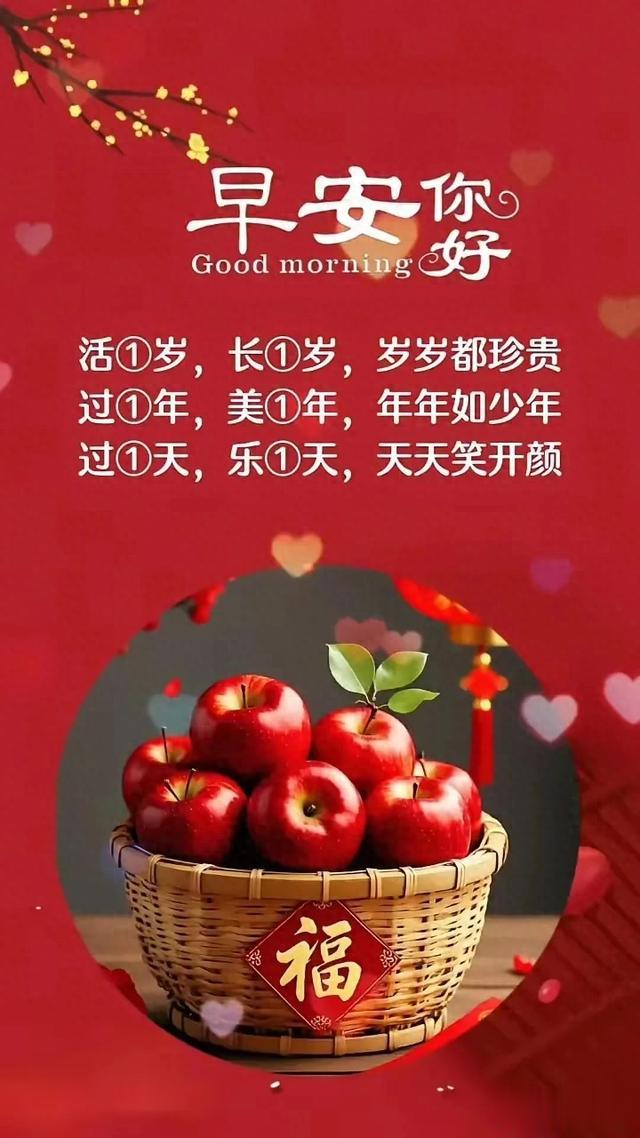
■ 戴春兰
当街上的艳红一天比一天繁密,当欢快的鞭炮声一声一声在耳旁炸响,当空气中都弥漫着米酒和煎炸的香味,年就摇曳多姿地踵过岁月的河,像闻到春信的花儿环佩叮当地降临了!
年,最早在孩子渴盼的眼眸里绽放。儿时老家,大人们是忙着酿酒、杀年猪、做烧大块的腊月,放了寒假的孩子们则天天在村口翘首以盼"爆米筒"的小贩。那个黝黑的大叔拉着拖拉机头似的机子走村串庄,一般一个村子只停留一天呢。
"来了!来了!"大家跟着机子兴奋地又蹦又跳来到晒谷坪,赶紧飞回家叫妈妈打米,自己又飞回去排队占位置。母亲看着孩子小馋猫样,抿嘴一笑,转身又多打两筒米,拎着满满一袋,三三两两说笑着出来。
大叔铆足劲儿用力一转,机子便"扑扑扑"地转动起来,冲出一股股黑烟。这一边刚把白花花的米倒进漏斗,就闻到爆米花的味道,许是加了色素,那一边机子口就接连冒出红的、黄的、白的"爆米筒"。大叔撑开麻袋一般的塑料袋,一根根拗成一米来长,整齐地装满袋子,再细心地扎紧口袋,受了潮就不酥不香了。
排在前面"爆米筒"的人家总会大方地拿出一袋分给整坪的大人孩子"尝尝鲜"。孩子们惊喜地接过,呼啸着跑远了。大人还笑着推辞,大叔也开口了:"吃吧吃吧!不过是一把米嘛◇保佑年年风调雨顺,日子越过越红火呢!"大家都哄笑起来,笑得满脸都是幸福的褶子。
大叔还会做一种"鸭嬷蛋"。雪白的爆米花裹着糖稀团成拳头大小,可不就是实打实的鸭蛋?吃起来口味和"爆米筒"相似,但孩子们一手拿着一样,既能像孙悟空一样耍金箍棒,又能模拟打战扔"手榴弹",欢笑声把寒冬都点燃了!
每年过年,最喜欢的还属牵着大人的衣角去赶年圩,在人群中挤进挤出,从街头一家一家地逛到街尾。一家老小置办新衣、新鞋,要暖和、好看、喜庆,衣服的质量和款式都不能差;要买鞭炮香烛草纸、写对联包红包的红纸、家里待客的饼果、拜年的"手信"……父母一件一件地摸着、捏着,比质量,讲价钱,忙试穿,直到十分满意了,才小心地掏出钱,捻出几张递过去。
孩子们眉开眼笑地试着新的衣服鞋子,总要挑自己最喜欢的再买下。大人买饼果时趁机每样尝一点,酥糖酥脆可口,麻香薄饼满是芝麻香,油炸"猪耳朵"厚实肥美,水果硬糖酸酸甜甜含在腮帮子里,圆鼓鼓的一个"包",伸手调皮地一戳,那个"包"就在左右脸颊间来回切换,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但孩子的脚都被琳琅满目的玩具牵绊住了:能"啪啪"打响的手枪,各色烟花鞭炮,能扭成动物花卉的气球,女孩子美丽的头花……孩子们提着大包小包,心里盘算着即将到手的红、包,恨不能把所有都搬回家!
空气中的年味越来越浓郁。孩子们要开始扫尘,用毛巾包住头,把鸡毛掸子绑在竹竿上,一丝不苟地把头顶上、屋梁上、墙壁上都细细扫一遍,然后擦窗户、洗桌椅橱柜。再贴上崭新的对联、福字,即使是老房子,也立马喜气洋洋地焕然一新。
家家户户的灶头都在"噼里啪啦"响个不停:肉香四溢的烧大块,鲜香甜美的包精,清新素雅的炸豆腐,还有灯盏糕、炸花生、炸豆子……白斩鸡黄澄澄的皮嫩滑上翘,烧大块蒸梅菜酸咸酥烂百吃不厌……比海潮还汹涌澎湃的香味,浓雾一般笼罩着整个村庄,撩拨得每位路人驻足细品。
更何况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乡心新岁切"呵!是为了夜深人静时仍在回味的家酷家酿?为了那合家团圆剪烛夜话的欢声笑语?为了空山鸟语般悦耳动听的家乡话?还是为了村口日日苦盼的日渐苍老的身影?哪怕远隔万水千山,哪怕已经白发苍苍,都会像南归的候鸟一般带着热切的向往朝家的方向飞奔!
(来源:闽西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