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请知悉。
前言苏轼可以算是收藏家吗?单看他给王诜的记文,似乎是不能这么认为的,但苏轼又确实收藏艺术品,而且并不像他在《宝绘堂记》中宣称的那样,仅仅是“少时之所好”。
只不过他在收藏时总带着些“纠结”,他有多珍爱那些书画,据为已有时就有多纠结,他对此讳莫如深,从来不在自己那些正式的文体如律诗或古文中提及。
 收藏家苏轼
收藏家苏轼这种态度在其早年所作的自传中即有体现:对待艺术品他总是乐于欣赏,而非汲汲于占有,苏轼的“纠结”与欧阳修坐拥古碑遗刻、并时时以之自许的陶然自得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是,苏轼的确曾经投身于绘画技法的研习之中,而不像一般的旁观者、批评家或理论家那样置身其外、只做客观分析。
他毕竟是那个但凡小酌便欲“书墙涴的坡公,所到之处,常常即兴题壁”,若不巧主人不买账、还是更爱原来的“雪壁”时,苏轼便会遭到指责。

以下,我将从苏轼浩如烟海的论画、论艺之文中撷取出一部分来分析,以期从中窥到这些艺术品怎样无所不在地渗入他的生活中:对于绘画,苏轼绝非只是发表空论而已。

参考资料
特别强调的是,这只是“部分”信息,还有大量相关材料散见于苏轼的文集中,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韩文彬关于苏、李(《西园雅集图》作者李公麟)交游考以及李公麟应苏轼及其门人之请所作画的研究。

韩文彬考察了苏轼时代的开封艺术品市场,透过那些各式各样的画展场所,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绘画在北宋士大夫阶层中的风行程度。
苏轼对待作品的态度苏轼年轻时曾斥钱十万,购得两块四面的唐代画家吴道子所绘菩萨像画版,送给他的父亲苏洵。

这在苏轼的人生之中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他一辈子在艺术品上花费最巨的一次,苏洵收集古画,并且懂得鉴赏,在他所有的私藏中,吴道子的这四幅画是他最喜爱的。

参考资料
1066年苏洵去世后,苏轼应先君故人释惟简之请,将四幅菩萨像捐给了当地一间寺院,据信,这种施舍所捐之物必须是施主“所甚爱与所不忍舍者”,方能算得最大的功德。
之后,寺院“以钱百万度为大阁以藏之”,苏轼“助钱二十之一”,并将苏洵的画像悬于四菩萨阁之堂上。

11世纪70年代,苏轼在杭州时,曾赠与郭祥正“御笔一双、赐墨一圭、新茶两饼”,御笔等虽为真物,但其实“得于大臣家”,故而“不罪浼渎”。

郭祥正
与此同时,苏轼考虑再捐一幅父亲生前所藏的罗汉像给大觉怀琏禅师,不曾想这次捐赠竟颇费周折:苏轼本欲捐出的是禅月罗汉像,与之接洽的僧人却修书来指名索要金水罗汉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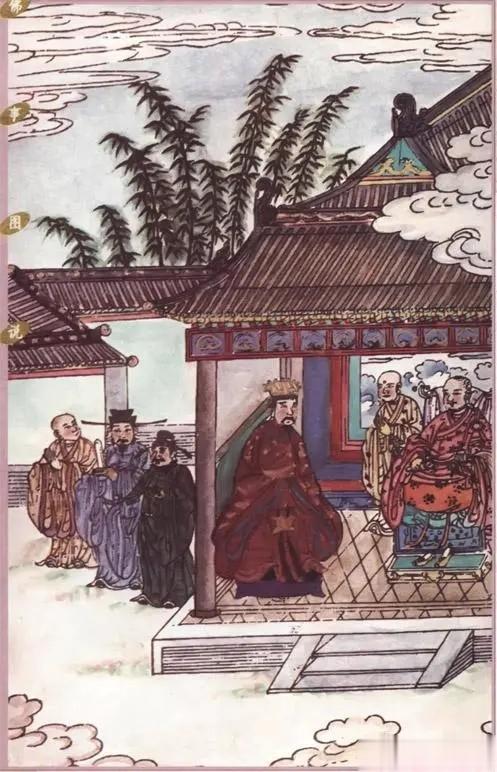
苏轼认为这是无礼的冒犯,在回信中甚不客气地说“开书不觉失笑”。这次布施最终有没有成功,我们不得而知。
11世纪80年代初,苏轼坐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友人王巩亦受到牵连,居黄期间,王巩曾致书给他,索要新近画作,但彼时苏轼却苦于无画可赠。

他回信解释说,在黄州,每次醉后都会大起丹青之兴,一气作画“一二十纸”,但往往差强人意、可留者不过其一,其余“多为人持去”,故而暂无可相赠者。

这一时期,苏轼还写了一篇有关蒲永升所赠画水之作的长文《画水记》,宋初川籍画家孙知微曾于大慈寺寿宁院墙壁上画湖滩水石,蒲永升为苏轼临摹了二十四轴。

苏轼在文中讨论了诸种“画水”的技法,同时,他还送了友人吴复古一幅山水画,该画出自苏轼新结识的一位不甚知名的画坛新人李明之手,苏轼建议吴复古用此画来装饰床上的绕屏。
后来,苏轼离黄北上,途径商丘时,曾遇到一位张太保,太保交给他十六轴罗汉画像,谓己“衰老无复玩好,而私家蓄画像,乏香灯供养”。

苏轼随后将罗汉像交与僧人开元明师,以为如此或能符合张太保之本意,在此期间,滕元发借给苏轼一套李成(10世纪著名山水画家)的《十幅图》,苏轼大喜过望,预备请人临摹后再归还给滕元。

1086-1088年苏轼任翰林学士时,李之仪送给他一幅李公麟所作《地藏》图,作为酬答,苏轼写了一篇评吴道子画的小文,与其所藏吴道子画(或为摹本)一幅,一并寄给了李之仪。
1088年,苏轼知贡举,阅卷之余,常与门人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及李公麟一起画马、画竹解闷,还依次为所绘之图赋诗。

1089-1091年,苏轼知杭州期间,他送给宝月大师一幅王诜所画的古松图,此图具有特殊意义:应宝月之请,苏轼托王诜向朝廷上奏“紫衣师号”。
1093年间,苏轼从扬州寄给鞠持正四幅蒲永升所绘水景图,而这很有可能出自多年前苏轼从蒲处获赠的、蒲临五代未孙知微绘大慈寺寿宁院壁画的那二十四个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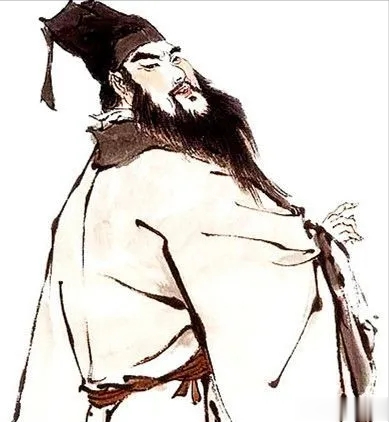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苏轼竟将其收藏了如此之久,苏轼在信中告诉鞠持正,夏日挂此画于高堂之上,凉风袭人,可以“一洗残暑”。

1094年,在遥远的北方定州,苏轼给李之仪寄去一幅宋初道士牛戬的《鸳鸯竹石图》,并说他此时唯念扫此长物”,遍散所收书画。
苏轼对书画的珍藏同年稍晚苏轼南游:过汝州时见到了弟弟苏辙,苏辙刚刚助资“百练”新修了当地隆兴寺中两幅吴道子所绘壁画,苏轼对弟弟此举甚为称赏,赋诗云“他年吊古知有人,姓名聊寄东坡弟”。

惠州贬谪期间,表兄程之才曾向苏轼索要墨竹画,苏回信说多年不画,笔已抛荒,暂无以相赠,但保证“候有嘉者,当寄上也”。
1100年,苏轼自海南遇赦北归,这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途中苏轼致信友人钱世雄,邀他来观赏自己收藏的一幅10世纪(五代西蜀)画家黄所绘的龙图。

信中说:今正曝凉之,只近来闲看否?
他请钱世雄来看“龙”并非只为了赏其图写之妙:以前苏轼牧守他郡,遭遇天旱时曾在此画前燃烛祈雨,他知道钱也正面临缺雨的困境,因此叫他不妨来“燔一炷香”。

尽管以上所引材料只是很小一部分,但亦足以说明苏轼终其一生都在积极地收集、珍藏、借出和获赠书画作品。

无论是数百年前的古迹还是朋友熟人的新创,他都一视同仁,加以珍存,他一天都离不开书与画,这不但是生命之必需,也是快乐之源泉。
当然,他自己也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创作,并且深知这些“东坡手迹”的风靡程度。
参考资料:
【1】中国知网——《苏轼书法的公私收藏》张家玮、曹建。
【2】中国知网——《苏轼收藏趣话》吕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