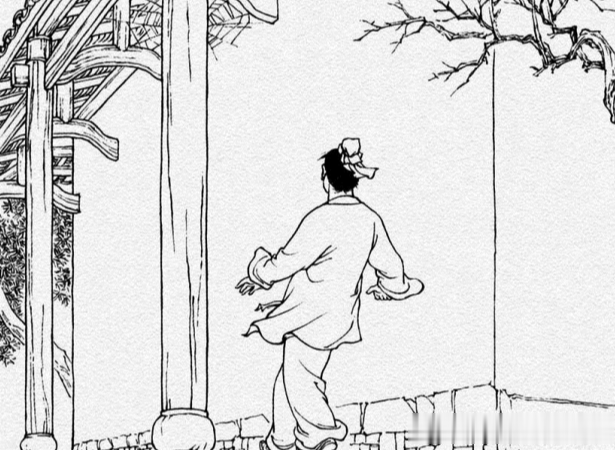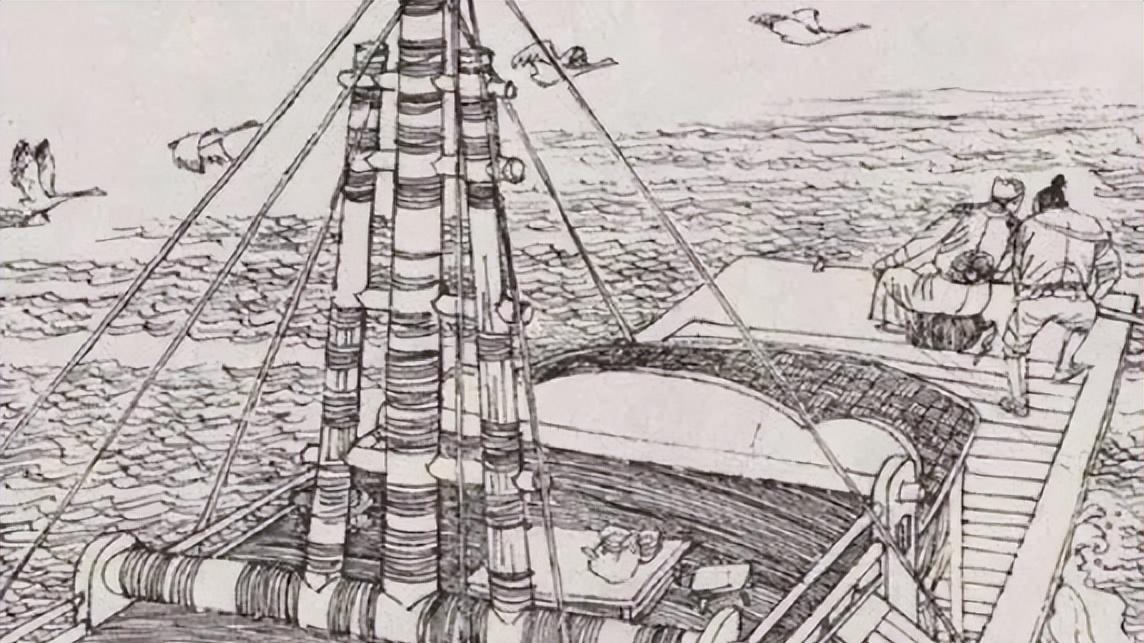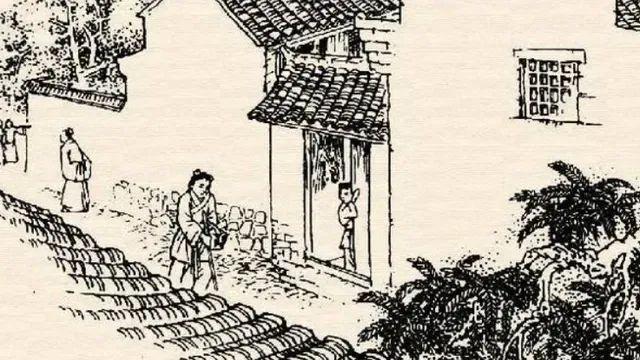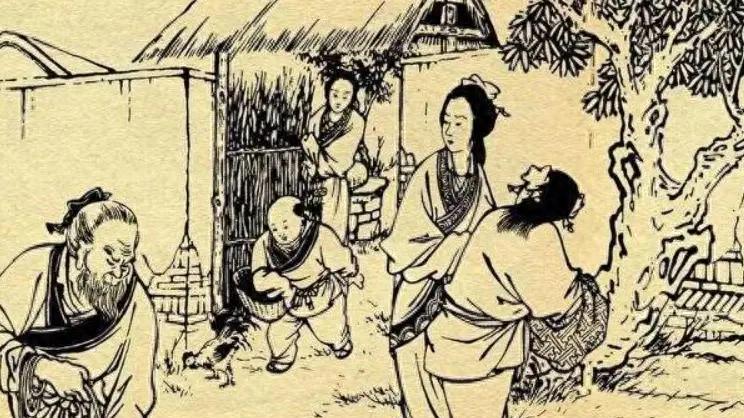绍兴府西郭门外有条杀猪巷,青石板路常年浸着血水,两厢皆是肉铺。其中金家肉案最是老字号,门前悬着块"一刀准"的榆木招牌,风吹日晒已显斑驳。
金大川年过五旬,生得豹头环眼,祖传的斩骨刀使得出神入化。那刀长二尺八寸,刀背厚如铜钱,刀刃却薄似蝉翼,斫肉不沾腥,剁骨不留痕。最奇的是刀身暗纹如血丝缠绕,每逢朔望便隐隐发烫,金大川只当是祖上积德,得了柄神兵。
乾隆四十五年端阳,巷口来了个碧眼虬髯的波斯商人,头戴雪白缠头,身披金线袷袢。他在金家肉铺前驻足良久,忽然指着案上斩骨刀道:"这刀卖否?"
金大川正剁着猪蹄,头也不抬:"客官说笑,屠夫卖刀如同将军卖剑。"那波斯人却从袖中排出五十两雪花银:"这个数如何?"
刀光一顿。金大川抬头细看,见那银子成色十足,够买十把新刀。他抹了抹油手,试探道:"客官莫非识得此刀来历?"波斯人笑而不答,只将银锭往前推了推。
"五十两是玩笑话。"金大川突然将刀收回案下,"若要买,须得重价。"波斯人竟不恼,反而眼睛一亮:"五百两可够?"说着解下腰间皮囊,倒出十枚金光灿灿的波斯金币。
围观者哗然。隔壁茶肆的王掌柜凑过来低语:"老金,这胡商莫不是疯了?"金大川盯着金币上陌生的异国文字,喉结滚动。他祖上三代用这刀,从未听说有甚奇异,怎值这天价?
"容我想想。"他最终收起金币,却说刀要再用三日才交割。波斯人也不催促,只叮嘱道:"刀需日日饮血,切莫闲置。"言罢深施一礼离去。

当夜金大川翻来覆去睡不着,子时披衣起身,就着油灯细看斩骨刀。刀身血纹在灯下竟似活物般蠕动,惊得他险些脱手。忽听院外竹梆声响,有个沙哑声音唱道:"慧眼识得尘中宝,愚人空握山里珍..."
金大川推门望去,见个独眼道人负着青布幡子蹒跚而过,幡上写着"一目了然"。他心中一动,忙唤住道人:"仙长可会鉴宝?"
道人那只完好的眼睛在月光下泛着青荧:"施主眉间聚煞,可是得了横财却生疑虑?"金大川大惊,遂引道人入内,奉上斩骨刀。
道人以指弹刀,其声如磬。又取朱砂在刀身画了道符,符箓竟渐渐渗入血纹。"果然如此!"道人叹道,"此刀内藏血髓玉,乃百年蜈精借血气养成的异宝。那胡商必是识货之人。"
金大川急问究竟。道人解释:"蜈蚣百年成精,需寻铁器寄身。屠刀日日见血,最合它修行。待吸足万牲精血,便能凝玉成珠,佩之可避百毒。看这血纹走向,再养三年便成大器。"
"五百两卖亏了!"金大川捶胸顿足。道人却冷笑:"贪心不足蛇吞象。血髓玉乃凶物,强取必遭反噬。那胡商分明懂行,才要连刀买走。依贫道看..."话未说完,金大川已摸出块碎银塞过去:"仙长指点个催熟的法子?"
道人独眼眯起:"每日以黑狗血浇灌,辅以沉檀香供奉。只是..."他压低声音,"蜈蚣饿极会噬主,施主好自为之。"说罢拂袖而去,青布幡子在夜风中猎猎作响。
次日金大川谎称刀被偷了,闭门谢客。他按道人所说,杀黑狗取血淋刀,又买来上等沉香日夜供奉。那刀起初嗡鸣不止,七日后竟安静下来,血纹愈发鲜艳,宛如珊瑚。
一个月过去,金大川瘦了一圈,眼窝深陷。这日他正焚香,忽见刀身血纹聚成蜈蚣形状,张牙舞爪似要破铁而出。吓得他连退三步,却听"铮"的一声,刀自己从案上跳起,直直插进房梁!
当晚金大川发了高热,梦见条赤红蜈蚣盘在胸口。惊醒时发现刀好端端摆在香案上,刀柄却沾着新鲜血迹。他强撑病体查看,院中黑狗皆被开膛破肚——那畜生竟自己觅食去了!
转眼到了交割日。波斯商人如约而至,见金大川面色青灰,不由蹙眉:"阁下可曾动过此刀?"金大川心虚,只推说染了风寒。当商人验看斩骨刀时,突然变色:"血纹僵死,灵性全无!你可是停了宰牲?"
原来金大川为催熟血髓玉,月余不曾用刀。那蜈蚣精断了血食,反噬自身精元,如今玉毁蜈亡。波斯商人顿足长叹:"明珠暗投!明珠暗投!"竟连金币也不要了,转身便走。
金大川怎肯罢休?抡起斩骨刀劈向院中石磨。"当"的一声,石磨裂为两半,刀身也断成三截。只见刀柄空腔里蜷着条三尺长的赤蜈蚣,通体晶莹如红玉,却已僵死多时。蜈蚣口中有颗鸽卵大的珠子,此刻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血色,最终变得灰白如砾。
"晚了三日..."金大川瘫坐在地,忽觉心口剧痛。解开衣襟一看,胸前赫然浮现出蜈蚣状的红痕,与当初刀上血纹一模一样。此时门外传来道人沙哑的笑声:"血债血偿,贪字头上一把刀哟!"
半年后,杀猪巷来了新肉铺。有人曾在破庙看见金大川,他蜷在草堆里不停抓挠胸口,地上扔着把断刀。问及波斯商人,茶肆王掌柜说那日分明看见商人化作缕青烟钻进了断刀裂缝,哪有什么胡商?根本就是刀中蜈精幻化的!
至于血髓玉,有人说被游方道人收走了,也有人说随金大川埋进了乱葬岗。唯有一点确凿:金家肉铺的榆木招牌,后来被王掌柜劈了当柴烧,火焰竟是诡异的青红色,还带着股腥甜血气,三日不散。
【后记】此乃丙申年余客居绍兴所闻。市井愚夫,多见利忘害;世间异宝,多有德者居之。强求不得,反遭其咎,可不慎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