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女性,西方为何偏爱用绘画,东方喜好用小说?
东西方在解读女性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在载体上表现女性时,西方人偏爱用绘画,重画轻文;东方人喜欢用小说,重文轻画。在审美意识形态中,东西方形成了不同的艺术态度,采取了不同的艺术方法,且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西方人开放,勿庸置疑,在食色性上是持“任性”态度的,他们对于性主题没有过多的禁忌,视若饮水,渴者解之,不会上升到道德层面,可是在拿女性说事上却有倾向性、偏爱性,最凸显的是在艺术上,比如偏好以绘画来表现女性,不屑于在小说上大废周章,浪费笔墨。

徜徉于西方的画卷长廊,满目的是女性的人体画,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最具代表人物的有画家鲁本斯《三美神》、安格尔《土耳其浴女》、布格罗《维纳斯的诞生》、雷诺阿《大浴女》、西费尔《裸女》等。他们是擅长用油画解读女性的巨匠,在他们笔下的女人丰乳肥臀,有肉有料,娇艳欲滴,极具官能美感,一个个都象是伊甸乐园里从未开垦的夏娃。颜小四认为,人体画是西方画家最专情、最痴迷的题材,也是人体写实油画独立画坛的招牌,几百年来,西方写实油画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从未动摇过。

而在小说上,拿女性说事的却凤毛麟角,难觅踪影,涉及淫诲的小说屈指可数,唯有一篇《《查泰莱妇人的情人》》算得上是大尺度。虽然放开手脚地去描写,也仅仅是夸张手法,着墨不多,不像中国小说所表现的百般招式,奇淫技巧。其它小说如美国作家亨利•米勒的《情欲之网》、俄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等在色情上描写,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浅尝辄止,且轻描淡写,不太露骨,过于粗线条,如放到中国小说群中简直是小学教材,不屑一顾。

反观中国却迥然不同,大相异趣。中国在食色性上的表现形式比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祖师爷,不过中国是用小说,非绘画,即重文轻画,重器轻雕。中国文人在性方面的态度却敢于发乎情,但并不止乎礼,他们或文或画都是大胆、放纵。然而,艺术表现形式上还是有侧重点,即小说中的性元素甚于绘画。中国绘画没有人体画,只有人物画,直到清朝潘玉良才开人体画之先河。潘玉良的人体画《浴女》,曾在美术界引起极大的轰动,同时也遭致诸多非议,甚至遭受人身攻击,骂潘玉良是:妓女对嫖客的赞歌。社会大众对人体画抱有偏见可见一斑。

以画而论,中国在绘画上还是输人一筹。或许,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中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现与束缚,人文精神崇尚内敛、含蓄,对待“人之大欲”讳莫如深,讲的是非礼勿言,所以,在性方面的观念与行为有所保守,要么羞答答,要么避而不谈。这似乎就是造成中国没有人体画的原因。如果说中国有“人体画”,那么就是春宫图。春宫图还不是写实画,即使在唐代最开放的气候环境下也见不到人体画,也许中国是注重写意画,西方注重写实画。一个讲意境,一个讲形似。

然而,中国擅长于用小说弥补绘画上的短板。明清言情小说多如牛毛,洋洋大观。在拿女性说事上,不仅有小说,而且还有理论专著,可以说,西方人工于实践,东方人工于理论。中国性理论是走在世界前列。早在公元202年前,中国就出现了性方面的理论专著,西汉成书的《素问》、《合阴阳》、《十问》是世界上最早的理论专著。抛开理论专著,单讲小说也是妥妥的学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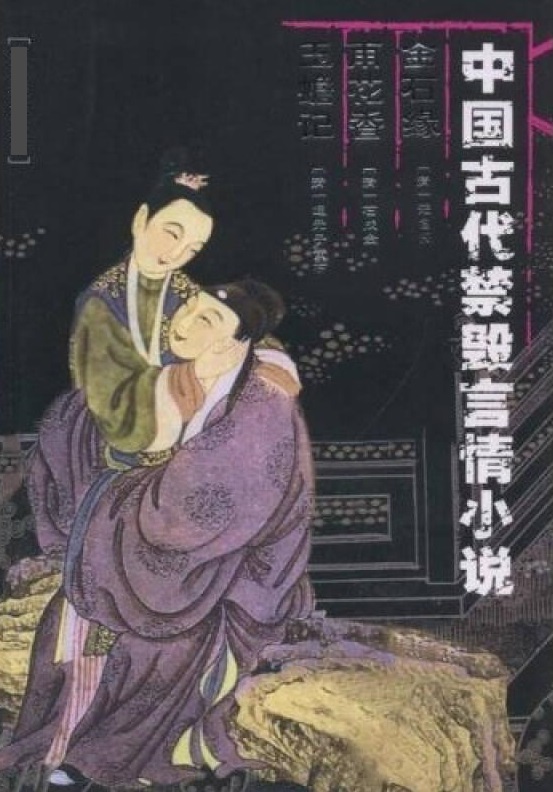
翻开艳情小说看一看,除了人人皆知的《金瓶梅》、《肉蒲团》外,还有许多传字系列:《如意君传》、《灯草和尚传》、《痴婆子传》;史字系列:《浓情快史》、《昭阳趣史》《绣榻野史》等,这些小说描写生动传神,情节活色生香,语言挑逗撩骚,读者观之如身临其境,如直击现场。上述作品极尽宣淫之能事,具有反叛性、反动性,其流毒甚深,破坏力巨大,曾有批评“开人情窦误成童”,所以,这些诲淫诲盗小说遭禁也是情理之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