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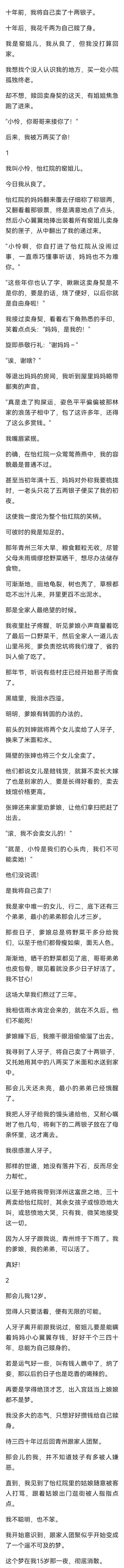


苍白头发的老母亲了,旋即笑开。
那老脸上皱纹倏地就展开了。
她抬起手,裂了好几道口子的大掌摸了摸我的头,一如小时候。
"小怜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花完了娘跟你哥哥弟弟再挣啊!"
到底是没忍住,我的眼圈红了。
这么多年了。
娘还是没变!
她还是很疼我,跟十年前提着扫把赶张婶的她一模一样。
不,还是不一样。
她老了,脸上满是皱纹和斑点,手也粗了许多,背也佝偻了。
唯有目光,一如既往。
我吸了吸鼻子,缓缓点了点头:"嗯,娘,那我先收着。"
见我将碎银子收好,母亲当下便松了口气。"小怜啊,娘,娘想给你梳个头,可以不?"
我愣怔片刻,就瞧着她从包袱里摸出一根有些老旧的竹簪子来。
见我盯着,她有些讪讪着。
"这是你爹给你做的簪子。"
女子十五许嫁,笄而字之,其未许嫁,二十则笄。
我看着铜镜里的自己,发髻散下,又被轻柔的梳起。
老旧的木簪子缓缓穿过。
那些青丝像是过去的十年时光,一点点被母亲拾起,爱护着。
她说:"小怜啊,你要是不想,以后咱就不嫁人啊,你跟娘一道在家,成么?"
她的声音极轻极轻,仿佛我是个易碎的瓷娃娃一般,声音大一点就会裂开。
我迟疑不答。
她抿了抿唇:"要,要不我们全家都搬走?成么?"
"娘听你的,找个不认识我们的地方。"
我缓缓低头。
12岁进怡红院到15岁梳笼。
其实满打满算我在怡红院也不过三年的时光。
可三年的时光,看过听过许多。
怡红院曾经有个头牌姑娘,三十岁为自己赎身,回了老家。
初时她的兄弟姐妹也都是欢迎的。
等那些年积攒的钱财珠宝都被收刮了,立马被卖给了老鳏夫。
那老鳏夫也不珍惜,因着她曾是勾栏里出来的。
一双玉臂千人枕,一抹红唇万人尝,特别没面儿,于是沉溺在赌场,输了,便让那姑娘继续老营生。
后头大概觉得这买卖来钱太慢,又把那姑娘去了青楼。
便是刻薄的妈妈提起这位来,也是一阵唏嘘。
她说:"那些家人跟勾栏里的恩客有啥区别?你花容月貌时,自然是疼惜的,捧在心尖上,有的不惜一掷千金,可等你容颜老去,恨不得一脚踹了,省的碍眼恶心。"
"自然,你的家人看中的不过是你积攒的那些钱财罢了。"
话说到这里,妈妈总会睨大家一眼。
"所以啊,妈妈让你们出这么多钱赎身,其实是在保护你们!"
人心实在难测。
唯有时间才能检验,而我……
需要冒险吗?
当年的我,敢于在夜里奔波好几里寻人牙子。
十年后的我,却胆小如鼠。
大概因着我一直没松口,回去的路上大哥和母亲都十分沉默。
洋州距离青州上千里。
我涂黑了脸,穿着破布衣裳,跟着他们餐风露宿,披星戴月。
一个月后总算到了熟悉的地界。
我,终于回来了!
6
父亲的坟头草很高,几乎都是飞蓬。我一点点的拔掉,听着边上母亲的碎碎念。
"老头啊,你地下有灵,一定要保护我们小怜以后顺顺遂遂,平平安安。"
飞蓬带起了新鲜的泥土,我轻轻摇晃了下,将那泥土抖落,看着地面留下的坑里有蚯蚓翻滚着。
那年大旱初起,便是飞蓬这样曾经被视如野草的,也被我们全家收入背篓里。
那会儿的我们是欢乐的,还比划着谁拔得更多。
真是时移世易啊。
瞧,如今它又是杂草了,被弃置在边上。
等日头上来,烈日暴晒,便活不成了。
我怔怔地看着那草出神,许久才陡然惊醒。深夜的山道上传来了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母亲和大哥也忙好奇扭过身。
旋即就是大喜。
"小怜,是弟弟!"
煤油灯的光在山里实在太微弱。
等走近了,我才看清穿着破烂的几个青年。
最小的那个,也不过那年的我那么高。
那是小弟。
他们到底年岁大了,已经不如小时候那般依恋我。
杵在那儿搓着手干笑。
只有小弟,呜呜呜着扑上来,一把抱住我。
"姐,对不起~"
我的身子僵了僵,还是下意识身后轻拍了拍他的后背。
我们在父亲的坟前跪下,大哥上了三柱香。
"爹,我把妹妹接回来了,您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妹妹的,肯定不会让她被欺负!"说完他满怀期待地看着我。
我将三柱香插上,只低低说了几个字。"爹,我回来看您了!
母亲和大哥表情有些失望。
弟弟们却未有察觉,依次去上了香。
祭拜了父亲,我们便下了山。
大哥依旧推着板车带着母亲,转头瞧见小弟紧紧扯着我,安下心来。
院子还是当年的老样子,院墙破碎了好几处,都被石头和竹篾混着黄土补上了。
大哥将板车推进去,母亲便迫不及待地推开一间屋门。
"小怜啊,这是你的屋,就在娘边上,瞅瞅,缺啥娘给你买!"
小弟忙点头:"对呀姐,我现在也能挣钱了,我可以给你买!"
"姐,我也可以,我挣得比小弟多!"
"就是,小弟现在还是学徒,每个月只有十来文钱!"
"你们,十来文怎么了?也能买很多东西的。"
几人挣得面红耳赤的。
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那会儿大哥总会跟着爹娘一道儿下田干活。
家里喂鸡喂猪煮饭的活儿便落在我们这些小的身上。
瞧着弟弟们听话,每次我都会偷偷在灶头做些好吃的,有时候是贴点野菜饼子,有时候是去河里捞点鱼虾煮汤。
他们每回都能这般争抢。
大哥见我笑了,转身便打了水进来。
"小怜你洗漱一下,早点休息!"
母亲才如梦初醒:"对对对,小怜你这阵子赶路太累了,早点休息。"
我有些触动。
分明母亲这阵子因着颠簸,胃口都不好了,脸色也惨白地厉害。
可现在,她眼里只有我。
我实在是不该,居然怀疑他们的真心。
可便是如此,我更不应该留下。
天未亮。
我悄悄开了一道门缝。
刚要迈出去,差点踩着一人。
仔细一看,赫然是三弟。
7
三弟听到动静迷糊着睁眼,扭头瞧见我,嘿嘿笑了起来。
"姐,你醒啦?大哥让我看着你,不然你要偷偷跑了!"
我:"…"
三弟这傻子!
还跟小时候一般不会说谎。
找个借口都不会。
我气乐了,索性坐在门槛上问他:"那封信谁寄来的?在哪儿呢?"
"你们都不识字,请谁读的信?"
三弟挠挠头:"我不知道谁寄的,大哥说一个商人路过带来的,他识字,读的。"
"那读的时候村里人在吗?"
三弟摇头:"不在。"
我稍稍松了口气。
不是村里或者镇上的人读的就好。
不然自己不在家,娘跟弟弟哥哥都得被指指点点。
可我也不能久留。
居发现我回来了,必然会来探听这些年的事情,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一旦某个人生出了好奇心,即便洋州距离青州千里,即便我在怡红院统共也就两个恩客,依旧会被扒出来。
我问:"大哥是不是让你们轮流看着我?"
三弟讪讪笑了笑:"姐还是跟以前一样聪明!"
我叹了口气。
也只有你才觉得我聪明了。
在怡红院里,我可是天字一号的傻子!
我这母亲和弟弟哥哥着实是有几分无赖在身上的。
可不止日夜守着,我刚想着是不是不吃不喝逼迫他们,娘立马就进屋,也不说话,就是一阵泪。
以至于回家半月有余,我愣是胖了一圈。这日,院坝上来了邻居。
我一个不查被瞧见了,那邻居愣了下,当下便扯开了嗓子。
"哟,阿娟啊,这是你们家大丫吧?"
"啥时候回来的啊?"
我的心当下就是一紧。
然后就听我娘叹了口气:"前阵子回来的,她当年被卖去了大户人家里当奴婢,后头瞧着她年轻老实,收了当妾,可惜怀了孩子月份大了还流了,说是不能生,要卖掉,这不,我们得到消息赶去接了回来,这些年攒的三十两都了进去!
我有些震惊。
娘这是自个儿编的,还是那封信里写的?
可一抬头,就对上那妇人怜悯的目光,我忙又低头。
"小怜啊,你赶紧进屋吧,小产也得做月子的,不然身子好不了!"
我顺势点了点头进屋。
就听我娘叹气着:"我们家小怜太可怜了,那老爷真不是个东西!"
"指定是家宅乱得很,要是我们小怜真生下个男娃儿,我们家还用种田啊?就跟着吃香的喝辣的了,哎,运道实在太差了!"
"现在小怜也不能生,身子还差,洗衣服都洗不了,怕是嫁也嫁不出去了。"
"我这些个儿子啊,都还没娶媳妇,你说说,这可咋办才好啊!"
那妇人跟着一阵安慰,只不过安慰没两句,就麻溜地走了。
我在屋里苦笑。
娘是有点小聪明在身上的。
虽说人总是扒高踩低,可当你卖惨时,人只会说你惨,不会细究你说的惨是不是真的。
娘啊,可你要是这样说,怕是哥哥弟弟的婚事都要被耽误了!
谁家的好姑娘能容得下我这样一个姑子在家啊?
我把担忧跟娘说了,她当下横眉冷眼。"胡说!"
"谁家的好姑娘瞧着你这样的姑子不生怜悯之心啊?"
"要是没有,咱们林家也不敢高攀!"
8
娘说得极是。
我回老家的半年后,便有媒婆上门来提亲了。
给我三弟提的。
那憨傻的,直接一句:"我大哥还没成亲呢,给我提啥亲?我不结,结婚还得花好些彩礼,我没钱!"
气的我娘提起烧火棍追着打了二里地。
最后在我们逼迫下,三弟不情不愿地结了婚。
他媳妇儿是镇上木匠家的女儿,三弟在木匠家当了五年学徒,如今学成了还在木匠家做活,人老实地过分,但凡有个外来的活计,挣了钱都给他师父说,该分多少,从不贪墨,木匠和他女儿都十分喜欢他,之前问了他,他也是如此说,木匠无法,只得请了媒婆上门来。
彩礼是没有的,不过是打了两条猪腿送去了木匠家。
等结了婚,我才给弟媳递了个金镯子,示意她别声张。
她知道我是大户人家的妾,虽说是被赎回来的,可到底锦衣玉食了一阵日子,有些金镯子也是正常,也就没吱声。
隔年三弟媳给家里添丁时,大哥的姻缘也来了。
我在家里住了四年,家里便多了两个三个小侄子。
等着余下两个弟弟也结了婚,我悄悄跟娘说了,开始在家教侄子念书学字。
大嫂和弟媳有些吃惊。
"妹妹(姐姐)居然还会读书识字?"
我淡笑。
被厌弃的那五六年里,实在不知做什么才好,偷偷跟送钱的人表明了想读书,没想到那人真应允了,还特意为我聘了一位西席来。
那先生原本瞧着我年纪大,又是女的,有些不屑。
可到底那些年没啥事情可做,我便拼了命地学,大约真是勤能补拙,五六年的学习,虽说不至于文采斐然,可寻常的四书五经倒是滚瓜烂熟。
因着要读书学字,原本的老屋子便被推倒了重修。
对外我娘极力夸着三个儿媳懂事,拿出了不少体己钱来修屋子。
村里人暗地里笑话她刻薄媳妇,她也不管,依旧每日里笑嘻嘻的安排人修屋子。
回头跟我小声道:"娘这都多大岁数了?还在乎这些?你瞅瞅,我现在孙儿都有三个,个个瞧着都是聪明蛋子,儿媳妇也是孝顺的,儿子还个个都勤奋肯干,还有小怜你……你才是真的给我们家争脸,居然会识字!"
我于家中给侄子开了课。
初时有人登门,鄙夷至极。
"阿娟你真是抠门的很,想给孙子开蒙,去镇上给先生交束修啊,还让小怜来,小怜能认识几个字啊?"
给将整本《论语》给侄子念了下来,这才没了声儿。
再接着,村里便有人领着小儿上门求我教课。
我跟娘他们商量了下,让她跟里长说说,收是可以,但只试着上半个月,若是课上喜欢胡闹的,便要退了,除此之外,女娃儿也可一起听课。
我的课堂渐渐热闹了起来。
因着不收束脩,村里好些女娃儿干完农活都来了。
我娘说,女娃儿若是能读书识字,说亲的时候就能被高看几分。
她还说,我要有空,多教教她们《女则》。
我回以微笑: "娘,女则我也没学过啊!"
9
平静祥和的日子转眼便又过了五六年。我渐渐成了村里的女先生。
人人都尊敬我。
怡红院里的那些事儿好像都离我远去了。
甚至每当洗漱时摸到肚子,我也鲜少再想起那个十月怀胎才生下的孩子。
可日子啊,总归是无常的。
年前一日,有马车驶入了村口,停在了院坝前。
我再度看到了那个无比熟悉的人。
我娘惊呼:"咦?你,你是那个送信的人?"
真巧!
我有些释然。
旋即微微福身行礼:"周管家,许久未见了。"
当年赠我银票,提醒我如何对付怡红院的妈妈,又特意千里迢迢来我这老家,提醒家人来接我,我欠周管家良多。
又或者是……
我看了看门口,马车里的人,是他吗?旋即又自嘲。
多大的脸啊!
周管家冲着众人笑了笑,又看向我:"能否移步说话?"
我自然是应允的。
有些事情,即便又一个十年即将过去,我依旧想追寻答案。
那一年,如此普通的我,为何会入了他的青眼?
又为什么,生了孩子之后他便厌弃了我。
总要有了答案,才能真的跟过去割舍。
显然,答案是残酷的。
河边,周管家将一位富贵的妇人从马车上缓缓扶下。
我扫视一圈,发现村里许多人都在远处围观着,他们议论纷纷。
我微微惊讶,回过神后还是缓缓福了福身。
"我是俊儿的母亲。"
即便有了猜测,当听到她的身份,我还是微微有些吃惊。
所以,这是来棒打鸳鸯了吗?
不!
他都厌弃我十几年了,哪里来的鸳鸯?
我听到自己近乎沙哑的声音。
"奴婢见过老夫人!"
那妇人浅笑了下:"若是我那儿媳如你这般安分守己,当年我便不用这般千里迢迢将你送回来了!
见我疑惑,她苦笑了下。
"那年我听闻俊儿包下了怡红院的风尘女子,甚为震惊,当下便派人去了小院,令我意外的是,我那贴身丫鬟回来却说,你居然在院子里种菜。"
我没吱声,只抿了抿唇。
"我那会儿便知,你与勾栏里那些只会谄媚逢迎的人不一样。"
"后来我便让人去怡红院调查了一下你的身世,发现了你未曾出的家书。
我的心一紧,旋即又释然。
是啊,不然他们如何能顺利找到我这老家,寻到我母亲和哥哥?
妇人转身:"林小怜,当年俊儿娶妻,我恐怕我那儿媳妇会视你如眼中钉肉中刺,只得将你安排回距离洋州千里之外的青州。我以为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可焕儿,他如今已十六了,也不知是谁在他耳边吹了风,非要来寻你!"
焕儿?
是,我那被抱走的孩子吗?
我内心一紧。
就听妇人缓缓开口:"焕儿自小便聪颖,六岁开蒙,十岁便为童生,十三已经是秀才,如今十六,眼见着便要参加会试成为举人,我……"
她深吸了口气。
"我不能让他寻到你!"
"纵然你如今已经是女先生,可俊儿那些酒肉朋友都知晓你。"
见我微微皱眉,她解释:"当年他之所以看上你,全因他们在酒楼的一场赌局。"
"赌,赌局?"
我身子微颤。
旋即苦笑。
是啊!
我既不是倾国倾城,又无出色才艺。
如何能让他在怡红院一眼便看中我?
原来,曾经的幸运,不过是一场赌局么?
妇人见我这般,又叹了口气,旋即看了眼周管家。
后者会意,低着头小声说着:"那日公子与五六好友相约惠丰楼,吃了好些酒,酒劲上头便赌了起来,恰好您打街边路过,跟在怡红院头牌身后,他们便以你作赌,输了,便要与你生个孩子。"
10
"荒唐!"
我笑了起来。
"怎会如此荒唐?"
居然拿生孩子作赌注?!
妇人叹了口气:"是啊,俊儿历来如此荒唐!"
她苦笑着:"可焕儿不一样。"
"林小怜。"
她认真的盯着我。
"父母之爱子,便为之计深远。"
"虽说焕儿你从未抚育过一日,可到底是你怀胎十月生下的。"
"你就当是可怜可怜这个孩子吧。"
说着她的眼神凌厉了起来。
猛地将裙摆拂开,跪了下去。
"便是你说我携恩求报也好,仗势欺人也罢。"
"林小怜,我的焕儿不能有个风尘女子的娘!"
"他至情至性,寻到你一定会将你带回去的。"
"我瞒不住你的身份,不能让你毁了他的前程。"
"试问:哪个举人能有个那样身份的娘?"
我的身子摇晃了下。
"所以,您这次来,是要我躲远点?"
"再次背井离乡?"
妇人摇头。
"不,我想请你赴死!"
"只有你死了,那孩子才会彻底死心。"
我愕然,许久才轻笑了声。
"凭什么?就为了一个不曾谋面的孩子?"
周管家将妇人扶了起来,小声道:"也可以为了您的母亲您的哥哥弟弟弟媳,还有侄子。"
我愕然看向他。
"你们敢?!!"
妇人叹气:"不到万不得已,我们自然是不会的。"
我抬头望着湛蓝的天。
"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吗?"
妇人语气坚定:"为了焕儿,只有绝路。"
说着她又朝周管家看了眼,周管家从家丁手里接过一个匣子,从里面取出了一卷卷书画来。
"这是大少爷的笔墨,您且看看吧。"
我摆手,淡漠地看着妇人。
"其实,你不告诉我赌局的真相,或许更好。"
"你只需跟我说,有友人知道我的身份,让我对他还抱有一丝幻想,这样不是更好吗?"
妇人摇头:"他不配,让你为他赴死!"
我怔了怔,苦笑了起来。
"能让我过完年吗?"
妇人颔首:"可以,年后我们来接你上路。"
马车浩浩荡荡地离开了。
可在村里却留下了谈资。
有好事的婶子来问我来人是谁,为何要跪下。
不得已,我只得编了谎言。
说那年孩子其实没死,如今孩子学有所成,想寻我回去,我即将母凭子贵,因舍不得家人,我年后才去享福。
母亲和哥哥都愕然。
我苦笑: "我没骗你们,我真的生过一个孩子。"
"他即将会试,过了就能成为举人。"
"我其实不大乐意去的,她说当年逼我离开那孩子憎恶她了,亲自来请我,孩子估摸着才能原谅她,还下跪求我。"
众人才恍然。
有人离去时,到底是没忍住嫉妒,说了声:"真是走了狗屎运啊,居然能母凭子贵!"
"可不嘛,有个举人老爷的外孙,老林家怕是要兴旺喽!"
母亲将我拉进了堂屋,仔细观察了我:"小怜,这是真的吗?"
我笑了。
"娘!那主家是好的,当年我赎身的钱都是他们拿的,花用了十来年,如今还剩下两千多两呢。"
生怕她不信,我拉着她回屋翻出了那些银票来。
这才叹了口气:"娘,您知道我那身份的,原本我想着回去怕也是不能登堂入室,只会困在孤僻的院子里,倒不如在村里教书呢,可她当年如此帮我,又给我下跪了,无论如何都要我回去,说是那孩子发现了我的存在,只有我去才能安心考试,我实在无法。"
怡红院里教的骗术到底是用在了家人身上。
谎话七分真三分假,便是母亲和哥哥也寻不出破绽来。
林家过了个红红火火的好年。
村里人知道我这女先生为了儿子要离开,纷纷惋惜。
年后离开前,我将银票留给了母亲他们。
来接我的周管家还奉上了一份万两银票,我忙提醒母亲他们财不露白,又笑着道:"娘,哥,弟弟,你们一定要让侄子侄女读书,等读出了出息,再去洋州寻我,可好?"
众人纷纷点头。
上了马车,我对上周管家的视线。
"那万两白银,算是我的卖命钱?"
周管家眼神躲闪。
"说吧,要我如何死?"
周管家抿唇:"洋州与悠州交界处有一青俊山,山峰陡峭!"
"我明白了!"
周管家的声音有些哽咽。
"其实老夫人想了许多折中的法子,想让您假死的,可大少爷实在太聪慧……"
"我懂!"
我叹了口气,重新摸出那些字画来,指尖一点点地摩着:"挺好的。"
二十年前,我为了家人卖了身。
二十年后,我为了家人又卖了命。
不过是宿命罢了!
我沉声:"周管家,我死后,这些字画请您交给他。"
戏得做全一些。
总不能让那未曾谋面的孩子因此荒废了学业。
这些天,我在这字画上写下了许多批注,也写下了期许,希望他金榜题名,蟾宫折桂。
自然,做这些也是为了让家人相信,我出事真的只是意外。
周管家却苦笑:"怕是不能了。"
我愕然看向他。
周管家扯起嘴角。
"如果我的死,能让周家出个进士,乃至状元,实在是一笔好买卖,不是么?"
我怔了怔。
这周管家怕是家生子了。
"周家是商贾之家,果然周管家您的账算的好!"
"谢夫人夸赞!"
======
三日后,马车在青俊山倾覆,滚落悬崖。
半月后,周青焕连同周家人一道在悬崖底发现了林小怜与周管家的尸体。
消息传至林家,全家悲恸。
半年后,周青焕中举。
隔年春,殿试金榜第二甲第12名。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