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秀于群言必毁之。原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山东军管区司令王耀武被俘后进了战犯管理所,依然有“同学”向管理人员举报,说王耀武这个人不老实,所谓的积极改造都是伪装。
在战犯管理所,所有战犯都被称为学员,学员之间互称同学,但战犯管理所的同学可不同于黄埔同学,在战场上还要留几分情面,而在功德林或其他战犯管理所、看守所,同学们则似乎更乐意互相举报,比如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还为此发生过冲突。
王耀武是正规军人,在抗战中立有赫赫战功,所以不管是在山东还是北京,他被俘后的日子过得都不错,但就是这个“不错”,让惯于内斗的被俘蒋军将领有些羡慕嫉妒恨,当面笑呵呵,背后告黑状,更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于是王耀武差点“倒霉”——沈醉在回忆录中说有很多人举报(诬告)王耀武,虽然沈醉没有明确指出举报者的姓名,但是他却在字里行间露出了马脚:不管是举报还是诬告,那些举报者中,极有可能有沈醉,而另一个举报者,应该也是个少将特务。

沈醉这段回忆才符合史实,我们看《特赦1959》,好像王耀武和沈醉很早就进了功德林,事实上他们一开始都分散在各地,1955年和1956年高级战犯大集中时才分别从重庆和山东转到北京,王耀武比沈醉先到,沈醉在1956年国庆后来到北京,王耀武已经是学习委员了。
王耀武在山东期间,跟徐州“剿总”杜聿明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前指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住在一起,文强被送到山东,迎接他的就是王耀武。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在山东潍坊,我们住在一个大村庄的地主家里。我一去,王耀武等在门口迎接,他拉着我的手说:‘哎呀你也来了。’王耀武对这里比较熟悉了,他说:‘分工合作吧,大家可以做什么事情,自己报名。’我就说:‘我会做湖南菜。我报名做湖南菜!’听我这样一说,有个在四川部队当军长的,他报名做四川菜。王耀武说一口山东话,每天起床都说:‘吃糖吃糖(起床起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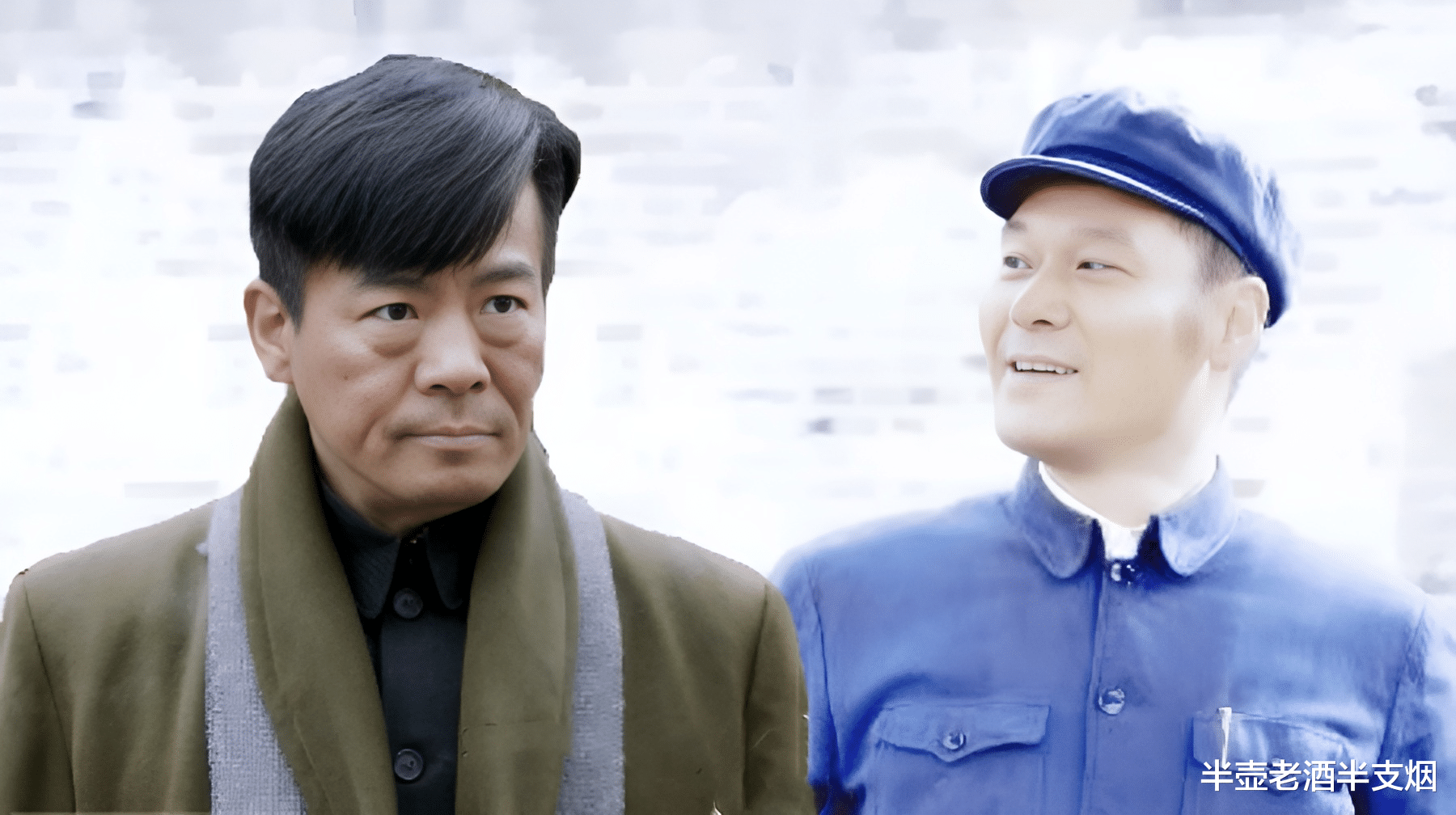
我们需要顺便解释一下,这里的“解放军官”,指的是“被解放(俘虏)的蒋军军官”,就跟“解放战士”不等于“解放军战士”一样。
山东解放军官训练团中的高级将领被集中到北京,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王陵基、宋希濂等人也先后从重庆转运北京,这下子功德林热闹了:黄埔系、杂牌军、“牛字号(特务)”汇聚一堂,勾心斗角开始了,算旧账的当然也比比皆是,比如杨伯涛和黄维,韩浚(叶立三的历史原型)和李仙洲,张淦(蔡守元的历史原型)和马励武,杜聿明和宋希濂,都有诉不清的恩恩怨怨。
黄百韬临死前对李以劻(时任“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视察官,1960年特赦)说的那番话可谓入木三分:“古人说,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是办不到的。”

沈醉回忆:“由于王耀武事事谨慎,从不乱反映问题或欺上压下,找不到推翻他的毛病。最后,还是有人不断向所领导和管理人员反映,说他白天装得老老实实,夜晚睡着做梦时,经常咬牙切齿地痛骂什么……(脏字,略去)等,一定是白天抑在胸间的愤懑,在夜间控制不住而发泄出来,说他是外装老实,内心仇恨共产党,不是表里如一。”
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王耀武说梦话,能听到并会去打小报告的可能是谁?当然是同在一个小组、住在一个宿舍的“同学”。
沈醉不但清楚描述了王耀武如何在梦中骂人,还知道接到举报的管理人员如何回复的:“一是从来没有发现王耀武弄虚作假欺骗领导;二是始终如一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没有理由撤换他;三是夜间说梦话,并不能说明他骂人是骂共产党,也可能是种生理上的习惯。”
读者诸君可以试想一下:什么人能听到管理员对举报的答复?沈醉把答复写得如此清楚,是不是无意间露出了马脚?

各绥靖区、绥署、战区的情报处基本都是由军统(保密局)特务组成(胡宗南的部队和部分桂系等杂牌部队除外),董益三的少将特务身份一直没有改变。
董益三是王耀武、沈醉所在第二小组的组长,但在很多时候,又得受学习委员领导,沈醉一开始也有点奇怪:“吃过早饭之后,他忽然回到组内来传达当天上午的学习内容。我很奇怪,他和我们一样是第二组的成员,怎么由他传达学习项目?下午我就打听到了,原来学习小组长之上还有一个学习委员,直接由管理所负责人领导,王耀武就是学习委员。但他平日还是在小组内与我们一道学习,每天学习完毕,由他召集各学习组长开一次碰头会,各组长向他汇报学习情况,由他汇集以后去向管理所的领导汇报。”
王耀武“管”着所有的学习小组组长,可谓“位高权重”,但他对沈醉确实客客气气,而沈醉有些不太愿意提起的小组长董益三,则“官派”十足。沈醉拿出一整条大前门送给董益三,结果人家只拿了一支,剩下的全都“丢还”:“我问汤尧,为什么老董宁愿去拾烟头而不要我的烟?他用轻蔑的口吻回我一句:人家是学习组长,你送烟给他,不是想拉关系吗?听了他这句话,我才想起第一天和董见面时,他就一再向我表示:‘我们重新交朋友。’我开始还有点不理解,经汤这一说才恍然大悟。”

邱行湘(被俘前为青年军整编第二〇六师少将师长兼任洛阳警备司令,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外甥黄济人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也记录了此事,而且他记录的董益三“告密”不止一次:“叛徒的名号曾经落在董益三头上,功德林期间,除了沈醉进厕所冲洗内裤是他告的状,黄维用某书撕作手纸也是他告的状。董益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一次学习会上,他公开宣称:‘告状是我争取进步的手段。龙有龙路,虾有虾路。杜聿明可以靠杨振宁加分,郑庭笈可以靠傅作义吃糖,杨伯涛可以靠说大话卖乖,邱行湘可以靠卖苦力受宠,我靠什么?无依无靠,只好打点小报告。’”
特务不愧是特务,即使进了功德林,依然保持着“职业习惯”,王耀武这个“聪明的老实人”跟沈醉和董益三分在一个小组,也应该算是不幸中的不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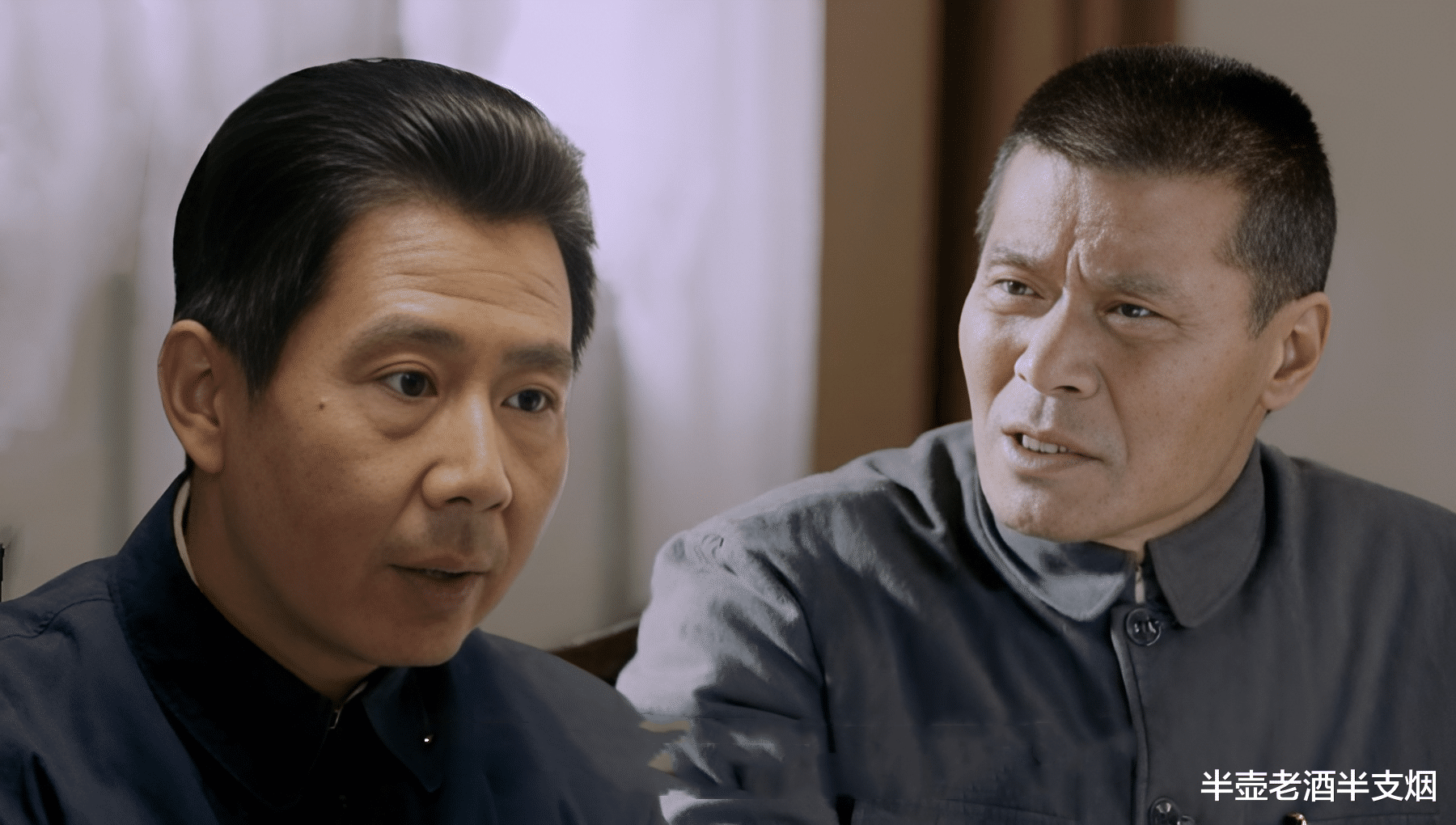
笔者一直认为,像王耀武、宋希濂、杜聿明那样在抗战中立有大功的战犯,吃得好点、出去得早点,都很正常,而沈醉和董益三这两个军统将军级特务,在1960年第二批特赦,却肯定是有深层次原因的:第二批特赦的时候,沈醉的“起义将领”身份还没有被确认,他是1980年才被认定为起义将领的,董益三更是跟起义投诚沾不上边,他们能比其他人早几年甚至十几年出去,您说是为了什么?您对蒋军将领之间的这种“感情”,会作何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