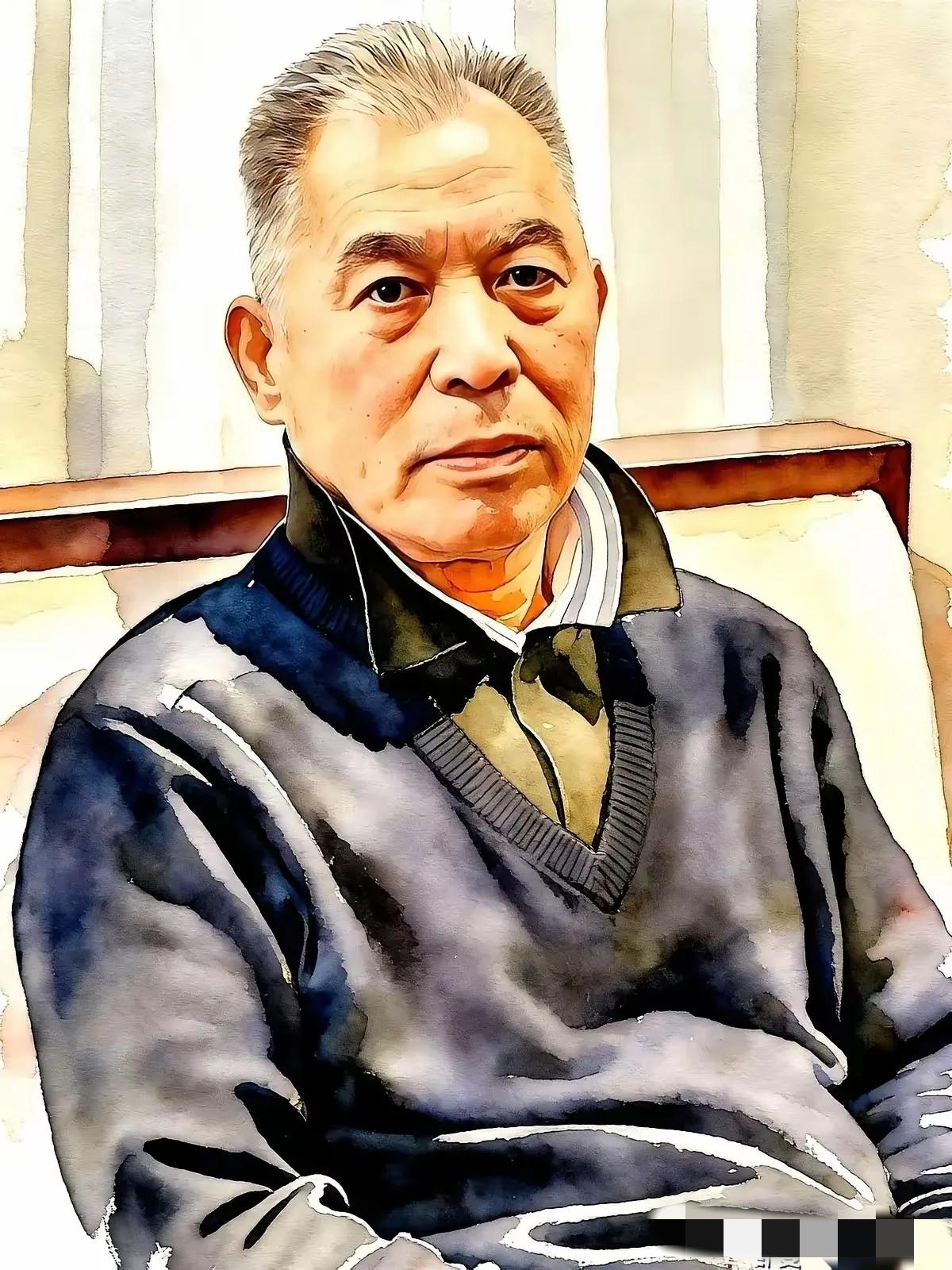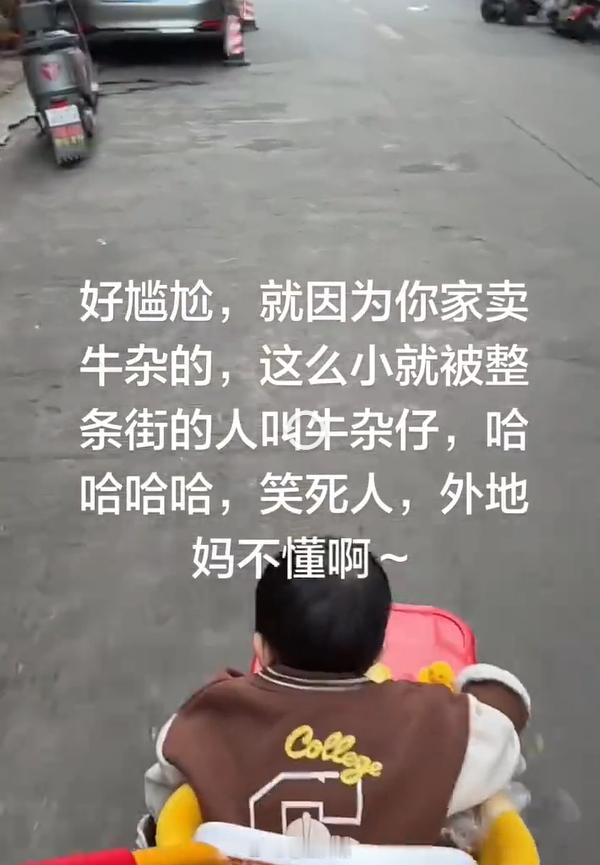很久以前我们村有个光棍,我记事的时候他大约40多岁,和他失明的母亲相依为命。 大伙都喊他“老根”,没人知道他的大名。他家在村东头,是间矮矮的土坯房,房顶铺着茅草,下雨时总漏雨,老根就用塑料布在屋里接水。他没正经工作,平时靠帮人耕地、挑粪、打零工过日子,挣的钱刚够娘俩糊口,可从没见他抱怨过。 记事起,村东头那间土坯房就没断过动静——不是茅草屋顶漏雨的滴答声,就是老根挪着塑料桶接水的窸窣声。 屋里总飘着股潮湿的土腥味,混着灶台上熬粥的糊香,那是老根和他失明的娘唯一的味道。 大伙都喊他“老根”,没人问过本名;四十多岁的光棍汉,日子像屋顶的茅草,风一吹就晃悠,却愣是没散架。 七八岁那年夏天,我蹲在他家门口看蚂蚁搬家,他背着半篓猪草回来,裤脚沾着泥,却笑着递我颗糖——那糖纸皱巴巴的,像是揣了很久。 我剥开糖塞嘴里,甜得眯起眼,盯着屋里接水的塑料布问:“老根叔,漏雨不烦吗?” 他正给娘擦手的动作顿了顿,没直接答,只把娘的手往自己胳膊上靠了靠:“你奶奶眼睛看不见,我得让她摸着稳当。” 后来才发现,他打零工回来再晚,灶上总温着一碗粥;帮人耕地累得直不起腰,路过代销店也会买块最便宜的糕,揣回家塞给娘——那是他一天里最轻快的时刻,比屋顶不漏雨还让他踏实。 有回下暴雨,我看见他搬着梯子上房,塑料布被风吹得哗哗响,他像只老蜘蛛趴在屋顶,娘在屋里喊:“根啊,慢点,娘不渴。” 他应着“知道咧”,声音被雨砸得碎,却比任何时候都清楚。 村里人常说他命苦,光棍带着瞎眼娘,日子熬不出头;可我见过他娘摸着他胳膊笑的时候,那皱纹里的光,比谁家的电灯都亮堂——原来苦不苦,不是旁人说了算的。 他从不抱怨,不是没知觉,是娘的手还在他胳膊上搭着;是每天清晨娘摸索着给他递鞋时,那句“慢点走”;是这些细碎的暖,把日子的窟窿都堵上了——就像他用塑料布堵屋顶的漏雨,笨是笨了点,却管用。 日子就那么过着,挣的钱刚够娘俩糊口,却没断过热乎饭;后来他娘走了,老根也搬离了村子,可那间土坯房的茅草屋顶,总在我梦里飘着粥香。 现在想想,哪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英雄?能把日子里的漏雨一点点接住,把身边人的冷一点点焐热,就已是顶了不起的事——你说呢? 那年漏雨的塑料布早烂成了碎片,可老根叔擦娘手时的动作,比任何屋顶都结实,一晃神,就暖了整个童年。
我父母都八十多岁了,我也五十多岁,现在我都不愿意去看他们,原因是什么呢那天
【13评论】【9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