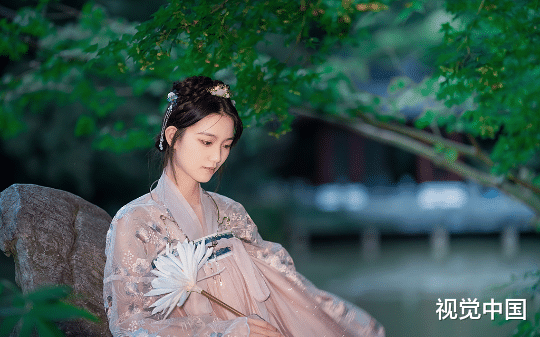简介:
十年戎马生涯,在被风沙侵蚀的城墙和一望不到边际的黄沙中,萧正峰偶尔会想起,那个站在粉润的桃花树下,身段曼妙捏着一枝桃花的姑娘。
此时,已经权倾朝野的他,踏过了刀光血影,骑着高头大马,背对着燕京城这十里繁华,低头望着地上跪着的形色狼狈的妇人。
他问:“夫人,若是一切能够重来,你可会选择今日今时的路?”
顾烟抬眸,轻笑了下。
若有来世,她又怎么会为他人做嫁衣裳?
-
顾烟重生了,这个时候,她那背弃了她的侄子还是青葱少年,以后权倾朝野的平西侯还只是三品武将。
他痴痴地看着她,脸都是红的。

精选片段:
燕京城最繁华的东十四街道上,一座宏伟的宅院。一个阔气的朱红色大门,两个昂然挺首的大狮子。
阿烟望着这朱红色的大门上尚还算新鲜的喜色,立在门前一座昂然挺首的大狮子旁,安静地等待在那里。
寒风萧瑟,路上并没有多少行人。
她低下头,把皴裂的双手藏进打着补丁的袖子里。
实在是太冷了,她身上的衣衫单薄。
抬头看向一旁的守门的小厮,那小厮是一脸的嫌弃和防备。
阿烟笑了下,并没有在意。自从十年前夫君亡去,她因了那一张拥有绝世容颜的脸蛋而屡屡惹来麻烦,以至于一刀下去自毁容貌后,这种眼光,她见多了。
她仰起脸,望向那朱红色的大门。
这是她夫君侄子沈越的府邸,他殿试当了探花,金榜题名,又被当朝九公主榜下捉婿,就此当了驸马,不知道羡煞多少人也。
可惜他这般风光后,就再也没有回去看过她一眼。
今年收成并不好,出去做点零碎活儿也没人要,这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她只好千里跋涉来到这里,投奔她的侄子。
十年的时间,她供养这个侄子读书,如今他算是飞黄腾达了,也没指望他能如何孝敬自己这个婶子,不过是求着能有一个照应罢了。
可是她已经等在这里半天的功夫了。
就在阿烟轻轻跺着脚以抵御寒冷的时候,那大门终于开了,一个婆子探头出来,眯着一双探究的眼睛望着阿烟。
这个婆子,阿烟是认识的,那是侄子的母亲身边的第一心腹人儿。
她怎么在这里?
阿烟笑了下,想着这侄子终究是和那自小分离将他抛弃的母亲相认了吧?
那婆子也认出了阿烟,一双势力的眼睛尖酸地望着阿烟,笑道:“哎呦,这不是二少奶奶么,怎么如今落到这个天地,这脸怎么成了这个样子。要说起来,满燕京城里,如今谁还能认出这是昔日那个晋江侯府的二少奶奶啊!”
阿烟并没在意,淡淡地问道:“越儿还没回来吗?”
婆子跨出大门,居高临下地站在台阶上:“你还是别来了,虽说你养了少爷那么些年,可是如今我们夫人过来认了儿子,今日少爷是不敢见你了。”
阿烟挑眉,轻轻问道:“为何不敢见我?我是他的婶母,难不成他认了亲娘,就可以不认养了他十年供他读书的婶母了?”
婆子冷哼一声:“如今这府里是住着公主的,堂堂驸马府,不是一般的门第,自然不是什么叫花子丑八怪都能进去的。”
阿烟仰起脸:“这就是沈越的意思吧?”
婆子连正眼都懒得看阿烟了:“我说二少奶奶,您还是赶紧走吧,您如今这个样子,进了咱们这府门,要是传出去,实在是丢人现眼。别说吓坏了那娇贵的公主,便是我这老婆子见了你这脸,都怕晚上做噩梦呢!”
阿烟沉默了许久,最后终于点头:“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
说完这个,她转身,昂头离开,临走之前,扔下最后一句:“告诉沈越,今生今世,我顾烟绝对不会再踏上他的门槛半步。”
婆子站在门槛上,见那昔日风光娇美的二少奶奶穿着破旧补丁的麻袄儿,就这么挺着腰杆一步步走了,走起来腰臀微摆,如同杨柳摇曳在风中,竟然还隐约有昔日的风采。
她不由得“呸”出一声:“小贱蹄子,都这副德行了,还浪给谁看!”
阿烟知道自己的脸难免引起别人的惊怕,于是干脆低着头,抄小道顺着这个大街走。
她这一路过来,其实是半乞讨走过来的。
原想着投奔沈越,结果他是不想见自己了,一时她望着这冬日里依旧透着繁华气息的燕京城,怔怔看着那挑起的酒旗子,竟然不知道自己该去往哪里。
其实燕京城里,昔日的闺中好友或者其他相知,倒是认识一些,如今她便是厚着脸皮用昔日交情来求得一个收留,也未尝不可。
可是顾烟是何许人也,她自然不会去打这种秋风。
今日她便是低到了尘埃里,那她也要在尘埃里自己爬。
她还有手有脚,也有一张嘴,便是揽不来零活挣不来银子,她可以低下头去祈求陌生人的怜悯。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青衣的小厮鬼鬼祟祟地出现了,怀里捂着一包东西,他追上了阿烟后,忙看看四周,小心翼翼地道:“今日少爷实在是不好见你,不过他知道你今日的难处,便说让我偷偷地把这个交给你。”
说着,他把怀里的一包东西往阿烟手里一塞,又硬着头皮道:“少爷还说,你以后就不要再到府门前来了,外人看到不好!”
说完这个,他头也不回地溜走了。
阿烟低头看过去,却见手里的是一个破旧的青皮包袱,那还是昔日他上京来赶考时,自己给他做的,当时里面是细细地包了各样小吃,还有自己辛苦多年积攒的银子。
如今打开这往昔的青皮包袱,却见里面是一件棉衣,还有十两银子。
阿烟笑了下,心道这就是她十年辛苦换来的,一件棉衣,十两银子。
该说沈越这孩子是个贴心的吧,知道她冷,知道她穷,也知道她饿。
阿烟没有扔掉这些东西,而是将那棉衣裹在身上,又将那十两银子塞到自己的包袱里了。
那棉衣是个锦缎的,和她如今这一身破旧的麻衣很不相称,甚至还是有几分滑稽,不过她如今不过是半乞讨的落魄妇人罢了,也就不讲究这些了。
正走着时,便闻到一股浓郁的肉香飘来,伴随着那股肉香,阿烟仿佛看到了肥而不腻的猪手炖在色泽浓郁的汤汁中,冒着热气,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
她麻木地转首,看向香味飘来的院子,却见那里有袅烟升起,隐约仿佛还听到小孩子的笑闹声。
想来那院子里,一定是一个温暖舒适,充满了欢笑和肉香的所在吧。
阿烟怔怔地望着那袅烟,忽而想到,自己名字中是占了一个烟字的,是不是也就如同这烟雾一般,转瞬即逝?
正想着间,忽而听到后面马蹄声响,她忙要躲到一旁,谁知道那骏马来势汹汹,就这么险些踩到她,她一个趔趄,狼狈地摔倒在地上了。
腊月里的燕京城,青石板的地面混合着些许被冻得僵硬的泥土,她这一摔,只觉得自己骨头都散架了。
这十年操劳,她没日没夜地忙碌,做着各种活计,虽则其实也只有二十六岁,这身子骨其实已经不行了。
她耳边嗡嗡嗡响着,便听到有吆喝声有呵斥声,还有骏马被制服后的嘶鸣声。
最后一个声音在她耳边响起:“这位嬷嬷,你没事吧?”
紧接着就听到另一个声音恭敬地向什么人禀报:“侯爷,无忌刚才窜入了一条巷子,险些撞上了一位老嬷嬷,幸好看起来并无大碍。”
然后呢,一个威严的声音低沉地响起:“过去问问吧,莫要伤了无辜之人。”
阿烟勉强起身,努力地笑了下,摇头道:“我没事的,不过是吓了一下,然后自己跌倒了。”
那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侍卫,此时见她抬头,看到她脸上那道狰狞的疤痕,倒是有些诧异,不过并没有露出什么嫌弃或者惊惧,只是有些疑惑她的年纪,看起来竟然不是自己以为的老嬷嬷吧?
阿烟低下头,知道自己虽然只有二十六岁,可是别人看着,怕都是已经三四十岁了吧。
女人的容貌是最娇艳的花朵,原本需要精心呵护,卖命操劳,她老得快。
而就在她说着这话的时候,那侯爷凌厉的眸子直射过来,一时眸光微动,拧眉淡道:“去把刚才那位老嬷嬷带过来,本侯要亲自问话。”
他的耳力目力一向惊人,堪称过耳不忘过目不忘,纵然是十年前偶尔听到的一点声音,在十年后他依然能够记得。
如果他并没有听错,刚才那个女人的声音,分明是十一年前燕京城里那个左相家的三姑娘——顾烟。
十年前,他还只是一介武将,远没有今日权倾朝野的威势。
那时候的顾家三小姐对于他来说,高不可攀。
不过因缘际会,他见过她的。
于是他眯了下眸子,吩咐道:“请她过来一下。”
他用了一个“请”字。
尽管世人皆知这位位高权重的平西侯一向谦和低调,不过能在他面前,被他用一个“请”字的人,普天之下并没有多少了。
很快,一身狼狈的阿烟就被请到了平西侯的马前,她跪在那里,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并没敢抬头看。
平西侯低首望着面前的女人,头发中已经掺着银丝,打着补丁的麻衣裹着一个锦袄,看起来极为滑稽可笑。
她低着头,他看不到她的脸,却能看到她因为跪在那里而伏在地上的手。
那是一双经历过多年操劳而粗糙不堪的手。
平西侯的喉头有些发热,心里竟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其实他和这个女人并不熟,只是因缘际会下的几面之缘而已。
可是,他也曾默默地关注过这个女人,一直到她嫁为人妇。
在后来的戎马生涯之中,在被风沙侵蚀的城墙和一望不到边际的黄沙中,他偶尔会想起,那个站在粉润的桃花树下,身段曼妙捏着一枝桃花的姑娘。
此时,已经权倾朝野的他,踏过了刀光血影,骑着高头大马,背对着燕京城这十里繁华,低头望着地上跪着的形色狼狈的妇人。
“你——可否抬起头来?”
跪在那里的阿烟其实并不认识眼前的这个平西侯,不过她意识到了什么,于是便抬起了头。
抬头望过去时,一个身穿玄袍的男子,魁梧奇伟,内敛沉稳,就那么威严而矜贵地立在皮毛光亮的骏马上。
他带着高冠,穿着锦袍,一个缀着珠宝的腰封——象征了他尊贵的身份。
平西侯眸间微动,尽管这个女人脸上一道狰狞的伤疤,不过他依然认出来了,这是昔日那个娇美无双的三姑娘。
他喉咙微动,沉吟了片刻,才哑声道:“你是顾家的三姑娘吧,为何出现在这里?”
阿烟抬头凝视着眼前这人,却见他一张脸庞刚毅坚硬,眉如刀裁,眸如寒星,一时她竟记不起,自己认识他吗?
至于他问的问题,自己又该如何作答?
左相顾家的衰败,晋江侯府的陨落,一群人等四散零落,她带着重病的夫君,领着十几岁的侄子,经历了多少磨难,最后她孤身一人,穿着这一身荒谬而可笑的衣着,如同一个老妪一般跪在这里,惶恐地回答着一个位高权重的王侯的问题。
平西侯见她良久不作答,淡淡地命道:“适才本侯治下不严,这才使得惊马冲撞了夫人,如今请夫人随本侯回府,本侯自会请大夫为夫人检查身体。”
************
阿烟被带到了侯府,经大夫诊脉后,并无异样,只是说平日太多操劳,身子亏空得厉害。
此时有侍女奉上了驱寒的热茶,还有侍女提上了食盒,里面是丰盛的饭菜。
这时候的阿烟已经没有了任何矜持。
她饿。
她低着头,吃了起来。
平西侯透过窗棂,静静地凝视着屋子里这个形容憔悴一身狼狈的妇人。
看了许久,一直等到她终于吃饱了,这才走进来。
阿烟见到这平西侯走了进来,忙跪在了地上。
此时此刻,她已经知道,这个人就是那位权倾朝野的平西侯,燕京城里,无人不忌惮。
他的威名远播,以至于当日她在穷乡僻壤的小镇,也曾听到他的大名。
隐约中她也记起,这个人昔年自己也是见过的。
就是在昔日未嫁之时,那个时候他还年轻,只是一个刚刚打了胜仗的武将,不成什么气候,跟在当日的齐王身后,并没几个人会多看几眼。
平西侯望着地上跪着的女人,沉吟片刻,想着该怎么称呼她,最后还是道:“沈夫人。”
阿烟手指头颤动了下,已经很多年没有人这么称呼过她了。
她那病重的夫君去了,临走前留下遗言,要她照顾好他的侄子。
一把刀割下去,她成了一个面目狰狞的妇人,蓬头垢面,灰头土脸,默默地坐着零活供奉着侄子。
人们通常随意呼唤她一声“顾婆子”或者“顾阿婶”。
沈夫人这个词,太过遥远,以至于她几乎忘记了。
平西侯见她如此,忙命她起身,勉强低笑了声:
“夫人不必紧张,本侯虽然素日与你并不相识,可是却和夫人的父亲顾左相有过几面之缘。如今既然夫人落难,本侯冒昧地问一句,夫人如何沦落到这燕京城街头,若是可以,本侯或许能帮夫人一二。”
阿烟听着这话,心中微暖,她也看出,这平西侯倒是一个仁厚之人。
当下她笑了下,低头将自己平生用三句话轻描淡写地说来,最后道:“世事沧桑,万不曾想今日民妇得侯爷救助,感谢侯爷一饭之恩,只可惜,民妇身无长物,无以为报。”
平西侯拧着眉,打量着她道:“夫人,那沈越承受你十年抚养之恩,如今金榜题名,为皇家乘龙快婿,竟然将你拒之门外,实在是忘恩负义之辈。若是夫人愿意,本侯自然向皇上禀明此事,还夫人一个公道。”
阿烟听此,却摇头淡道:
“侯爷,沈越纵然不孝,纵然忘恩负义,可也是人之常情。世间知恩图报者本为少数,是以才能传颂千古。再者民妇十年辛苦将他抚养,原本不是求他知恩图报,而是我家夫君临死嘱咐。今日民妇见他住大宅,封高官,认了母亲,娶了公主,也算是春风得意,民妇也算不负夫君临终所托。”
平西侯越发拧眉:“夫人看着这等忘恩负义之辈飞黄腾达,难道心中不还有怨恨?难道不曾为自己十年付出而后悔?”
阿烟依旧笑,笑得淡漠:“民妇相信,恶人终究有恶报之时,他既我亲手抚养,我却不愿意他因我而毁。世事多变,将来总有一天,他会得到自己应有的报应吧。我顾烟,却只要问心无愧便是了。”
平西侯听此话,从旁静静地望着这个带有狰狞伤疤的女子,削瘦憔悴的她立在那里,竟隐隐有几分恬静淡定的释然。
他轻叹一声,深深地望着她,试探着道:“不知道夫人离开燕京城后,打算前往何处?”
阿烟低头:“无根之萍,随风漂泊罢了,去了哪里,便是哪里。”
平西侯略一沉吟,终于道:“夫人,我府中有东书房,至今无人打理,若是夫人不嫌弃,可否留在府中,为我操持那东书房之事?”
听到这话,阿烟笑了,一笑间眸中仿若有流星划过,灿灿生辉。
她笑望着平西侯,摇头道:“多谢侯爷美意,可是民妇十年为市井妇,如今已经目不识丁,怕是有负侯爷所托。”
平西侯听此,微皱眉,道:“侯府之中还有一跨院,院中一直杂乱不堪,无人管理,若是夫人不觉得折辱,冒昧问一句,可否——”
阿烟已经明白这平西侯的意思,他也是小心翼翼,既不愿伤了自己的自尊体面,又想着能够对自己有所照拂,她眸中泛出感激,不过她还是笑着摇头:
“侯爷,民妇如今一个人在外头习惯了,这侯府里规矩大院子大,怕是住不习惯。”
平西侯听此,坚毅的唇轻轻抿着,就这么望着她。
阿烟却别过脸去,透过雕花窗棂,望向外面的天色,淡道:“如今天色已晚,民妇该离开了。”
平西侯垂下眸子,语音暗哑:“夫人,本侯命人送你出去吧。”
一时阿烟迈出门时,平西侯望着她那虽然穿着极为滑稽,可是依稀能见昔日娇美婀娜的身段,心间微动,轻轻握了握拳,忽而沉声问道:
“夫人,若是一切能够重来,你是否依旧会选择今日今时的路?” 阿烟听到这话,身形顿住,微愣。
今日今时的路,是什么路?
她的人生有许多的岔路口,譬如选择嫁给她的夫君沈从晖,譬如拒绝那些求她为妾的众多男子,譬如选择十年寒窗供养沈越苦读。
无论是哪一个岔路口,她但凡选择另一条路,都不会走到今日的地步。
她怔怔站在那里,闭眸良久后,再次睁开眼,落日的余晖映到了她的眼眸中。
曾经清澈的眼眸中,都是余晖的昏红。
她唇边绽开一个凄凉而无奈的笑容,缓慢而决绝地道:“若有来世,我自然再也不会走到今日这个地步。”
纵然不悔今生,可是若有来世,她却是再也不要为他人做嫁衣裳,再也不要付出所有只为了一个忘恩负义之辈,再也不要去嫁给那个临终前将一个沉重的担子放到自己肩上的男人,再也不要十年的孤身守候,到头来看到的只是一个飘落在风中的可笑谎言。
说完这个,她不再回头,快步走出了这花厅。
走廊之中,有一阵香风吹过,远远地,一个凤钗云鬓华衣丽服的夫人在众侍女的拥簇下走来。
阿烟见了,忙低头,恭敬地候在一旁,一直等着这夫人从面前经过。
低头间,那绣有精致花纹的裙摆在青石板路上摇曳出动人的姿态,脂粉的香气儿弥漫在鼻端,这是来自燕京城最尊贵的侯夫人的气息。
其实曾经的阿烟,也是那个当自己行过,众侍女婆子都要低头让路的那个人。
曾经也是那个香风鬓影,被人高高仰视的女人。
不过现在,阿烟淡定地站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这位夫人从面前经过。
一直到侯夫人走到了回廊拐角处,她才抬起头。
恍惚间,她好像听到那位侯夫人问左右:“今日个侯爷招的是哪个小妖精伺候?”
一旁侍女忙回禀道:“今日不曾招哪个伺候,倒是一直和一个外面带回来的婆子说话。”
“婆子?”听到这话的人显然有些诧异。
侍女小声道:“原是今日侯爷在街道上,惊马冲撞了一个婆子,于是便把那婆子带府里来了,就是刚才夫人看到的那个,已经命人送出府去了。”
那侯夫人仿佛了然,淡道:“那个婆子?穿着实在是怪异。”
一时她语气中有些不悦:“只是一个婆子罢了,在二门外放着也就罢了,竟然还带到这书房里。”
阿烟远远地看过去,隐约可见那位侯夫人的容貌。
这个女人她却是认识的。
是当年御史大人李家庶出的四姑娘。
阿烟记得,当时她嫁给了武将萧正峰,传闻那萧正峰乃是粗鲁之人,这李四姑娘嫁了的第二日,都没起来床。
不曾想,如今竟来是这般富贵加身了。
阿烟心底不免一个轻叹。
世事沧桑,就是这般弄人。
这李四姑娘怕是永远也不会认出,那个狼狈的婆子就是昔日她一脸羡慕地望着的顾家三姑娘吧。
********************
离开了平西侯府后,阿烟背着沉甸甸的包袱,走在稀冷的街道上。
如今是快要过年了,许多店铺都开始关门,街道上并没有多少人影。
走出城后,她漫无目的地在这官道上踏着积雪而行,也不知道行了多久,却见来到了大名山下,山下有一个茅屋。
踏入这个茅屋,却见茅屋破败不堪,里面有一个炕,还有一个灶台,靠着墙壁的地方放着一个古老而陈旧的红木箱子,不过那箱子上早已挂满了蜘蛛网。
看起来是废弃已久的,今晚她倒是可以在那里落脚。
包袱里有平西侯府的侍女给她放进去的吃食和衣服。
今晚她只需要烧一堆火,将吃食烤一下,便能在那茅屋里安度一晚了。
她这个打算原本是极好的,可是谁知道,刚走进茅屋,便觉得眼前有人影闪过。
紧接着,后背那里感到一股沁凉,她僵硬地立在那里,低头看过去时,却见血红色的剑尖从前胸刺过来。
看到那血后,她才慢慢地意识到疼痛,撕心裂肺的刺痛,从中剑之处蔓延全身。
浑身无力,她僵硬地倒在那里,脸朝下。
她想,自己是要死了。
临死之前,她在冰冷而坚硬的泥土中,努力地睁大眼睛,想去看看那个杀了她的人。
可是她拼尽所有的力气,只能看到一个袍角,和一双靴子。
那是一双男人的朱靴。
在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她忍不住去想,到底是谁,要对她这样一个穷途末路的穷婆子施以毒手?
可是这一切,仿佛都和她无关了。
******************
而阿烟所不知道的是,她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穷婆子的死,却在这燕京城中,激起了千层浪,并引起了其后十年的朝廷纷争。
从知道她死讯的那一刻起,权倾天下的平西侯萧正峰矢志将长公主的驸马沈越绳之于法。
可是那一日她死后,大雪将一切证据掩盖,想要取证竟然艰难万分。纵然他手握重权,可是对方却是长公主的驸马,他若要指责对方罪状,必须有证据。
而就在此时,沈越竟然鼓动翰林院学子,联名上书,谴责萧正峰戕害民妇,而证据则是,那一日萧正峰的贴身侍卫一直远远地跟随在那个妇人之后。
大昭国多年以来,一直重文轻武,是以朝中武官备受冷落,文官权势熏天,然而自萧正峰以来,他一改前风,武将大有力压文臣之势。
也是因为这个,其实翰林院学子对萧正峰颇有不满,如今恰好借机闹事,将此事渲染得纷纷扬扬,大街小巷无人不知。
可是若指责萧正峰派侍卫杀人,也仿佛并没有确凿证据,一切不过是捕风捉影罢了。
因为此事涉及朝廷重臣以及长公主驸马,且又搞得大街小巷无人不知,影响极大,当今文成帝大怒,命大理寺定要查出真相,捉拿真凶。
这几乎是兴业年间一大疑案了,其涉及到的嫌犯位高权重,牵扯的人物又纷繁复杂,最后大理寺审查十年无果,一直到十年之后,一代神探成洑溪插手此案,才终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然而结果,却让大家都觉得有些无法承受。
顾烟重新睁开了双眸。
她僵硬地环视四周,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
这是一间闺房,自己所躺的罗汉床旁是一个金丝楠木梳妆柜,并金式风格底箱柜,旁边放着一个双拼六角圆椅桌,而墙上挂着丝绸卷轴四条屏纯手工绣花鸟绣画,一旁则另有一张用篆文写的绣图,那上面赫然写的便是‘玉不琢,不成器’。
此时应是晨间时分,浓郁的红光从翠纱糊着的窗棂上投射过来,把屋子折射上一层斑斓的光彩。
这厢房是朝东的,是西厢房。
而屋子里的各样布置,恰是她少女之时闺房的模样,就连墙上字画的字迹,都是那么清晰而熟悉。
熟悉到让人心颤。
午夜梦回,多少次,她重新回到少女的光阴里,无忧无虑地在顾府过着闲适而自在的日子,又有多少次,醒来之时面对着穷困和艰难,将梦中落下的泪悄悄拭去。
如今,眼见着这番情景,她忍不住抬起手,摸了摸脸颊,那脸上细腻幼滑,并没有沧桑岁月留给她的痕迹,更没有那道自己亲手割下的伤疤。
她踉跄着起身,跌跌撞撞来到了梳妆柜前,对着那面半人高的铜镜细看。只见铜镜里的人儿,乌发如云一般流淌在胸前,一张巴掌大的小脸儿细□□致,一双眸子犹如盈盈秋水,带着丝不敢置信,就那么望着自己。
这是一个姿容绝美的及笄少女,犹如带着朝露的一朵牡丹,正徐徐绽放,鲜嫩得隔着铜镜都能感觉到那蓬勃稚美的气息。
这不是那个经历了世间沧桑困苦地流落街头的妇人,而是十一年前的自己。
那个时候,父亲尚在,自己未嫁,顾府正是风光兴盛之时,能够踏进顾府门槛为花厅坐上客的,那都是燕京城里有头面的人物。
阿烟就在这惊疑之际,忽而听到一个爽朗响亮的声音。
“姑娘怎么自个儿起来了?”说着这话时,门前的帘子被打开了,一个穿着绿袄的女孩儿走进来。
女孩儿约莫十四五岁,浓眉大眼,梳着双髻,行动间倒是颇有几分干练爽快。
阿烟喃喃地道:“绿绮……”
这是自小跟着她的丫鬟,在她十三岁那年提为一等丫鬟,后来她嫁了,也就跟着她陪嫁了。
绿绮见阿烟神情有些不对,忙走过去扶着她:“姑娘,今日个风寒才好,怎么就这么起来了,竟是连个鞋袜都不曾穿。”
被绿绮这么一说,阿烟低头看过去,这才见自己正赤着一双脚踩在地上。
那双脚小巧精致,十个指甲用凤仙花染成了粉红色,犹如十个精美的小贝壳一般,十分好看。
此时阿烟心里已经隐约明白了,自己重新回到了少女之时。
不管这是不是一场梦,在这梦未醒时,她总是要好好回味这久远时光里那点点的悠闲和幸福。
当下绿绮扶着阿烟重新上了罗汉床,又盖上了锦被,正要歇下的时候,便听到外面一阵喧嚷。
这绿绮一听,便皱起了眉头,不高兴地道:“一天到晚,也不分个时候,真不知道又在闹腾什么!”
阿烟躺在那里,让冰冷的脚趾感受着锦被中的温暖,随口问绿绮道:“外面这是怎么了?”
绿绮颇有些无奈:“还不是王嬷嬷家的狗儿,真不知道又惹了什么事儿呢!”
阿烟听到这个,静静地躺在那里,脑中便渐渐回想起来了。
记得当年她刚及笄的时候,自己奶妈王嬷嬷的儿子狗儿,据说是沾染上了赌瘾,偷偷地拿了王嬷嬷的体己钱出去。后来这狗儿输了个精光,被外面的人逼着追债,王嬷嬷没办法,便拿了自己的首饰出去变卖,为狗儿还债。
她素日是不操心那金银之物的,对于些许首饰也并不放在心上,又因早年受母亲教诲,知道从小要待下人和善宽容,这王嬷嬷是自己奶妈,素来敬重的,是以竟然听之任之,只训说两句也就罢了。
如今回想起来,这竟然是开了她偷鸡摸狗的先河,因了自己纵容,后来她真是无法无天。
先是狗儿因贪财,中下别人的圈套,从而被人收买帮人做事,以至于吃里扒外,间接导致了父亲仕途上的不幸,后来晋江侯府没落后,自己和沈从晖带着体己金银赶往老家,谁知道半路却被这王嬷嬷偷走了家底,之后又遇到了盗贼将余下财务家什洗劫一空,从此后自己和夫君落得一个困苦下场。
想到这里,她唇边不免泛起笑来,当下也不再休息,吩咐绿绮道:“伺候我穿衣吧。”
绿绮听了,倒是微惊:“姑娘,你这是要亲自去过问这事儿吗?”
绿绮也是知道,姑娘对那王嬷嬷极为敬重,尽管这王嬷嬷总爱倚老卖老,可是平日里姑娘也多是忍让宽容。
阿烟心中泛起一个冷笑,挑眉,淡道:“家里出了这档子事儿,姑娘我总是要去看一看的。”
绿绮见她那绝色的小脸儿显出几分坚定的清冷,不免越发诧异,想着姑娘病了一场,倒是变了一个性子。
穿戴齐整,走出西厢房,迎面见到的便是少女之时顾府的院子。
顾府这座宅院也是前朝便留下来的了,至今也有数百年了,府内房舍古朴简约,而错落有致地分布于院内各处角落的汉白玉雕件,则为这个古老的宅院增添了几分富丽清贵之气。
院子靠近大门之处有两棵枣树,据说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这枣树每到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必是挂满一树甜枣,那果子饱满红润,清脆甘甜,有仙果之称。往年当今永和皇帝也曾亲自莅临顾府,品尝着顾府的仙果。
因了这个,每年中秋佳节,燕京城权贵,朝中百官,两只眼睛都会盯着这颗枣树的果子,端看这顾左相的果子都会送给哪些人家,以此推断朝中的动向。
而此时,就在这参天枣树之下的几口大缸旁,王嬷嬷正和一个妇人争吵着,一旁站着狗儿,并有几个没梳头的小丫鬟在看着热闹。
那妇人正是周姨娘,约莫三十多岁的年纪,容长脸儿,穿着一身锦缎,乱着一头的乌丝,此时正和那王嬷嬷吵闹个不停。
“谁家偷了我的东西,谁心里有数,老娘骂得就是你!不要以为这一家子都是傻了,看不出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老东西!”
王嬷嬷哪里是个省事的,气得老脸都红了,指着那周姨娘骂道:“你当你是谁,也敢在老娘面前叫嚣,当日夫人在的时候,是谁天天跑过来端茶递水,一口一个王姐姐地叫着,如今倒是好,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竟然把自己当做主子来了,真以为生了一个姑娘,你就是主子了吗?我呸!”
如今她们两个这一闹腾,声音嚣张得紧,一时之间,有耳房里洒扫的小厮和丫鬟也都看过来,探头探脑,好不热闹。
阿烟见此,已经蹙紧了眉。
她往年只知道王嬷嬷素来嚣张,且和这周姨娘分外不对眼,不曾想,这两个人竟然吵成这般模样,成何体统。
一时阿烟想起父亲,便问一旁的绿绮:“老爷不在府里?”
绿绮听了,不免叹道:“姑娘,你怎么忘了,上个月老爷亲自过去边境督军并运送军饷过去,一时半刻不会回来的。”
一时看着那两个人,绿绮撇嘴道:“若不是老爷不在,她们两个敢吵成这样?还不是山寨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阿烟听闻,点头笑了下,却是想起那北狄人扰边的事儿来。
近一二十年来,北狄的珝虓继承父业,登上北狄王之位,然而此人野心勃勃,不愿偏安一隅,矢志一统天下,这几年因他休养生息,兵强马壮,便时常派人骚扰边境,借机试探。
而在永和六年,也就是如今阿烟十四岁的时候,北狄王珝虓派人北狄大将军沄狨攻打大昭,永和帝大怒,便派了自己的皇子齐王边疆为帅,前去迎敌。这一场仗约莫打了一年之久,恰当时齐王吃了一场败仗,当时朝中便有风声传出来,说是齐王勾结外敌。
虽则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可永和帝到底有几个儿子呢,对于这位平日里最为寡言且和自己疏远的齐王,他还是有些不放心的。当时太子也是不安,便过来府中找了一向信任的顾左相。
如此一番商议后,永和帝便派了顾左相前去督军,并运送军饷前去边疆。
也是凑巧了,因这军饷及时到达,边疆众军军心大振,几场大战打下来,这北狄的铁骑军算是撤了。
听说齐王原本上了奏本想要反击攻向北狄的,可是永和帝却来了一句“穷寇莫追”,就此将士气正旺的大昭军给拦在那里,不许进发了。
因了这事,朝中当时也有所议论的。
不过阿烟却是想起来那后来的平西侯,当初不就是因为这一场和北狄的大战,当时只是一个校尉的萧正峰带领一个十八人的小队,偷袭了北狄军一个营,并斩杀北狄王子比烖,立下大功。从此后,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开始了他在沙场之中所向披靡的战绩,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开始了大昭国一段名将的传奇。
阿烟回忆往事,想着此时此刻,或许父亲也在边疆,或许那位日后将威名赫赫的平西侯,如今只不过是一个初现锋芒的年轻人吧?
当下望着眼前争吵的二人,她淡笑着,也不说什么,就这么静静地在一旁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