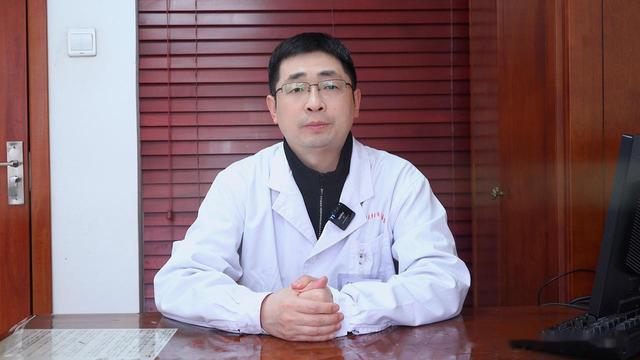“气血津液”理论是中医内科四大支柱理论,其辨证方法是中医临床辨证方法之一,排第一位的是“气”。无论是传统中医还是现代医学,临床都有重要地位,比如“呼吸”就是人体生理核心指标。
中医认为,气是天气万物基础物质,《素问》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人体之气有推动、防御、温煦、固摄等作用。
气在人体运动形式有四种:升降出入。从脏腑之间的气机运转看,心肺之气是降的,肝肾之气是升的,脾胃之气处于中焦,属于升降的枢纽。

气机如果升降失常,升得太猛太过,降得太快太多,那么临床上就叫“气逆症”。气逆会引起咳、喘、呕、嗝、闷、烦、晕等症状,影响全身,或加重原有病症。
中医辨证“气病”,一般要分虚实,虚证包括气虚、气脱、气陷、气失固;实证有气滞、气闭,加上气逆。“逆”是“反”、“以下犯上”的意思,“气逆”就是两层含义:升气太过,超标了,上冲而逆,降气时,当降不降,反而上蹿。
气逆的病机,多见于外邪入侵,寒热不均,饮食不调,痰瘀内阻,情志失控等方面,由于气是通行全身的,所以五脏六腑都有气逆的表现。但临床上,最重要、最常见的是三个脏腑:肺逆、胃逆、肝逆。
为什么肺、胃和肝的气逆最主要,也最常见?

肺主气,朝百脉,所以调气一定离不开肺,气逆也必定影响肺脏;胃主降浊,胃气是身体最最重要的养护之气,中医治病调理一定要考虑胃气,胃逆意味着胃气不降反升,中枢乱了;肝最易气郁气滞,病症由小至大出现肝不藏血、肝阳上亢、肝风内动等问题,肝逆意味着肝气下降,疏泄失职。
肺逆,就是肺气上逆,多由外邪入侵、痰饮犯肺、肺失宣肃而引起,多表现为咳嗽、喘气、胸闷、哮喘等。
胃逆,就是胃气上逆,多由寒热夹杂、水饮停胃、胃失和降而引起,表现为呃逆、嗳气、恶心、呕吐、反酸等问题。
肝逆,就是肝气上逆,多由肝气上冲、肝风内动、肝失疏泄而引起,表现为头痛、眩晕、脸红、咳血、晕厥等问题。

临床辨证气逆多为实证,少见因虚而气冲上逆的问题,肺气虚、肾气虚、胆气虚、胃气虚或阴虚引起的肺逆、肝逆、胃逆较少见,主要是痰、火、寒、饮等实邪聚于肺,胃火太盛引起的呃逆,肝气郁结引起眩晕等,都是实证。
既然是实证,按照“实则泻之”的治则,肺逆、胃逆、肝逆该如何调理?首先是都要考虑降气,然后选用不同的方剂。
1、肺逆,要宣降肺气,可用“苏子降气汤”。
肺逆主要症状是咳、喘,临床辨证要问清有痰或无痰,有热或无热,痰液是稀薄的还是黏稠的,这些是基础。

治疗方剂可考虑苏子降气汤,该方记载于《备急千金要方》,由紫苏子、半夏、厚朴、甘草、当归、肉桂、前胡、生姜、大枣等9味药组成,主治气喘、痰咳,可降气平喘,化痰止咳。
另外有中医用“三子养亲汤”,这个也可以,但要辨清肺寒、肺热,寒用白芥子,热用葶苈子,而苏子降气汤含有散寒药、温阳药,适用范围更广一些。
2、胃逆,要和胃降逆,用“旋覆代赭汤”。
胃逆明显表现就是呃逆,打嗝,这个病症太常见,寻常发病用生姜水、紫苏梗、芦根水等都能对付,但对于反复发作,问题较多的患者,需认真用方剂调理。
方剂可考虑“旋覆代赭汤”,该方出自《伤寒杂病论》,由旋复花、代赭石、人参、甘草、生姜、半夏、大枣7味药组成。

方剂里旋覆花是点睛之笔,根据药性,凡是花类药材都是升浮的,只有旋覆花是例外,它是降气的,而且专降胃气。另外,代赭石重镇降逆,半夏是止呕止呃要药,为方子功效加保险,全方和胃降逆,止嗝化痰。
3、肝逆,要平肝潜阳,用“天麻钩藤饮”。
肝逆,在头则痛,在脸则红,在胸则闷,而且血随气逆,还可诱发吐血、昏厥等问题,有的中医选用柴胡疏肝汤或木香顺气丸调理,这些药方可能分量不太够。
柴胡疏肝散多见于肝气郁滞,木香顺气丸可疏肝散郁,但肝气逆的问题,比气滞、气郁还要重,所以更合适的方剂是天麻钩藤饮。

天麻钩藤饮是现代中医方剂,记载于《中医内科杂病证治新义》,由天麻、钩藤、石决明、栀子、黄芩、杜仲、川牛膝等11味药组成,以天麻、钩藤为主药,平肝熄风潜阳,尤其是川牛膝引血下行,肝逆的血气归位,再加上方剂里有清热、补益、安神等成分,共同把肝逆病症恢复。
总之,肺逆、胃逆、肝逆作为临床气逆证的三大主要表现,中医有不同的辨证和方剂,关键是辨证论治,而且要遵医嘱用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