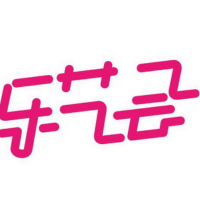郑朝晖
在我看来,读书如对谈,里面有一个因人而异的道理在。比如读到心心相印的文字,就仿佛遇到了知音,不妨快读。这里的“快”,既是畅快淋漓的快,也是“秋风走马出咸阳”的“快”。当然也有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文字,这时候,我就如对雠仇,反复在心里与之论辩不休,如果无可辩驳,就欣然接受,因为扩充了我的认知;如果仔细论辩之后,能够发现其背后的讹误,还要再三权衡,究竟是他对还是我对,每当这些时候,我读书就如“幽咽泉流冰下难”了,但这样的“慢”也是有一种快乐在其中——因为在这样的辩难过程中能够感受到自己认识的精进。

最近读8年前出版的一本书《盗火》,是“凤凰网读书文库”的一种,是凤凰网组织的几次读书会活动现场的记录,从中依稀还能够看到一些当年读书界的盛况,掩卷不免唏嘘。我以为什么观点都放到桌面上来论辩,这是一个从容大度的文化应该有的态度。并不是每一个头上有癞疮疤的都忌讳“光”、“亮”这些词的,只有像阿Q那样常常在屈辱中讨生活的人,才会特别敏感和警惕,也才会十分的忌惮,实行“光亮钳制主义”,这叫色厉而内荏——这是题外话。这本书中刘瑜、许知远、熊培云的讲话我读起来都比较快,每次读刘瑜他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一般速度都比较快,很多话自己就在嘴边但不知如何说,他们一说,嘿,就是我心里那点东西。

读到窦文涛和张翠容,就慢下来了。因为它们讨论的问题是关于中东地区的。关于中东,我们所知道的大概只有大国博弈、教派之争还有反恐。张翠容是香港的一名记者,她写了一本书,名字叫《中东现场》,她引导我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今天中东的问题。她说:“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采访,把问题梳理一下,让读者明白中东冲突的源头。最重要的是人,当地人的故事,在这样生存状态下,他们怎么理解自己的生活……”我们常常概念化地理解中东局势,简单地将那里看作是国际势力角力的斗兽场,却忽视了那里具体的生活和具体的人,他们的思考和他们的感受。比如张翠容提到突尼斯是世俗化进行得比较彻底的国家,但那里的人们却起来抗议不让留胡子和包头巾。在有些人看来这是文明与落后之争,但在那些突尼斯人看来不过是对生活习惯的坚持而已,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以,我一贯主张“穿鞋主义”:鞋子好不好,不用别人灌输、教育,穿鞋走路的人一穿就知道了。“穿鞋主义”的表现自然就是大家“用脚投票”。说得再天花乱坠,真理在我,大家不买账,一切都是徒劳。所以,我觉得整天“下一盘大棋”论者也应该想一想,老百姓想的就是安安稳稳过日子,凭什么大家都那么心甘情愿,哭着闹着一定要去做别人的棋子呢?——政治有时候真不是概念和逻辑,恰恰是平平常常的生活感受,什么是好的政治?让人舒舒服服、太太平平过日子的政治就是好的政治。这是我从张翠容的书里学到的。

当我读到摩罗和陈远的对话时,似乎阅读的速度就更慢了,因为摩罗的很多观点我都不以为然。非但不以为然,而且以为颇为有害,而偏偏他的观点现在在很大范围内颇有市场。摩罗一上来就趾高气扬地劝诫大家要反省自己,重新审视历史。比如对五四、对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都应该重新思考与认识。他的逻辑也很有意思,他觉得我们当时只知道开启民智,却没有意识到从全球文化发展来看,那两个阶段也正是西方思想试图影响全球的时期,所以,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就让自己的思想西方化了,但现在我们强大了,所以不应该再被西方化,而应该用“东”去“化”他们才是正道。摩罗的观点有两个基本的认知,一个是我们现在思考问题的框架是西方化的,一个是文化不是一种精神产品而是一种政治、经济和军事形成的权力。在摩罗看来,作为一种“权力”,西方文化迫使我们接受了他们的思考框架,按照他们的思维去思考问题。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如果历史地看,这样的逻辑其实并不成立。就拿中国的历史来说,蒙元、满清虽然拥有绝对的权力,但是最终却被中原化了,蒙古传统或者满族传统恰恰变成了一种点缀和补充,蒙古人、满族人都是用汉文化的框架来思考问题。看来,在文化方面,权力有时候恐怕未必在所谓的“权力”的一方。还是那句话,老百姓的生活选择才是最有力量的,这就是“穿鞋主义”——具体的生活是最真实的,水门汀比垫土为屋干净,席梦思睡着比硬板床舒服,坐汽车比坐马车快捷,这是谁都不否认的。原来中国人都穿“裳”,就是裙子,但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大家都穿起了裤子,似乎并不需要哪国国君用严刑峻法去强推的。要说我们被“西化”了,但是中国人一到过年就要全国“大迁徙”,各自奔回老家去,再西化的城市,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赏月,似乎并不需要通过国家规定去执行和实施。人类历史上,国家可以被占领,历史可以被篡改,但是唯独真实的生活感受却是无法改变的。“用脚投票”,就是大众按照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去选择自己愿意的生活方式(只要被允许),违背了这种选择的事情,讲得再了不起、强制性再强也没有用。

摩罗的错误在哪里?关键是他思考问题的前提是错的。他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但在我看来“各美其美”的前提是“美美与共”。西方与东方固然有差异,也不免有冲突,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就不会喜欢贝多芬,中国的《高山流水》也不会在太空飘荡。所以,其实不可能有一种文化真的可以改变另一种文化。所有的变化,不过是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大家通过选择,越来越趋向于人类共同认为的“美好生活”而已;具体表现是“西”还是“东”,是大家在具体的生活里“用脚投票”的结果,这是谁也拗不过的。我们老祖宗说“无为而治”,就是不要“拗”,用脚投票的力量是无法抵抗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就是这个道理。

再深入一层看摩罗的观点,我们就可以发现,他所持的对抗论的背后恰恰是一种文化自卑。他说:“……文化是一个利益结构,用谁的文化去统治世界,这个世界就要服从谁的利益。”我们之所以要反抗,就是因为我们被“统治”,逻辑前提还是我们是“失败者”,既然在摩罗看来我们是失败者,那么又有什么力量去反抗呢?所以,其实是摩罗的观点是立不住脚的,他不具备人类视角也缺乏历史的视角。这样说来,我所说的摩罗,恐怕就不仅仅是指具体某个人了,这样的人东方有之,西方也有之。1918年,施宾格勒写了《西方的没落》,预言了西方的衰败,鼓励西方国家以普鲁士精神奋起努力,实现自救;结果到了二十一世纪,东方的摩罗又说我们要以东方文化反抗西方文化的统治,西方文化衰败了一个世纪,居然还是统治力量,这不禁让人觉得迷糊,究竟谁才是赢家——倒是希特勒很聪明,借了这本书煽动起了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或许在施宾格勒看来,西方注定是和东方对立的,西方也注定应该统治东方的,一旦不能如愿,那就是“没落”了。这样的想法与摩罗的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美好的山水,游人如织;宏伟的建筑,观者如堵;潮流的器物,趋之如骛;舒适的生活,梦寐以求,这是人性使然,是谓“穿鞋主义”。这大概是“摩罗”们用简单逻辑武装起来的脑袋所不能知道的。我觉得在《盗火》所记录的整场对话中,陈远实在是太软,太绅士了,也可能他彼时还并没有真正看清摩罗观点背后的逻辑漏洞。

——这就是我读书的“慢”。因为摩罗与陈远的对话在我心底里盘桓了将近两个星期,在我内心里,不断和摩罗较劲,然后我以为自己想明白了,就有了不得不写下来的冲动,似乎只有这篇文章写出来了,我才可以接着往下读。现在我要继续读书了,哈哈。
本图文已经获得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