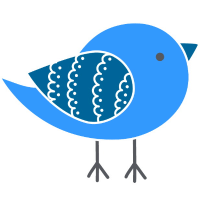7
燕子飞回来了,衔来了一封信!许平心想,我要是它多好,可以随时地飞来飞去,把孤独痛苦找个人诉说。
性格孤僻的人不会由于孤独而痛苦,好像人本身就木偶化了。许平痛苦得难受。他想她是知道的,高考体检,他曾经对王晓云说过他是B型血,王晓云也是B型。B型血的人性格外向,热情奔放。那他变了吗?变了,不外向了,不激情奔放了,变成小甲虫了,缩头缩脑的。他知道这是质变的开始,任何事物开始质变的时候都要经过一翻折腾,折腾总要痛苦。
痛苦总要找人倾诉,找人安慰。他向谁倾诉呢?谁给你安慰呢?

他接住这封信,是她!那纤细的字,是提着心在写,害怕笔尖戳破这雪白的印有学院字样的信封。是她,王晓云!
许平想象着她一直在打听着他,或者早就知道他在这儿,她在经过一番考量一番决择终于落笔。这倒使他惭愧了,一个多月以来,他给高中同学写了好几封信,有给考上的,有给没考上的,就是没有给她写。是不愿写吗?不是;是不想写吗?不是。他扪心自问。
记住她吧,她会给你带来无限的快乐。他突然想到那个小本子,是的,忘不了的,忘记过去等于背叛……
高考过后,像许平这样县城离家远的同学都没有回家,一个个抱着满怀的希望等待着已经订好的试题参考答案。城里同学一天跑学校两趟,那焦急烦躁的样子就像知道自己达线了而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一样。平时成绩一般的学生也在可怜地等着,看自己做的题目答对了没有,能估多少分。
许平每天也在等待,坐在学校院墙边的一棵老榆树下。这是高考期间看大门老头卖水卖茶选择的地方,树下摆放着一条长椅,那个时候人多,生意好。高考结束了,学生走了,又是暑假期,老头没有搬走椅子,他是存心留给同学们坐的。人与物是相似的,没有人陪伴,椅子也很凄凉。
中午,日照当头,树影婆娑,万赖俱寂,连知了都不叫了,许平不知道树上有没有知了,有,为什么不叫呢?想起初夏时,他和几个同学在这儿挖过知了的洞,找到洞,就用树棒沿洞四周慢慢把土撬开,洞变大了,手伸进去,把灌在洞穴里的泥土抓掉,知了就暴露出来了,这是蝉的蛹,刚成形,不会飞,他们叫它肉知了,肉知了烤着很好吃,这是小时候他常干的事。现在,树下挖过洞的痕迹还在,只是树上没有知了的叫声了。
他在专注地翻着一张招生报。突然,一女子清亮的嗓音和只有穿高跟皮鞋着地时才有的噔噔声同时向他的耳朵里灌来:“许平,你在干嘛?填志愿了?”
他抬起头,王晓云已经亭亭玉立地站在他跟前,他发觉他第一次目不转睛这么近距离地上下打量一个女生。她穿着淡青色的百褶裙,红色的高跟皮鞋,一双肉色丝袜一直向上套着,上身穿着白色的短袖对襟衬衫,纽扣绷得很紧,突显出胸部高挺着的乳罩的轮廓,“马尾巴”今天散开了,瀑布式地披在肩上,一身淡雅、素净,赏心悦目。当他们目光碰到一起时,他迅速地移开,继续看报。他说:“你吃饭没有?”她说:“吃过了。”说着就坐在他的旁边,一下拽过他的报纸,看都不看报纸一眼,而是笑着看他。
“还当教师了?”她问。
他说:“不当了。”
“那为什么?当初不是热情很高吗?”她笑,露出了两排雪白的牙齿。
“我不想当了,不愿意听到别人热情很高地说提高教师待遇呀这种可怜的话,好像老师比别人矮一截似的。”
“不过,我认为你是块传道授业的材料,或者走研究型道路,不要从政。”
“怎么讲?”他疑惑又惊讶,仿佛与他并肩而坐的不是她而是一个能占卜未来的老道先生。强烈的阳光从密匝匝的叶缝中射下去,如银针扎在地上,留下斑斑点点。他感到身上一乍一乍,像是在起痱子,又像是血液从毛细血管中渗出,浑身不自在。但这种感觉瞬间就没有了,反而对她来了兴趣,像一个虔诚的信徒洗耳恭听。
“参与政事者,也就是说,你要挤进人与人链接成的这根链条中,一环套着一环,你领导别人同时也被别人领导,你要使自己不脱节,你本身得有惯性和可塑性,惯性就是你做事要跟着转,要有章法,要有张有驰;这可塑性就凭一张嘴了。那一张嘴要会掉得弯转得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要使你的上级肯定有你这么靠得住的下级,而你的下级又心悦诚服的被你领导着快乐着。这是本事,各行各业都要有本事,从政要有从政的本事,会的是专业,不会的当领导,这就是政治。”
一点不假,他想他一点可塑性都没有,说话像炮铳式的,使没有听过他说话的人目瞪口呆,他老是爱说“你要考虑后果。”而不是“有话好好说”。话不投机半句多,满肚子话不想说,不对眼的人不说,说了又让人家不是滋味。
“这一点,你比不上我们班长,不过他处理好了对上,没有处理好对下。”
她研究班长了,研究了吗?班长拿我俩说事呢,班长说我俩互生情愫了,你知道吗?你有情愫吗?
他说:“你继续往下说。”
“我们女的不同于你们男的,我以后不管到哪里,从事什么职业,那里的人不会因为多了一个女同志而有什么介意,不管阅历是高是低都不会。人们传统意识女人总是依附男人的,为什么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个单位,领导安排男人做事和女人做事,期望值就是不一样的,也可能是怜香惜玉吧,要求男人做事是丁是丁卯是卯,你搞不好就被熊,一次两次都搞不好,你就完了,领导见你就头痛,于是你就闲着了,不用你了;女人就不一样了,哪有领导头痛女人的,没有。”
“我爸是镇长,他回家总是讲人啊人的。”
怪不得,环境能影响人,也能改变人。他想,她将来要么平庸,要么出人头地。
“所以,为了不至于卷入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务中去,我喜欢你当教师。”
她一股脑儿说完,脸通红。低头理了理裙子,一头秀发滑下来遮住了整个脸面,只见她头一仰,顺手一捋,又齐刷刷地披在后边。
……
现在,这一切显得那么遥远,又是这么近。
“……临走时,我从李老师那儿得知你的消息。鬼使神差,我也搞上了教育,是学院的教育系。我想以后可以当教师,也可以管教师,是吧?许平。在此,向你报告一下我近来的状况,开学第一天,辅导员要我当学习委员,之后教育系又重新选举我当上了系团委组织委员,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后,我向辅导员说我怕不能胜任,尤其是系团委组织委员,没有共青团工作经历。辅导员说好好干,干中学,学中干,工作经验哪有什么现成的,都是慢慢积累的。在此,谢谢你,关于我入团的事,你和班长的争论,我略知一二。对于别人的议论,我是这样想的,我走我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许平一口气读完王晓云的来信,回味无穷。激动的心要跳跃出来。他听见了左右心脏撞击他胸膛的咚咚声。他交叉两只手紧紧地按住胸口,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等心脏稍稍地恢复了一点平静,他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一遍又一遍。幸福说来就来,来得太突然了,字里行间看出来王晓云一直在想他!在爱他!
他闭上了眼睛。一个黑影在他眼前游荡:“恋爱双方都有爱与不爱的自由,双方都爱,幸福地结合,双方不爱,爽快地分离。一方在爱,一方不爱,叫单相思,那就痛苦地分手。可你就不同了,你怎么都会痛苦。这话怎么讲?你和小花,她爱你人与才于一身,为了得到你,有时她表现出赤裸裸的性,这是古老的纯朴的爱,你会感觉她好可怜好可爱。但你俩结合了,王晓云会痛苦,会骂你是个傻瓜木头人。而当你和小花结合了,过一段时间你会后悔,因为你忘不了王晓云。你选择了王晓云,你对小花又不忍心。实际上,你当初就不该……”
“那我怎么办?我不能老是痛苦呀。”
“好,恕我直说,你现在的心已经系着两头,从你的心发出的两条感情线,一条已经和小花联上了,现在和将来,不管她怎么爱你,你放在这条线上的力量不会加大,甚至还会减小,因为她不如你;另一条线,王晓云把线已经伸过来了,但是你克制住没有明显去接,你的感情线又没有大胆放开,讲你是麻木不仁吧你又不是,实际上你麻木不仁的背后是强烈地爱的冲动。”
“这么说,我选择王晓云,能说对小花不道德?”
“哎,你们人间向来以善与恶来评价一个人的道德,对善进行褒扬,对恶进行咒骂,这无可非议。但我的朋友,善中混有伪善者,对你们年青人来说,伪善是不能原谅的。爱是神圣的,不能虚假虚伪。就说你,小花爱你要命,你真的爱她吗?我看未必。你有她那么真心投入?你对她的爱难道不混杂着对王晓云的爱?而这种爱是小花不能接受的,王晓云也不能接受。我能感觉到你对小花就那么一回事,在敷衍她的爱,你不主动去爱,你没有她狂热,她一心想委身于你,但你不接受。你克制住了你的性爱,你是怕背上道德的枷锁,保住不了自由身。对王晓云,你不主动,虽然想主动,但你有小花的包袱在背着,所以你才不能敞开心扉大胆表达去爱王晓云。实际上你爱的天平秤是倾向王晓云的。所以说,我的朋友,我建议你同小花开诚布公地谈谈,她会退出的,她是一个弱者,爱是不能将就的,与其你带着亵渎的心去接受小花,不如让小花带着对你的爱爽快地离开你。”
他明白了!他没有回信。他要想一想,想一想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要镇定一下他的痛苦的神经。
作者简介
陶继亮,笔名水拍岸,安徽省明光市作协会员,省散文家协会会员。供职于乡镇、市直机关,曾任乡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市水产局副局长、市委组织部选派办主任、市人社局局长、市民宗局局长、市医保局党组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等。散文、小说散见于《滁州日报》《明光文学》等媒体公众号,散文《孤独的“正塘”》入围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入围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