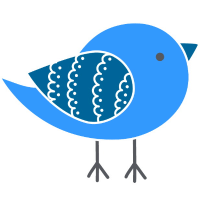时间对人就是这么奇怪,穷日子度日如年,好日子过得真快;百无聊赖时过得真慢,考虑问题心里装着事过得真快。这不,元旦过后,一个月又过去了,放寒假的时间快到了。这个寒假怎么过呢,不回家?不行。放假了,过年了,你为什么不回呢?回家吧,家里还不知道是怎样的情况呢?你能逃避了吗?到王晓云家去,不可以吧,这么快就去人家,也不是你的性格,况且王晓云会怎么认为你呢,有家不回,在回避什么?她不知道,绝对不让她知道!这么多天来,许平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家,从容面对。

许平坐了一整天的车,晕乎乎的。傍晚,他忐忑不安地踩上了家乡的田野,没有兴奋,一切都是这么平常,就像这平静的土地。田埂沟里、路上的坑洼积着的雨水已经结上了薄薄的冰层,鸡皮似的,踩上去唏哩哗啦,随后就冒出了泥浆。麦田的背阴处还零星地分布着尚未融化的雪,经过冻结,踩上去硬梆梆的。田野无遮无挡。西边天,太阳还留着半个脸面,红红的半边脸失去了光芒,眨眼工夫,就溜了下去。一群麻雀叽叽喳喳旋风似地从头顶上掠过,越小越小,当成为密密麻麻的小黑点时,已经落在了村南打谷场的草堆上。
打谷场南头草堆边有一个人在弯腰拽草,远远看不清楚,再近些,是个女人。女人站直起来,向他这边望着,继而又弯腰拽草,再近些,是她,是小花。他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本想,既然回来了,抽个时间和她好好谈谈,假期这么长,不可能不见面,解释一下,关系不至于想象的那么别扭。就像她说的是命运给他们之间安排了一个插曲。如果他整天闷在家里,稀里糊涂,避之远之,恰恰说明他是懦夫,他欠人家一个情。相反,勇敢地走出去,见到她,让她恨他骂他甚至狠狠地打他才好,把他的虚伪彻底地击碎,他心里才好受。
许平继续向前走。当他的目光重新投向草堆时,只见她停止了拽草,匆匆跑进草堆旁边的茅屋里。毫无疑问,她看见了他,或者说远远的他看不清她时她就看清了他,只是没有躲开,当他走得更近一些,她才故意躲开给他看。他想,要是以前,她远远地就跑过来迎他了。不过,今天,许平想要的就是这种结果。永远躲开他才好呢!
许平茫然了,他不能走开,他要进去。
茅屋是看场用的,冬天,粮食进家了,场也不用看了,这倒成了麻雀栖息的场所。茅屋不大,门檐不高,人低头才能进去。墙拐角尽是麻雀屎,靠西山墙放了一张凉床,床腿不高,床经是用麻绳网的,有弹性。她坐进去,两脚着地,头低着,两手捂着脸。
许平直直地站在门口,看着她。“小花,我——”
“不要讲了。”小花气呼呼地说,泪汪汪的眼看着他。
“小花,对不起。我--”
“我不要你对不起!许平,你说真话,是不是不爱我了?你要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
“不是的,我念书早着呐,本科,我还要考研。这么长的时间,我怕你等不及。”许平心虚了,又不敢说出我不爱你了。
“那就是说,你心里还是有我的。我不怕等,等你,一直等下去!”
许平彻底地绝望了。没想到小花这么执着她的爱。心想,我,许平,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呢?我的心已经出轨了,我俩还能在一起吗?没想到她没有放弃,她这么固执,许平想错了,低估她了,上帝也低估她了。
这该怎么办呀?
各自回各自的家,各自找各自的妈。一路无语。
许平到家时天已经黑透了。全家已经吃过饭,他妈在洗碗刷锅,姊妹俩洗洗准备睡觉了。
一看儿子回来,母亲赶忙问:“吃饭了没有?”
许平说:“不饿。”
母亲说:“坐了一天的车,怎么不饿呢?下点面条给你吃。”
“不吃,我累了,我要休息。”许平说着就去拿脚盆洗脚。一脸的沮丧。
看着儿子不高兴的样子,父亲说话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要不要找先生看?”
“没有哪儿不舒服,就是累,想睡觉。”
“那你就洗洗睡吧。”父亲说。
小妹看出了哥的心思,跑到屋里,说:“哥,你不去看看小花?小花上午还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说我不知道。”“还有,你不在,两家已给你俩定过亲了,估计小花家怕你变心。”
“什么?定过亲了?我不在家,怎么定亲?”许平愕然。
“东西已给送过去了,三转,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小妹说。
“是谁的主意?”许平一脸的疑惑。
“是她家提出来的,亲迟早是要定的。”小妹说。
“太不像话,不懂规矩!”许平气愤了。
“哥,你是不是不想要小花?你是不是另有女朋友了?”小妹一脸的嬉笑。
“小孩懂什么,去睡觉去。”许平拿这个小妹没办法,没大没小的。
一个多月以来,小花表现得确实坚强。许平的来信给她带来的锥心刺骨的痛只能深深地埋在心里。正如她父母亲说的那样,她不能对外声张。被对象甩了,丢人的事,别人知道只能看你的笑话。自从与许平处朋友到现在,庄前庄后的老少爷们,姑娘媳妇的,那真是羡慕嫉妒恨。尤其是那些没对象没嫁人的村姑娘,看她的眼神都充满着敌视,心想就不漂亮一点儿吗,狐狸精勾魂眼,活生生把许平勾走了。许平也是的,图她什么?图她漂亮图她家境好?她爸不就是个乡村医生吗?还有什么呀?许平也是的,考上大学了,什么美女没有,要知识有知识,要漂亮有漂亮,不随你挑的吗?你的标准怎么就这么低?早知道这样,我也去勾!这些村姑把她与许平的恋爱的罪过全部推在小花身上,这些村姑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小花不憨,小花多精明,村姑眼神里的一招一势小花都能看出来。有一天镇上逢集,小花和一群大姑娘小媳妇上街,路上她们嬉嬉笑笑打打闹闹逗小花,哎,小花,许平来信了?你这几天瘦了,想瘦的,想人的罪难受啊!一位媳妇凑过来笑嬉嬉鬼不叽叽在她耳边说:“哎,小花,你同许平睡过了?没睡赶紧睡,打上印记,不这样的话,许平会不要你的。你怀上了?看你瘦的,要注意身子。”说完就跑,小花撵上去一阵疯打,打得那媳妇不要不要的。
我就让你们羡慕!就让你们嫉妒!怎么着?小花心想,想得美滋滋的。
此一时彼一时也。她爸妈的意见是对的,丢人显眼的事不能传出去。一传出去,那些大姑娘小媳妇的眼神就不是羡慕嫉妒恨了,而是看笑话幸灾乐祸了。况且心爱的许平还没有彻底摊牌,只是试探性的口气。她要努力,有一线希望也要争取,争取许平要她。
父母都不在努力吗?“三步走”计划不在实施了吗?
小花从打谷场上把一粪箕草背回家时,父亲从诊所刚回来,正在洗刷准备吃饭。母亲还在锅台上忙着贴饼炒菜。小花把烧草放在锅屋,顺手拽一把草塞进锅灶门里,用火叉挑着,使得锅门里快要熄灭的火“通”地一下燃烧起来,烧草发出霹雳哗啦的声响,一股浓烟顺着烟道升腾出去,弥漫在夜空。
母女俩在锅灶上一前一后忙着。
母亲说:“拽个草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小花没有立马应答。过了好长时间才说:“许平回来了。”
母亲问:“你看到他了?”
小花说:“嗯,在场上遇到的。”
母亲说:“你俩讲话了?喊来吃饭呀?”
小花说;“他有点不高兴,讲话吞吞吐吐的。我也没给他好腔。回家去了。”
母亲说:“明天晚上喊来吃饭,有话桌面上讲。听到了吗?小花。”
小花说:“噢。”
母亲说:“明晚上,你就照我说的去办。”
农村分田到户以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粮食连年丰收。加上小麦水稻价格上涨,这一年粮价涨到五、六角钱一斤,除了公粮,家家户户年底都能落个万儿八千斤粮食。粮食多了,就盖房子,把原来的土坯房全部打倒,盖成砖瓦房。许平家当然还是土坯房,有钱给孩子念书呢。先生家有房三处:三间诊所算一处,本来就是砖瓦房,这是老两口住的地方;原来三间草房也就是现在的锅屋算是一处,是全家吃饭和那个油瓶儿子睡觉的地方;去年在家后边自家的宅基地上又盖了三大间砖瓦房,基本上是女儿小花的闺房。
吃过饭,先生老两口回村上自家诊所睡觉去了,小花跑到后屋她自己的闺房睡觉去了。
小花又是一夜无眠。心爱的人近在咫尺,却不能在一起。不过小花知道,许平就是这样的人,讲好听一点是正经、传统、封建,讲不好听的是没开窍。每次在一起,也就两三次吧,都是小花约他,他从来不约她。在一起,亲呀搂呀都是小花主动的,他是迎合的,有时候小花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蠢蠢欲动急得要命,他就此打住从不越底线。小花也不知道他的内心世界是什么,内心世界是怎么想的。就是那封信,他也只是说为她考虑,他要念大学读研究生,怕她等得难受,怕她得精神病,所以他想放弃不想谈了,不过如此罢了。从这一方面来讲,只要小花不放弃,许平就没撤。
小花心想,有什么话,明晚再说吧。
作者简介
陶继亮,笔名水拍岸,安徽省明光市作协会员,省散文家协会会员。供职于乡镇、市直机关,曾任乡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市水产局副局长、市委组织部选派办主任、市人社局局长、市民宗局局长、市医保局党组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等。散文、小说散见于《滁州日报》《明光文学》等媒体公众号,散文《孤独的“正塘”》入围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入围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