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沉淀。
以色列借美国之力,逐步蚕食巴勒斯坦的土地,烽火不熄,硝烟不散。
每一日,巴勒斯坦的土地上都弥漫着鲜血与哀嚎,无辜生命在战火中消逝。
这场冲突撕开了战争的血淋淋真相,也暴露出以色列毫无底线的侵略行径。

为了建立国土,竟以他国人民的性命铺路。
这不正是美洲大陆上曾上演过的悲剧?
印第安人的哭声尚未散去,巴勒斯坦人的呐喊已再次回荡。
历史惊人地相似,开门揖盗的巴勒斯坦人,即将成为另一个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的悲剧
巴以冲突的阴云,笼罩着一段令人心碎的历史。
燃烧的土地、哀嚎的平民,映衬出战争的冷酷无情。
以色列在强权庇护下,步步紧逼巴勒斯坦的家园。
这一幕,何其熟悉?

巴勒斯坦人今日所遭受的苦难,正是印第安人昔日的悲歌。
当哥伦布首次踏足美洲大陆,迎接他的是热情的印第安人。
他们跃入水中,以礼相待,却换来对方的武力相向。
哥伦布用铁链禁锢他们,用严刑逼问道路的方向。
这一幕是未来数百年殖民暴行的预演。
自那时起,印第安人的命运早已写定。

历史书上将他们称为“野蛮人”,并以“物竞天择”的名义掩饰对他们的屠戮。
事实上,正是这些所谓的“文明人”,以“开化”之名行掠夺之实,才是最大的野蛮者。
普利茅斯,这片美洲东部的港口土地,曾迎来了搭载清教徒的“五月花号”。
初至陌生土地的移民者,若非印第安人的慷慨相助,恐怕难以熬过最初的两个冬天。
是印第安人教会了他们种植粮食、捕猎狩猎,并将南瓜与玉米作为馈赠。
当“感恩节”被设立时,这份节日的感念并未回馈给真正的恩人。

如今,普利茅斯的印第安人集会上,“感恩节”成了“哀悼日”。
殖民者的本性逐渐暴露,友谊化为敌意,感恩变成屠杀。
随着更多殖民者的涌入,印第安人被视为障碍,被驱逐、分化、清剿。
各部落的反抗虽英勇悲壮,却难以撼动武装精良的侵略者。
从1622年到1769年,清剿与杀戮贯穿了整个北美大陆。

美国独立后,疆土扩展如火如荼。
联邦政府继承英国殖民者的政策,将对原住民的征讨推向新高度。
按理说,一个国家建立后,其疆域内的居民理应成为公民,无论文化落后与否,政府都有责任给予保护与教化。
美国的“民主”政府却选择了截然相反的道路。
他们没有耐心,也没有怜悯,而是将印第安人视作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在“种族优劣论”的荫庇下,他们堂而皇之地推行种族灭绝政策。
这种血腥政策自1803年购买路易斯安那地区起,绵延近百年。
联邦军队和民兵对印第安部落展开无休止的屠杀,鲜血染透了北美大地。
为了配合军事行动,政府制定了令人发指的法令。
1814年,时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参考早期殖民地屠杀奖励机制,颁布法令,规定每上缴一个印第安人的头盖骨即可领取奖金。
若是12岁以下的孩童或女性,赏金为50美元;若为成年男子,则翻倍至100美元。
而那被全球称颂了两百年的《独立宣言》中,写着“人人生而平等”,却难掩这句口号的虚伪本质。

所谓“人”,在当时的美国,仅限于白人男性。
妇女、黑人皆被排除在外,至于印第安人,甚至连被纳入考虑的资格都没有。
历史轮回,苦难重演
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血腥屠戮与无情驱逐,美国政府终于将印第安人逼入保留地,为白人殖民者腾出了大片土地。
19世纪30年代,印第安人的土地范围曾覆盖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大部分地区,而到最后,仅剩下总面积不足2万平方英里的分散保留地。
以大平原上的科曼奇人为例,这个曾经驰骋在3亿英亩狩猎地上的民族,到了19世纪末仅能栖息在区区300万英亩的保留地中。

即使这些零星保留地也未能逃过殖民者的魔爪。
随着白人对土地的贪欲无以为继,美国政府将目光投向了印第安人最后的栖息之所。
188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道斯法案》。
法案的核心分为三步:
首先,解散印第安部落,将部落土地强行私有化,并分割为若干“个人份地”,分配给印第安人;
其次,凡接受份地分配并脱离部落的印第安人,可被授予“公民”资格,但必须接受所谓“文明教化”;

最后,将分配后剩余的土地出售给白人定居者,所得款项由联邦政府“代管”,声称用于印第安人的“教育”。
通过土地私有化,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经济和社会体系被彻底摧毁。
到1933年,印第安人土地仅剩4700万英亩,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
那些因接受份地而获得“公民”身份的印第安人,也未能真正融入美国社会。
他们被迫脱离部落保护,孤身面对白人社会的剥削与歧视。
从执行结果来看,所谓获得“公民”身份的印第安人,非但未能融入白人社会,反而普遍陷入了无尽的贫困深渊。
他们的土地、文化、传统甚至族群意识,在所谓的“文明开化”政策下被一步步剥夺,最终成为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牺牲品。
而这种灭绝文化与摧毁族性的手段,其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寄宿制学校的设立。
在寄宿学校里,印第安儿童被强制剪去长发、改换服饰、学习英语,甚至禁止使用母语。
他们的文化根基被连根拔起,而这一切,被美其名曰“教育的成功”。
随着政府拨款增加,这样的寄宿学校雨后春笋般涌现,构成了灭绝印第安人文化的“最后一环”。

那些学校剥夺了印第安儿童的童年,剥夺了他们回归族群的可能。
这种冷酷无情的文化消灭战,在某些殖民主义者笔下,被描绘成“文明战胜野蛮”的凯歌。
令人讽刺的是,以色列的历史何尝不是一场被迫与反抗交织的血泪史?
在二战时期,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曾屠杀600万犹太人,那场浩劫带来的创伤深深镌刻在以色列民族的记忆中。
他们明白,一个强大的国家是生存的保障,于是毅然选择回到祖先居住的土地,重建家园。

这种“复国”之路,却建立在另一场苦难的基础之上。
为了争夺巴勒斯坦的土地,以色列对当地人展开了同样冷酷的屠杀。
那些犹太人曾经历的痛苦,如今被他们带给了巴勒斯坦人。
冲突难以调和
在一战后,作为战败国之一,奥斯曼帝国不得不将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大片领土交由协约国分割,而巴勒斯坦则被划入英国委任统治的范围。
这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逐渐兴盛,特别是在欧洲“灭绝恐惧”阴影下挣扎的犹太人群体,更加迫切地寻求一片“故土”作为栖身之地。

“锡安主义”由此得名,“锡安”是耶路撒冷老城外围的一座小山丘,自古象征着以色列的家园。
尽管工业革命与现代化的浪潮席卷欧洲,但对犹太人的仇视与歧视却未曾减弱,反而愈演愈烈。
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世俗犹太人认同复国的理念,渴望通过建立纯粹的犹太人国家来改变他们两千年来被压迫、流离失所的命运。
犹太复国主义者所瞄准的建国之地——巴勒斯坦,并非一片“无主之地”。

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数以万计的阿拉伯人,他们在这片家园上繁衍生息,与土地紧密相连。
犹太人复国的计划,无疑与土著阿拉伯居民的基本生存权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最初,犹太复国主义者试图与当时统治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帝国达成协议,寻求和平途径以实现建国目标。
这一尝试并未成功。
一战期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以其化学贡献协助英国军队,在军事技术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凭借这一影响力,许多犹太名门与英国政府建立联系,为复国运动争取到了关键支持。
1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致信犹太复国主义同盟主席罗斯柴尔德,明确表达了英国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之家”的支持。
这封信件,即后世所称的《贝尔福宣言》。
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的衰亡标志着巴勒斯坦进入英国委任统治的时代。
犹太人的复国梦并未因《贝尔福宣言》的承诺而加速实现,反而遭遇重重障碍。
英国人不仅没有兑现支持犹太复国的承诺,还逐渐收紧犹太移民的入境政策。
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步伐被迫放缓,而与此同时,东欧的犹太人却因迫害加剧,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向巴勒斯坦迁徙的浪潮。
面对内外交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一度将目光投向其他土地。
阿根廷曾被视为可能的复国地点,而英国更曾提出从其殖民地乌干达划出一片土地供犹太人安身。

不过,这些方案最终都未能成行。
巴勒斯坦,尤其是耶路撒冷,对犹太民族有着无可取代的宗教和历史意义。
在复国主义者看来,唯有回归这片祖先之地,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的复兴。
这一选择拉开了苦难的序幕。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民族主义意识觉醒的阿拉伯人开始公开反对犹太复国主义。
袭击犹太人定居点、组织武装行动,甚至联合对英国施压,要求彻底关闭犹太移民通道——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冲突的火焰开始燃烧。
与此同时,石油的重要性逐渐显现,英国的政策重心也随之偏向阿拉伯人,这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的混乱与对立。
德国纳粹的上台和二战的爆发,使犹太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数百万犹太人被驱逐、囚禁、屠杀,犹太民族在欧洲遭遇前所未有的灾难。
而这一切,在战后欧美世界的主流舆论中掀起了强烈的同情浪潮。
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血腥事实,最终推动了国际社会对犹太人建国权利的支持。
心力交瘁、国力耗尽的英国不愿再承受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负,最终选择将此问题移交给联合国。
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第181号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和一个犹太国。
根据决议,犹太人将获得约55%的土地。
犹太人对此欢欣鼓舞,将之视为复国梦的实现,而巴勒斯坦人及周边阿拉伯国家则愤然反对,认为这一分配无视阿拉伯人的基本权利。

从这一天起,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开始了更加惨烈的对抗。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
翌日,第一场中东战争骤然爆发(1948年5月15日至1949年3月10日),这一战争注定改变中东的历史进程。
以色列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国际支持,不仅稳固了建国的基础,还在战场上占据上风。
当战火停息之时,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已化为废墟。
他们失去了联合国原本分配给他们的近四分之三的土地,而这片土地早已成为权力博弈的筹码。
超过70万巴勒斯坦人被迫背井离乡,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
这一切,仿佛历史的轮回。
犹太民族在近两千年的流浪中忍受了无数苦难,而如今,巴勒斯坦人却被迫接过了这份苦涩的遗产。
他们从自己的家园中被驱逐,被迫在异乡徘徊。
如今,哈马斯成了巴勒斯坦人反抗的极端化象征。他们所追求的,不过是一个能与以色列平等对话的独立国家。

可是,历史的重压和现实的桎梏,使这种诉求在战火与硝烟中显得无比遥远。
巴勒斯坦的命运悬而未决,留下的是一段伤痕累累的历史,和一个依旧迷茫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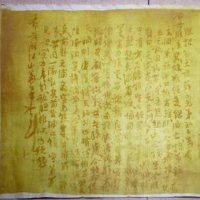
摇了一夜床
文明必将战胜邪恶 正义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