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类角度看,东方古代文学中民族意识最突出的是颂诗和史传文学。
东方民族通过敬祖祭神、赞美故土山川风物、歌颂君王和民族英雄来增强民族凝聚力。
文学,有意无意地成为东方民族共同意识形成的手段。
东方各自民族的历代知识精英,把民族的神话、传说、真实的或臆想的祖先、民族历史的大事件或某些名山大川加以象征化的文学表现,赋予它们以民族文化的内涵,不断传承积淀,从而形成共同的民族意识。

颂诗传统在古代东方比西方发达。
在神话时代,西方有奥林匹斯神系,但西方先民不及东方先民对神的敬仰和恐惧,颂神不如东方人经常和普遍。
中世纪对上帝的赞颂,其根源来自东方,且西方只有一个上帝,不像东方的神灵众多。
东方的宫廷政治比西方经历的时间长得多,宫廷诗人为君王歌功颂德的传统远远胜于西方。
颂诗作为一种情感高尚、格调庄严的抒情诗,以神格灵迹、英雄壮举、君王功德、山川风光等为赞颂对象,抒发的情感往往是一种时代的集体情感,从而与一定时期的民族意识相通。

先看东方古代的颂神诗。
古代东方大多属于农耕文明或被农耕文明同化的游牧文明,而普遍崇拜太阳神。
许多民族都有太阳神颂诗。
如古代埃及的《阿蒙颂歌》、《赫普里颂》、《阿吞大颂歌》,巴比伦的《沙玛什赞颂》、赫梯的《太阳神颂歌》,印度《吠陀》中有11首赞颂太阳神苏利耶的颂诗,日本把太阳神天照大神作为日本岛民的先祖加以赞美。

然而,天宇中只有一个太阳,太阳普照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无所偏袒。
因而在古代东方颂诗中的太阳神,往往是公正严明的形象,被描述为正义化身的审判者,慷慨无私的施与者。
印度的苏利耶“无所不知、无所不见、眼观整个世界、洞察善与恶,且异常迅捷”。
埃及的《阿吞大颂歌》中写道:
你使远方诸域国泰民安,创造了天界的尼罗河,尼罗河为他们从天而降。
她在山间波涛汹涌,犹如在海上,在他们所居之地灌溉农田。

噢,它们,你的意志,俱已付诸实现,永恒的主宰!天界的尼罗河,你为外域者以及一切野生走兽而创造;而地下尼罗河,你为埃及而创造。
这些太阳神颂诗从太阳的本性出发,表现的不是民族意识,而是相反的普世观念。
在太阳神之外,东方古代民族还有各自的民族神。
在对民族神的赞美中,却有着明显的民族意识。
在两河流域尼普尔城出土的《恩利尔,无所不在……》中有这样的诗行:
恩利尔!当他以其手在世间划定圣域,当他为自己建造了尼普尔城邦,基乌尔,丘阜、其洁净之地,皆为甘美之水,在万城之中央,在杜兰基地方,为自身兴建!异域诸邦在其面前俯首!……让遥远的诸域在其面前折服!
犹如潮水漫流于世,惠赠涌入仓廪,祭品聚集于库中,贡品陈于主殿,奉献于埃库尔,天蓝色的寺庙。
恩利尔是尼普尔的守护神,曾成为宇宙的主宰。
诗中表现了苏美尔时代诸雄争霸中尼普尔人的民族思想。

古埃及中王国时代奥西里斯崇拜盛行,奥西里斯成为埃及的民族神,刻写在公元前15世纪一块石碑上的《奥西里斯颂歌》描述其强大:
其力至强,将其仇敌打翻在地,其威至大,使其仇敌望风披靡。
他令仇者胆战心寒,他使心怀叵测者败逃,他心如铁石,践踏敌对者。
颂诗中“仇敌”、“心怀叵测者”、“敌对者”在神话中指塞特,在埃及的社会现实中指入侵埃及的希克索斯等异族人。
这里奥西里斯的威力和“心如铁石”,助我惩异,已完全不同于太阳神的阔大胸怀。
因为古代埃及人在奥西里斯的神格中倾注了民族的血脉与灵魂。
不仅苏美尔和古埃及的颂神诗如此,《吠陀》中对因陀罗的赞颂,《阿维斯塔》对玛兹达克的颂扬,都可以读出这样的民族意识。

次看古代东方文学中的君王和民族英雄颂诗。
随着地缘性的利益群体出现,国家开始产生,但很长时期是专制君王管理下的国家政体。
在古代东方,不论是君权神授,还是政教合一,或是世俗王朝,君王与国家和民族总是联在一起。
君王贤明才高,则国家民族昌盛;反之则意味着社会动荡和遭受异族凌辱。
说到古罗马,人们马上想到渥大维;说到马其顿,自然想到亚历山大;同样,汉谟拉比与巴比伦、居鲁士与波斯、大卫王与古代希伯莱,阿育王与古代印度、哈伦·拉希德与阿拉伯等都是与民族联在一起的君王。
对于历代君王,宫廷诗人都有诗作赞颂。

大量的奉承帝王、艺术平庸的颂诗已被历史所汰洗,只有那些真正具有雄才大略、对民族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君王的颂诗,才受到后人的珍视而得以流传,也只有这样的颂诗才凝结着民族意识的内涵。
如中国《诗经》“大雅”、“周颂”中对周文王、周武王的颂诗、古代南印度桑伽姆时期的《勋业诗四百首》、《十王颂诗集》、朝鲜李朝建国颂歌《龙飞御天歌》等都是这样的颂诗。
这些诗作往往把君王的文治武功、才情智慧与国家兴衰、民族命运结合起来,抒写忠君爱国的情怀。

古埃及第十二王朝的法老塞索斯特里斯三世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国王,他四次率军远征努比亚,拓展国土疆域;对内改革弊政,削弱地方贵族势力、强化中央集权,促进政治稳定;组织开凿阿旺斯运河,注重商贸和生产发展。
他巡视埃及城镇,庆典上人们诵唱《塞索斯特里斯三世颂歌》:“神多么高兴,/是你增加了他们的供品!/人们多么高兴,/是你保卫了他们的边疆!/祖先多么高兴,/是你增加了他们的遗产!/埃及多么高兴,/是你维护了它的风尚!”在“多么高兴”的反复咏唱中,洋溢着国泰民安的民族自豪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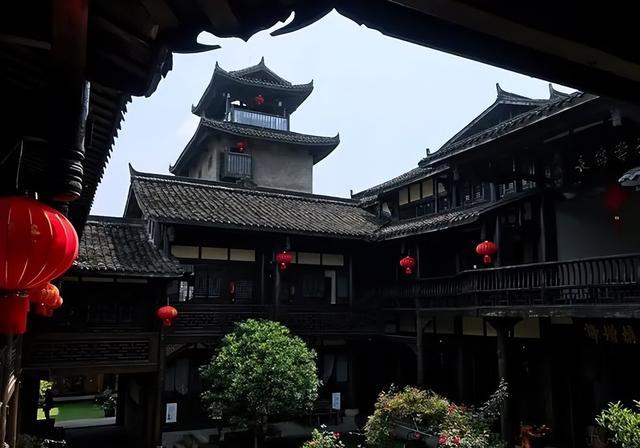
在民族发展中,君王固然有着重要作用,但在抗击异族侵略或征服异族的战争中,东方古代各民族都有一批勇猛善战,甚至捐躯沙场的英雄。
东方诗人缅怀他们的功绩,把他们当作民族精神的象征加以颂扬。
古波斯的扎里尔和鲁斯塔姆、阿拉伯的赛福·道莱、中国的张骞和文天祥、印度的地王和西瓦吉、日本的丰臣秀吉等都是这样的民族英雄。
西瓦吉是印度17世纪反抗莫卧儿王朝外族统治的民族英雄,他联合马拉特人,坚持武装抗敌35年。
诗人普生(1613—1715)创作了《西瓦吉王》和《西瓦吉五十二首》歌颂其英勇伟业和赫赫战功,其中有一节:“正像因陀罗制服金帕妖精,/罗摩摧毁罗波那的狂妄野心,/狂风驾驭云层,湿婆毁灭爱神,/毗湿奴降服了长着千只手臂的精灵,/正像天火毁灭森林、豹子威镇鹿群,/雄狮战胜野象,海火使海水沸腾,/光明驱散黑暗,黑天杀死刚沙暴君,/猛虎一样的西瓦吉消灭了异族人。”
诗作以大量的印度传统神话典故映衬出西瓦吉抗敌中的勇武,以形象迭加的方式突出西瓦吉抗敌壮举与印度民族传统的内在联系。

再看东方古代的自然颂诗。
民族共同体常常是指人,但不应仅仅指人。
民族成员对民族的认同是多方面的,其中作为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尤其是那些让民族受惠或独具特色的山川风物就是民族情感寄托的重要方面。
古代东方诗人往往把这些山川风物作为民族构成的一部分加以咏唱颂扬。
古埃及的《尼罗河颂》、古代希伯莱的《向锡安山欢呼》、阿拉伯尚法拉(510—?)的《沙漠之歌》、日本山部赤人的《咏富士山歌》、舒明天皇(629—641)的《天皇登香具山望国之时御制歌》、朝鲜权近(1352—1409)的《咏金刚山》等都是这类自然颂诗。

如咏富士山:
甲斐骏河两国间,当中屹立富士山,
山高入天云难过,飞鸟高翔也难攀,
燎原大火为雪灭,降雪又为火烧干,
山神有灵不可说,神灵何以欲难名,
堂堂有名石花海,包围全在此山中,
人人可渡富士河,此山之水注成功,
日本古国此大和,山神坐镇如宝库,
骏河高耸富士山,一生长见不知足。
这类颂诗在自然风物的描绘中,渗透着爱国激情。
倾注于故国山水、自然景物中的民族情感,经历代文人反复咏叹而积淀,自然物事已不再只是“自然”,作为民族的象征而存活于民族成员的心灵,成为民族凝聚力的一种触媒。

史传文学是东方古代各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包括历史人物传记、历史事故、历史小说、咏史诗、述史诗、历史剧等具体的样式,而它们共同的根本特点就是以一定时期的历史作为创作素材。
这里的“历史”,是群体的历史、民族的历史。
即使是个人传记,也是以个体的方式展现的民族历史。
能成为“传主”的人,不是普通的、一般的个体,往往是处于民族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
对此,我们只要简略列举东方古代文学中重要的史传文学作品就能看出这一点:古埃及刻写在石碑墓壁、书写于纸草的传记文学;希伯莱《旧约》中几个老族长的传说和王国兴衰的史述;波斯菲尔多西的叙事长诗《列王记》;印度波那的小说《戒日王传》、伯德姆那帕的叙事诗《冈赫尔德传》;阿拉伯穆格法的文学传记《波斯诸王传》;日本的历史演义小说《平家物语》、《荣华物语》;中国的《史记》、《三国演义》;朝鲜的历史散文《三国史记》、历史小说《壬辰录》;越南吴时志的历史小说《皇黎一统志》;缅甸吴格拉的历史散文《缅甸大史》;泰国昭披耶帕康的传记体历史小说《拉提叻》;斯里兰卡的叙事长诗《大史》;马来西亚历史故事《马来由本纪》、历史人物传记《杭·杜亚传》等。

这些史传作品的民族意识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历史题材的选择,二是作者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态度。
东方古代的作家、诗人往往选择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事件和人物加以表现,赞美颂扬推动民族发展、挽救民族于危亡的英雄,谴责鞭挞导致民族衰亡、断送民族前程的败类。
“民族利益”是史传文学作家评价历史人物、事件的基本价值取向。

苏美尔的《乌尔覆灭哀歌》是一篇富于艺术感染力的咏史诗。
乌尔是当时苏美尔的五大城邦之一,曾经一度称霸苏美尔平原。但在公元前二千年代初年,内有叛乱、外有强敌(埃兰人入侵),加上天灾而遭到毁灭性打击。
这篇距今四千多年前的诗作以这一历史事件为素材,融入神话内容,深切地表达了诗人对故国惨遭毁灭的沉痛哀思。
先写诸神离弃乌尔,乌尔一片破败荒凉,人们为乌尔遭毁而哀伤;次写乌尔主神、月神之妻宁伽尔四处奔走,请求大神恩利尔宽宥乌尔;再写恩利尔不听请求,降灾乌尔的情景:恩利尔呼风唤雨,只见狂风大作、大雨倾盆、烈火熊熊、洪水滔天,埃兰人横行劫掠,人们妻离子散,痛苦不堪,死尸横陈,哀鸿遍野,宁伽尔面对惨景而悲伤哭泣;最后写人们向宁伽尔谴责暴风,祈求再建乌尔,诗作虽然对乌尔覆灭这一历史事件作了神话式解说,但通篇洋溢着对故土和故土民众的深挚感情,对宁伽尔女神倾注着赞美,而对大神恩利尔——尽管他是主宰苏美尔人命运的主神,却颇为不敬,对“暴风”的谴责,实际将矛头,指向了大神(恩利尔就是风神)。

传记文学是古代埃及文学中最有特色的文类。
古埃及传记文学盛行与亡灵崇拜有关,传记是为传主死后审判和复活准备的,因而往往以炫耀为目的,对传主的功名业绩往往夸大其词。
但“夸大”不是“虚构”,还是以一定的史实作依据。
从现存的古埃及传记文学看,传主主要是国王、大臣、学者(祭司)或将军,他们的功绩往往与民族的发展、命运相系,在他们的功劳、贡献的夸耀性描述中,常常透射出民族自豪感。
《乌尼传》的传主是古王国第六王朝的一位大臣,他受命率军远征亚洲,凯旋而归,传中有诗:“这支部队安全归来,/它夺取了沙漠的土地。
/这支部队安全归来,/它把沙漠人的国家夷为平地。
/这支部队安全归来,/它拔除了沙漠人的堡垒。
/这支部队安全归来,/它砍掉了沙漠人的无花果树与葡萄树。
/这支部队安全归来,/它放火烧掉了所有的建筑物。
/这支部队安全归来,/它消灭了成千上万个沙漠人。
/这支部队安全归来,/它带回无数俘虏。”

诗中的炫耀自不待言,但确实洋溢着弘扬国威、征服异族的喜悦,基调与前述苏美尔的《乌尔覆灭哀歌》截然相反,但抒发的都是民族的情怀。
古埃及新王国时期不断向外扩张,因而产生“军功传记”,其中的民族豪情更盛。

《马来由本纪》(敦·斯利·拉南著)是创作于17世纪初的历史故事,记述了马六甲王朝成败兴衰的历史过程。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马来诸国的宫廷生活、王朝礼仪、外交活动、战事冲突、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丰富内容。
但表现得最突出的是马六甲昌盛时期在政治、外交、军事、文化方面扬名四海的成就和作为东南亚历史舞台中心的显赫地位,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勇谋兼具、武艺非凡、在外交场合和战场较量都多次维护民族尊严的民族英雄杭·杜亚的形象。
总之,与“颂诗”一样,东方古代的史传文学在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艺术再现中,渗透着鲜明的民族意识。
诗人、作家为民族历史上的“黑暗”而哀伤,为国家前途的“辉煌”而自豪;他们痛恨民族败类,颂扬民族英雄,字里行间跃动的是爱国热情和民族信念。
正是这些史传文学作品,使民族的历史资源增值,使一些民族英雄走出历史、超越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