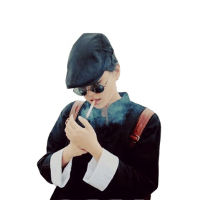我生于至正十五年的烽烟里,父亲在滁州城头挥剑时,太平陈迪家的屋檐下传来我的第一声啼哭。他策马奔回,在青石上刻下“到此山者,不患无嗣”,那刀痕里藏着乱世枭雄初为人父的狂喜。我的襁褓裹着起义军的战旗,幼年便知龙袍的重量——五岁执笔描红《千字文》,十岁随军祭祖,十三岁成为大明首位太子,每一步都踩着父亲用白骨铺就的阶梯。
一、儒袍与铁甲之间宋濂先生教我“仁者爱人”时,父皇正将胡惟庸的党羽悬首城门。那日我跪在奉天殿前,额头抵着冷砖为他求情:“滥杀伤国本。”父皇掷来的砚台擦过鬓角,墨迹在汉白玉阶上蜿蜒如血。后来马皇后偷偷告诉我,那方砚是郭子兴赏赐的旧物,父皇摔它时手在颤抖。我懂他的恐惧——从放牛娃到天子,他总怕这江山如元末流云般易散,却不知最锋利的刀,正是他亲手锻造的猜忌。
在西安考察建都时,我见秦王府的朱漆剥落如疮疤。二弟朱樉虐民致死的罪状在袖中发烫,却仍要替他向父皇求情。父皇骂我妇人之仁,却不知我夜夜梦见凤阳灾年的饿殍。若连兄弟都不能容,又如何容得下天下苍生?
二、东宫里的囚徒东宫的书架上,《贞观政要》与《大明律》间夹着四弟朱棣的边关捷报。他送来的人参我转赐太医,北疆的雪狼皮垫在监国宝座下。朝臣说我“宽仁”,藩王赞我“公允”,唯有父皇嫌我少了帝王狠绝。那年蓝玉在漠北屠城,我罚他三年俸禄,父皇却笑着将虎符塞进他手中——原来帝王之术,是要用鲜血浇灌忠心的。
最痛是洪武二十五年春。巡视陕西归来,咳出的血染红迁都奏折。父皇握着我的手说:“标儿,西安的城墙要再加高三尺。”他不知道,我最后的气力都用在为三弟求情——那个在封地铸铜人取乐的荒唐王爷,终究是我的手足。
三、未落子的棋局临终前,允炆的《削藩策》草稿藏在枕下。我多想教他:对待你四叔,当如驯烈马,既不能折其蹄,亦不可纵其性。可惜喉间涌上的腥甜淹没了教诲。恍惚间,听见父皇在孝陵痛哭,他一生杀伐决断,此刻却像个弄丢糖人的老农。
若天再借我十年,大明该是另一番光景:蓝玉不必因“谋反”被剥皮揎草,方孝孺无需血溅聚宝门,四弟的靖难铁骑永远困在燕山风雪里。可历史最残忍处,便是“如果”二字永远悬在棺椁之上。
今日东陵的残碑犹刻“兴宗”二字,那是允炆追封的孝康皇帝名号,后被四弟抹去。我躺在父皇子午线的东侧,看他龙驭宾天时,是否后悔没教会允炆:守江山光有仁心不够,还需懂得在龙鳞下藏一把匕首。
我这一生,困在储君名分里,既未能成为父亲期待的虎狼之君,也来不及做儿子需要的慈爱严父。唯愿九泉之下,能见马皇后纺车旁的油灯长明——那抹暖光,比奉天殿的龙椅更像我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