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晶源阅览趣事
2025-04-02 11:26:49
#律师来帮忙#
我国《人民警察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和公安部规定均明确禁止刑讯逼供,刑法亦设有刑讯逼供罪,并对致人伤残或死亡者按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根据最高检公布数据,1979至1989年间每年查处约360件,1991至1998年增至400余件,2003年前十个月也有400多件立案,尽管数据有限,但表明刑讯行为在1979至2003年间总体未见明显减少。公安部也承认问题严重,2002年全国派出所留置室发生百余起非正常死亡事件,群众谈“留置室”色变,反映出刑讯逼供在本世纪初仍较普遍。其背后深层原因在于“权力权利化”,即执法权力滥用成为个人意志工具。
权利,作为历史演进的产物,其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或同一阶段的不同文化背景下,被人们赋予了多样的理解。西方学者从利益、自由、法力、意志等多重维度进行阐释,而中国(含台湾、香港)学者则提出了权能、可能性、资格、界限等说法。尽管解读各异,但权利作为社会意识的本质,是对特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其核心概念围绕利益与意志的自主性展开。在众多观点中,本文倾向于两种解释:一是权利为正义原则和法律所赋予的利益与自由;二是权利是对自由需求受扰时的法律界定。权利就是法律对主体追求自由与利益行为的许可与保障,拥有权利,即意味着此追求获得了法律的正当性支持。
权力,如同权利,是人类社会发展至特定阶段的产物,其概念众说纷纭,包括效力说、力量说、公共权力说、工具说、国家意志说等。其中,本文倾向于“公共权力说”与“力量说”,认为国家权力源于个体在自然状态中无法克服生存障碍而自愿让渡部分权利,由此汇聚形成维护集体利益与自由的公共强制力。无论权力的外在形式如何变化,其本质始终是对社会或他人的一种强制性、支配性力量,而这种力量实际上是公民个体权利的集合体。因此,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根基,应当在于其是否保障了公民“自存”所必需的自由与利益。一旦偏离这一功能,国家权力的价值基础也将随之动摇。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权力是实现权利的保障,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持,个体权利难以落实;反过来,权利又是权力正当性的来源,失去保障公民自由与利益的功能,国家权力也失去存在的意义。区别在于,权利强调个体的自由和利益,具有可选择性;而权力则指向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对权力主体而言是一种不可选择的责任。因此,应明确区分两者,防止“权利权力化”和“权力权利化”。前者是指私权主体借助公权手段强制行事,如债权人通过公安机关讨债,破坏法律平等与市场秩序;后者则是权力主体将公权用于私利,表现为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严重侵害国家和人民利益,背离法治原则。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警察的职权亦源于人民通过宪法及人民警察法等法律的授权,权力的行使必须以维护人民利益和自由为前提,不能侵害公民权利。“十五大”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强调现代法治国家是法律至上的民主国家,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全体公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议会等组织形式,将国家权力授予国家机构,并由包括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在内的公职人员具体行使。所有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和限度内行使权力,因为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执行法律就是遵循人民意志,是对人民的尊重。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公安民警矢志不渝的根本宗旨。人民赋予公安民警以权力,这既是一种强制力量,也是一种支配力量,其核心目的正是通过公安民警依法运用这份力量,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打击犯罪是手段,守护人民权利才是终极目标。然而,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却是对公安民警权力功能的严重扭曲与背离。综观其原因,既有公安民警为追求更高的破案率和更快的破案速度而采取的不当手段,也有上级领导和社会舆论对侦破工作施加的巨大压力,还有深挖余罪的需求、荣誉感的驱使、犯罪分子的狡猾多变以及侦破手段的相对有限,更有极个别办案人员因心理问题而走上歧途。
刑讯逼供现象的本质,是权力功能异化为私人目的的过程,可概括为“权力权利化”。当办案人员以“多破案、快破案”为由实施刑讯,若其目的为保障公民权利,则手段与目的矛盾;若为个人或单位荣誉,则是以公谋私的“权力权利化”。迫于上级或舆论压力行刑,同样是借公权减轻个人负担的私用行为;而在无确凿证据下为“深挖余罪”而刑讯,或因侦查能力不足、心理失衡等原因行刑,则更是滥用公权、假公济私的表现。这些现象均表明,刑讯逼供行为并非单一执法偏差,而是权力背离其为民服务宗旨、异化为谋取私利工具的过程。因此,从法理上看,“权力权利化”正是导致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直接根源。
1
阅读: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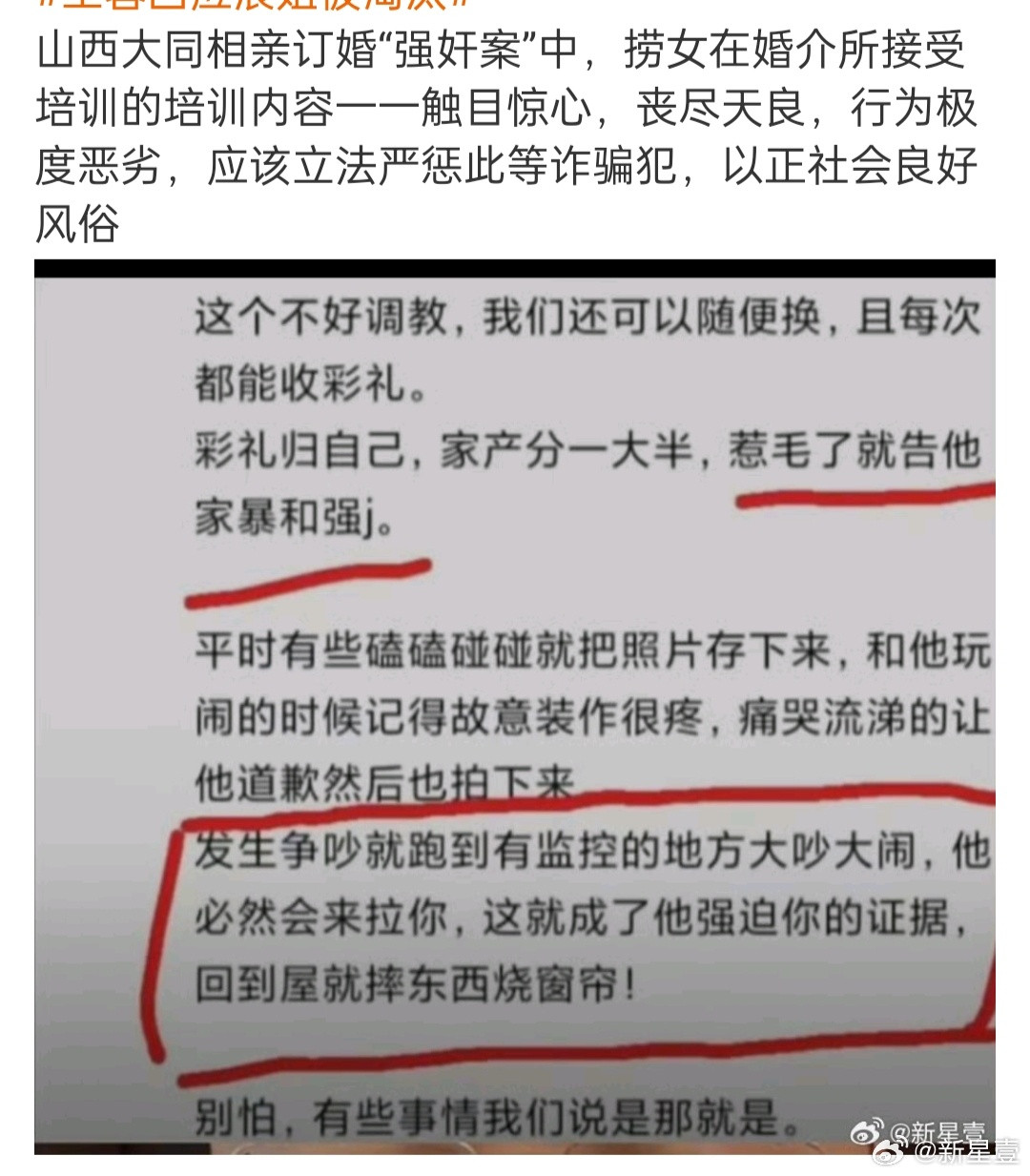

一叶舟
就是违法成本太低!就是没人把他们怎么样!刑讯逼供必须严刑俊法!
一叶舟
必须判七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