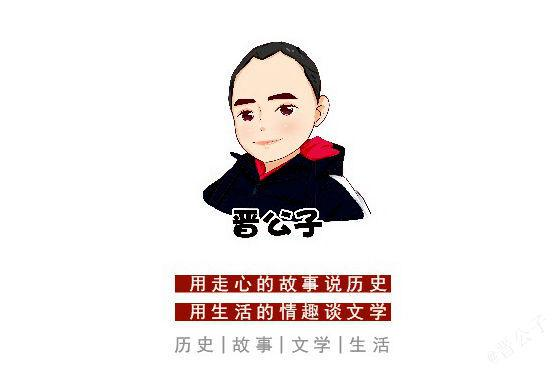本期话题公元前651年九月晋献公薨逝,晋国随即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流亡公子重耳和夷吾为争夺新君之位展开了激烈的角逐。重耳听从舅父狐偃的建议,拒绝回国即位的邀请,而夷吾则在大夫郄芮的策划下捷足先登。为何原本领先的重耳要主动放弃竞争?即位后的夷吾又会遭遇怎样棘手的麻烦呢?


公元前651年九月,晋献公薨逝。随即,中大夫里克发动政变诛杀骊姬与奚齐,晋国的各方势力由此迅速展开了新一轮的君位角逐。
这一回合的角逐复杂到什么程度?甚至连《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对其中的许多细节都不甚了了。
关于这件事,司马迁在《晋世家》中写道:
(献公)于是遂属奚齐于荀息。荀息为相,主国政。秋九月,献公卒。里克、邳郑欲内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乱,谓荀息曰:“三怨将起,秦、晋辅之,子将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负先君言。”十月,里克杀奚齐于丧次,献公未葬也。荀息将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齐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献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荀息死之。——《史记·晋世家》

里克究竟依靠什么人发动了政变?
司马迁说是“三公子之徒”,也就是故太子申生和两位公子重耳、夷吾的私属势力。这个结论的依据出自《国语》。《国语·晋语二》记载里克在政变之前同两位大夫荀息、丕郑紧急磋商,向他们二位询问了同样一个问题:
“三公子之徒将杀孺子,子将何如?”——《国语·晋语》

里克声称三位公子的属下对少主奚齐怨毒至深,誓要将当初骊姬迫害三公子的仇恨报复在奚齐身上。
但从事件的后续发展看,三公子之徒并未参与政变,里克也没有那么大的政治能量,将三位公子的私属势力统统整合到他的手中。政变其实是里克联合晋献公的近卫军首领七舆大夫发动的。在政变前打出“三公子之徒”的旗号就是虚张声势,里克想藉此讹诈荀息和丕郑,裹挟他们参与政变。
但让里克始料不及的是,荀息和丕郑都没有走他画出的那条道儿。

身为晋献公钦点的顾命大臣,荀息面对里克的恫吓无所畏惧,表示将忠实地执行晋献公的遗命,与少主奚齐共存亡。
于是手握兵权的里克一刀抹了荀息的脖子,让他与奚齐殉了葬。荀息要做忠臣或许并不出乎里克的预料,但丕郑撺掇里克作“曹操”可着实吓他了一跳。
丕郑说:
“夫国士之所图,无不遂也。我为子行之。子帅七舆大夫以待我。我使狄以动之,援秦以摇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赂,厚者可使无入。国,谁之国也!”
——《国语·晋语二》

丕郑的意思是,政变后只有扶立一位弱势的晋君,他和里克才能攫取最大的政治利益。照这样算来,公子重耳的背后有狄人的势力支持,而公子夷吾则可能与西邻秦国达成了某种政治默契,二位公子都太强势,必须将他们拒于国门之外。
按照丕郑的计划,里克将联合七舆大夫以近卫军控制住国内的政局,而他则出使戎狄与秦国,争取通过外交谈判说服这两方势力放弃对重耳、夷吾的支持。解除二公子的威胁之后,再从献公九子中另择一位弱势公子立为国君。
如此一来,“国者,谁之国也”——明面儿上还是姬姓当家的晋国私下里就是里克和他丕郑说了算了。丕郑的野心太大,他就差没公开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造反口号了。他的提议刚一出口就遭到了里克的否决,原因不为别的,里克的实力撑不起这么大的政治野心。


就在里克与丕郑商量新君人选的同时,朝廷中另一派亲近公子夷吾的势力——大夫吕甥与郄称也迅速行动了起来。
他们向夷吾传话说:
“子厚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国语·晋语二》
此时的夷吾为躲避骊姬之祸,逃到了梁国。来此之前,大夫郄芮指点夷吾:
“梁近于秦,秦亲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骊姬惧,必援于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是吾免也。”——《国语·晋语二》

梁国地近于秦,而此时主政秦国的秦穆公正是晋献公的女婿,故太子申生的妹夫。夷吾一旦逃亡梁国,摆出一副要与秦国连手的架势,骊姬势必生畏,不得不赦免夷吾以寻求秦国的谅解。
果然,在夷吾抵达梁国的第二年,骊姬命奄楚给他送来了一只玉环——古时候的官场惯例,一个官员犯了事儿,待罪于边境,听候朝廷的处理决定。朝廷如果授他一只环,那意思便是“还”,罪已赦免,他可以回国都去了;如果授他一只玦,那便是“决”,君臣决裂,他将遭到无情的惩罚。
骊姬送来玉环说明夷吾可能已经成功地搭上了秦国这条线。

现在骊姬、奚齐已死,吕甥与郄称一面催促夷吾尽快争取秦国的明确支持,一面遍告朝臣:
“君死自立则不敢,久则恐诸侯之谋。径召君于外也,则民各有心,恐厚乱,盍请君于秦乎?”——《国语·晋语二》
吕甥与郄称宣称,献公尸骨未寒,为臣者万不可有自立篡国之心。这话似乎就是针对丕郑的野心膨胀而提出的强硬警告。二位大夫建议作速确立新君,以免诸侯觊觎,趁虚而入。
至于新君人选呢?吕、郄说这就要看既是强邻又是姻亲的秦穆公怎么表态了——眼下夷吾是晋国各派系中与秦国接触最早最频密的,他当然最有可能博得秦穆公的力挺。

夷吾内结吕、郄为谋主,外攀秦国为奥援,这对里克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假设此时里克误信丕郑之计,做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梦,那他在朝中势必遭遇吕甥与郄称的激烈抵抗,而丕郑出使秦国恐怕也很难说服秦穆公放弃与夷吾的合作,转而支持里克篡权做贼。
对里克和丕郑来说,此刻务实的态度不是去奢求主宰晋国,而是要设法保住自己在新朝的一席之地。
因为夷吾的问鼎之势已是咄咄逼人,倘若他真在秦穆公与吕、郄大夫的里应外合之下成功上位,那就意味着里克与丕郑在新朝的权力结构中几乎无可避免地会被边缘化。要恋权固位,里克只剩下唯一的选择:主动拥立公子重耳返国继位。

可让里克意想不到的是,派去戎狄的使者传回消息,重耳婉拒了回国的邀请,表示不能胜任国君之重。
寄人篱下与九五称尊哪一条路更诱人?答案一目了然。其实重耳甫一接到里克的邀请,他的选择也是后者。但当他兴奋地告诉舅父狐偃“里克欲纳我”的时候,狐偃却当头浇了他一瓢凉水。狐偃说:
“夫坚树在始,始不固本,终必槁落。夫长国者,唯知哀乐喜怒之节,是以导民。不哀丧而求国,难;因乱以入,殆,以丧得国,则必乐丧,乐丧必哀生。因乱以入,则必喜乱,喜乱必怠德。是哀乐喜怒之节易也,何以导民?民不我导,谁长?”
——《国语·晋语二》

要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一定要在发轫之初夯实基础。只有根深蒂固,才能枝繁叶茂。
那什么是事业的基础呢?《三国演义》里的刘备说过,“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广树恩德、争取民心就是基础,它要比跨州连郡、万马千军来得更为重要。
所以陶谦让徐州与刘备,他推辞;诸葛亮劝刘备速取荆州,他又辞;庞统劝刘备突袭益州,他再辞。这个到了46岁高龄还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的男人最终靠自己苦心经营的仁义之名、人和之势践祚九五,与曹、孙两家鼎足而立。
对眼下的重耳来说,里克给他准备的这张龙椅便是“益州”。对取益州这件事,刘备曾说:
“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摷以急,吾以宽;摷以暴,吾以仁;摷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三国演义·庞士元议取西蜀》

狐偃警告重耳,此时如果仓促返国,你很有可能就要失信于天下!虽然当初为了躲避骊姬的迫害,逃窜到夷狄之地是情非得已。但毕竟你因此背上了背叛君父、背叛祖国的罪名。
虽然献公、骊姬已经相继离世,人身安全可以无忧,但叛国之罪并未洗刷干净。如果你重耳在这个时候顶着叛国者的骂名趁着先君大丧之际返国夺权,满朝文武将会怎么看你?天下诸侯又会怎么看你呢?
于是乎,虽然心有不甘,重耳还是照着狐偃的意思推却了里克的邀请:
“子惠顾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备洒扫之臣,死又不敢莅丧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辞。夫固国者,在亲众而善邻,在因民而顺之。茍众所利,邻国所立,大夫其从之。重耳不敢违。”——《国语·晋语二》


这厢,重耳拒绝了里克,而在那厢,同样叛逃国外的夷吾可是迫不及待地要收拾行囊回国继位去了。
因为他的谋主郄芮告诉他,天下事论势不论理,认钱不认人。为了说服里克与丕郑放弃重耳,支持自己,夷吾向他们许诺,倘若继承大统,将封赠里克汾阳之田百万,封赠丕郑负蔡之田七十万。
里克、丕郑不过担心自己在新朝地位不保,现在夷吾既然主动释放善意,还附送大礼,二位大夫自然乐得顺水推舟。

里克、丕郑易于说服,但秦穆公就大不相同了。穆公之所以这么积极地掺和晋国的新君之选,目的是要为秦国东进中原的宏图远略扫清障碍,光靠钱是肯定砸不动他的。
为了打动秦穆公,夷吾可是咬了牙,下了血本了:他向秦穆公许诺,只要秦国发兵,助他回国登基,他就把黄河西岸的八座晋国城池全部割让给秦国。

河西八城的归属不但影响到秦国的东进战略,同时也事关秦国的国防安全,(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旧文《秦穆公究竟算不算春秋五霸之一?》),这是一笔秦穆公无法拒绝的交易。
最终,正是河西八城这个价码换来了秦国的合作。在秦军的护卫下,夷吾回国即位,成为了晋国的新君——晋惠公。
夷吾成功地登上了晋君的高位,但他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当初急功近利,不计后果地向里克、丕郑和秦穆公开出了三张大额支票,现在债主们纷纷上门要求兑现了,“资不抵债”的晋惠公夷吾该怎么应付呢?
参考文献: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徐元诰《国语集解》
李尚师、李孟存《晋国史》
本文系小书房1538(XSF1538)的晋公子原创。已签约维权骑士,对原创版权进行保护,侵权必究!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
欢迎分享转发,您的分享转发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
— THE END —
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图片|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