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后,黄宗羲在化安山的石室中完成了《明儒学案》的最后一字,忽然回想起少年时代在诏狱外焚烧诉状的火光——那时他是奋力捣毁诏狱的复社青年;中年时四明山竹弩绷断的声音仍在耳边回响——那时他是抵抗清朝的浙江义士;而如今,他却在寒岩上静坐,成为后世称之为“蕺山学派殿军”的人物。八十五载春秋如刀斧般刻下:十六岁时锤断了诏狱的枷锁,四十四岁时倾尽家财募兵,五十三岁时凿石室藏下《明夷待访录》。临终前的大雪封山,老人将“党人·游侠·儒林”六字刻在砚底,也许这就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风起云涌的时代终于铸造了一个被历史裹挟的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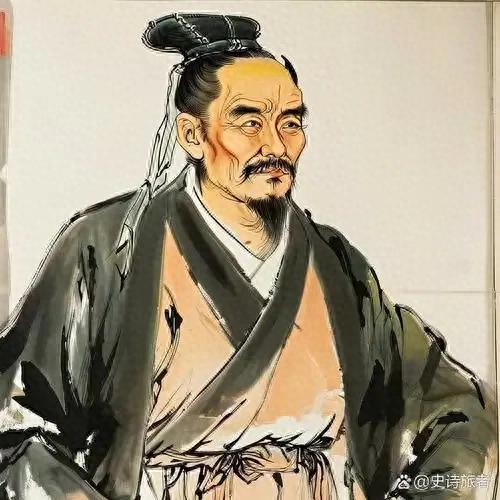
(1)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9月24日),黄宗羲出生于浙江余姚通德乡黄竹浦的一个官宦家庭。黄家自南宋以来世代为官,其父黄尊素当时担任宁国府推官,后因政绩卓著升任山东道监察御史,成为东林党在朝中的重要代表。这个书香世家的诞生之年,大明王朝已显现崩溃的迹象。北方五省大旱,河南的流民聚众起义,而万历皇帝深居宫中二十余年不朝,六部堂官空缺达二十四人。更荒唐的是,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时竟获赐河南良田两万顷,地方官员为凑足数额,强行划拨山东、湖广的熟田,致使数万农户流离失所。
天启六年(1626)春,魏忠贤以“东林七君子”之名将黄尊素与高攀龙、周顺昌等七人逮捕。三月,年仅十九岁的黄宗羲护送父亲北上,途中目睹押解官差对父亲的凌辱。根据《黄忠端公年谱》记载,途经苏州时,周顺昌因拒绝向阉党下跪而遭锦衣卫虐打致死,少年黄宗羲第一次见证了忠良的惨死。抵京后,黄尊素被投入镇抚司诏狱。这个专门拷打犯人的魔窟,“狱中席地皆砖,夏月则火燎烟熏,严冬则积雪没胫”,黄宗羲每天变卖衣物为父亲送饭,目睹阉党用“琵琶刑”折磨犯人的惨状。六月,黄尊素意识到自己难逃一死,咬破手指在囚衣上写下绝命诗,并秘密托付同乡将沾血的《国朝献征录》带出监狱——这部百余卷的明代人物传记汇编,后来成为黄宗羲研究制度兴衰的重要典籍。临刑前夜,黄尊素通过狱卒传话给儿子:“不必读时文,但不可不读史。”这句遗训彻底改变了黄宗羲的人生轨迹。当余姚家中接到噩耗时,七十一岁的祖父黄曰中在粉墙上疾书"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借春秋典故激励孙子复仇。这个充满血腥气的夏天,将温文尔雅的书香子弟锻造成了持锥刺奸的刚烈义士。
(2)崇祯元年(1628)正月,随着明熹宗的去世、魏忠贤的自尽,新帝朱由检开始清算阉党。当朝廷为东林诸君平反的诏书传到余姚时,十九岁的黄宗羲取出珍藏两年的铁锥——这正是当年他为父亲被押解时请铁匠特制的三棱锥,长七寸三分,可藏于袖中。五月初三,刑部大堂。当佥都御史许显纯被押解上堂时,这个昔日掌管诏狱的酷吏早已不见威风,但当他瞥见旁听的黄宗羲时,竟面露讥笑。
据《明史·许显纯传》记载,此人乃万历皇后外甥,仗着皇亲身份有恃无恐。主审官尚未开口,黄宗羲突然从证人席跃起,袖中铁锥寒光乍现。在场的衙役还未反应,他已跨过三尺公案,左手揪住许显纯的发髻,右手铁锥直刺其大腿。“这一锥为天启五年七月十三!”每喊一个日期便刺一锥,正是其父在诏狱受刑的日子。许显纯哀嚎着搬出皇亲身份求饶,黄宗羲厉声驳斥:“亲王谋反尚需伏法,况尔等阉党!”随后受审的崔应元更显荒唐,这个曾将黄尊素折磨致死的锦衣卫千户,此刻竟自称清廉。黄宗羲夺过衙役的水火棍,将其打翻在地,生生拔下整绺胡须。当他捧着仇人的须发跪在父亲灵前时,余姚老宅的松木灵位上还凝着两年前的血渍——那是黄尊素棺椁返乡时,少年咬破手指写下“仇雠未报”留下的印记。六月廿九日再审阉党李实时,黄宗羲刚取出铁锥,这个曾构陷东林党的太仆寺少卿便瘫跪在地,连声招供。刑部官员后来在结案文书中特别写道:“黄子当庭雪冤,刚烈罕有,虽逾矩而未究。”消息传遍南北,茶馆酒肆的说书人将其改编成《孝子锥奸传》,甚至出现“黄尊素魂附铁锥”的神异传说。这场震动朝野的复仇,使黄宗羲成为天下闻名的孝义典范。据说,那根行刺所用的铁锥后来被黄宗羲熔铸成镇纸,伴随其一生。

(3)崇祯三年(1630)暮春,二十一岁的黄宗羲赴南京参加应天乡试。在秦淮河畔的江南贡院,他遇到了复社领袖张溥、张采。这个以“重振古学”为名的文人集团,此时正举办三千士子齐聚的金陵大会。黄宗羲在《思旧录》中回忆:“见娄东二张主盟,以为得见东汉太学遗风。”此后八年,黄宗羲往来于江浙复社据点。崇祯十一年(1638)秋,当得知阉党余孽阮大铖在南京招摇,他连夜起草檄文。十月,百余名复社成员联署的《南都防乱公揭》张贴在南京国子监照壁,文中直指阮大铖“始焉诬陷清流,终则献媚阉宦”。这个曾为魏忠贤立生祠的奸佞,只得躲进牛首山祖堂寺,连日常采买都遣家仆扮作樵夫。但轰轰烈烈的清议运动难掩现实困境。崇祯十五年(1642)黄宗羲在《留书》中反思:“二十年来,文人以门户相争,较锱铢之胜负,于国计民生毫无裨益。”最令他痛心的是,当李自成逼近北京时,复社众人仍在争论《历代名臣奏议》的注疏体例。崇祯十六年(1643)深秋,黄宗羲回到余姚化安山,在龙虎草堂拜谒刘宗周。这位以“慎独”著称的大儒,要求弟子每日黎明即起。
山中五年,黄宗羲将父亲遗留的《国朝献征录》与刘宗周批注的《皇明经世文编》对勘,完成《弘光实录钞》四卷,其中对南明党争的剖析,已显露出后来《明夷待访录》的思想雏形。在刘宗周“证人之教”影响下,黄宗羲养成了独特的治学方法:每日晨起燃香计时,端坐抄录典籍,香尽方休。这种苦功使他练就“日读夜思,万言不忘”的本领,为其晚年编纂《明文海》、《明史案》等巨著打下根基。而牛首山上避祸的阮大铖,数年后竟降清成为南征向导,恰印证了黄宗羲“空谈误国”的论断。
(4)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消息传到余姚时,黄宗羲正在校勘《宋元学案》。他掷笔长叹:“文山(文天祥)当日,尚有江南半壁可守。”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监国,三十四岁的黄宗羲星夜北上,却在抵京当日就被阮大铖逮捕——这个当年被他驱逐出南京的阉党余孽,如今竟摇身一变成为尚书。
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攻破南京。趁乱逃回余姚的黄宗羲,听闻老师刘宗周绝食殉国的消息,在日记中写道:“乾坤崩裂,吾辈岂能苟活?”遂将祖产二百亩田契当街焚烧,当众宣布:“愿从抗清者,每人发银五两!”三日间聚集乡勇五百余人,这支以黄氏家丁、乡民为骨干的“世忠营”,成为浙东最早成建制的抗清武装。在四明山区的七百个日夜,黄宗羲摸索出独特的游击战术。他命士卒将毛竹打通关节灌入火药制成“竹节铳”,在海拔800米的华盖山主峰设瞭望台,用铜镜反光传递军情。
顺治三年(1646)冬,清军重兵围剿,黄宗羲率残部退守舟山群岛。当他目睹鲁王朱以海在战船上“日费千金置酒宴”时,在《行朝录》中写下振聋发聩的论断:“明亡非阉党之罪,亦非东林之过,实因君主视天下为私产。”(意译)顺治八年(1651)中秋夜,清军突袭舟山。黄宗羲长子黄百药为掩护妇孺撤退,身中数箭阵亡。
五年后,次子黄正谊在运送军粮途中坠崖,儿媳周氏闻讯自缢。最惨痛的是顺治十三年(1656),清军焚毁黄氏“续钞堂”藏书楼,三代珍藏的三千卷典籍化为灰烬,仅抢出残稿《弘光实录钞》——书页边缘仍可见火燎痕迹。顺治十八年(1661)四月,永历帝在昆明遇害的噩耗传来。
五十一岁的黄宗羲在《山居杂咏》中写下:“乱世苟活廿载余,故人零落半丘墟。”此时其家族谱系已残破不堪:兄弟五人仅存其三,子侄辈七人中四人战死,长孙黄千人在逃亡途中夭折。他在给弟子万斯同的信中坦言:“昔年锥刺阉党,自诩刚烈,今观之不过私仇;抗清廿载,方知制度之弊深植千年。”(意译)康熙元年(1662),黄宗羲将抗清期间所著《海外恸哭记》重新修订。在新增的《田制篇》中,他追溯万历朝福王占田旧事,指出“君主夺民之产,犹强盗劫掠”,这种认识比早年单纯反清复明的思想,已然产生质的飞跃。书稿完成当日,他把伴随自己二十年的佩剑熔铸为犁头,在化安山麓开垦出三亩学田。

(5)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当礼部“博学鸿儒科”的征召行文送至余姚时,六十九岁的黄宗羲正在续钞堂校勘《明儒学案》。他取出崇祯三年南京乡试的准考证——那张盖着“应天府印”的桑皮纸,在背面写下《辞征状》:“羲蒙圣朝容隐,苟全草野,敢希荣进?”特意将“崇祯”年号显露于折痕处,交由弟子万斯同带往北京。康熙二十八年(1689)重阳节,绍兴知府送来“乡饮酒礼”请柬:洒金红帖上印着“敦请故明翰林院待诏黄公”,这是清廷给予前朝遗臣的最高礼遇。黄宗羲命次子正谊将请柬原封退回,附上自撰的《辞乡饮酒礼贴》:“羲乃明室孤臣,非新朝耆老。”但他在退回的礼盒中,却悄悄放入新著《破邪论》——书中首次出现“康熙二十八年”纪年。这种矛盾姿态引发时人争议。顾炎武曾致信质问:“既用虏年号,何以拒征召?”黄宗羲在回信中解释:“不仕以示义,不死以示仁。”其书房悬挂的自书条幅更直白:“国可亡,史不可亡;君可替,道不可替。”康熙二十三年(1684),他默许弟子陈锡嘏将《明夷待访录》抄本赠予浙江巡抚,书中“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的论断,竟未遭文字狱追究。
康熙三十四年(1695)七月,85岁的黄宗羲预感大限将至。他强撑病体登上化安山,在父亲黄尊素墓旁自选墓穴,手书“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二十字命石匠镌刻。墓碑特意选用余姚本地的梅园石——这种石材遇雨显青,暗合其"明朝遗民"身份。临终前夜,他将珍藏的《弘光实录钞》残稿交给万斯同:“此中俱是血泪,他日修史可鉴。”下葬时,家人按其遗嘱将遗体置于石板,仅覆白布三丈——这是明代生员服制用布。陪葬品除了《明夷待访录》手稿,再无甚值钱之物。墓碑不署清朝年号,却刻“龙飞乙亥”(干支纪年),这种葬仪既恪守遗民气节,又默许新朝存在,恰似其晚年思想“守故国之节,开新民之道”的辩证统一。
三百年后,在余姚黄氏宗祠发现的康熙三十五年(1696)礼部咨文显示,清廷曾密令"黄宗羲著述勿禁勿传"。这种暧昧态度,使得《明夷待访录》在民间秘密流传。
光绪十年(1884),梁启超初见抄本时惊叹:“此真极大胆之创论!”谭嗣同更直言:“三代以下无可读之书,唯此例外。”现代史学家钱穆评价:“梨洲气节,守汉官威仪于文化,开民本先声于启蒙,当为明清之际第一完人。”当四明山的竹节铳锈蚀成泥,化安山的镇纸铁锥却淬炼出文明的火光。这位从诏狱血泊中走出的书生,最终在故纸堆里完成了对专制王朝最致命的刺杀——他用三百年后的回响证明,真正的复国不是龙旗再举,而是让《明夷待访录》里的每一个字都化作种子,在华夏文明的冻土下等待惊蛰。正如那句俗语:“风雷不袭堂前燕,星火偏燃劫后灰。”这簇从明末残阳里引燃的思想火种,终究在历史长夜里照亮了启蒙的新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