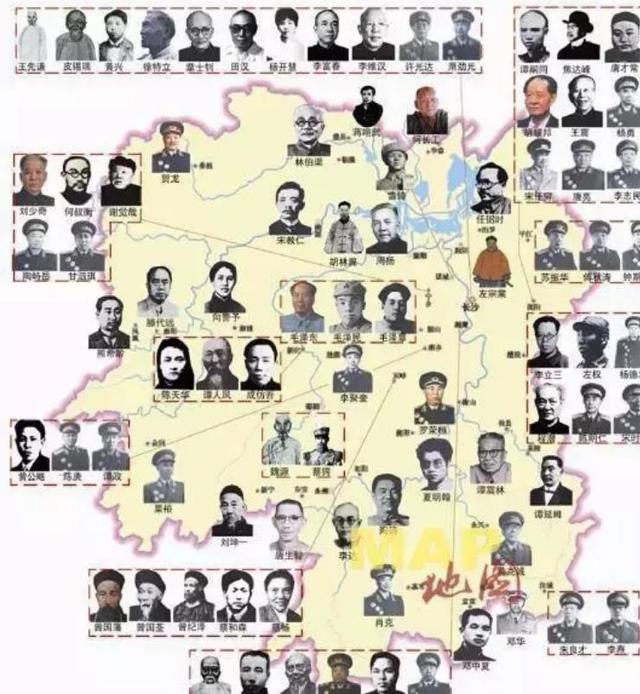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咸丰皇帝令各省组织团练对抗太平军,而最后只有湖南异军突起,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成了清王朝的救命稻草。不仅如此,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湖南人也是出尽了风头。

那么湖南为何会在太平天国时期迅速崛起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不用怀疑,就当时那个历史背景来看,恐怕也只有湖南人能拯救行将灭亡的清王朝。
嘉庆朝以前湖南是典型的落后分子清代各省中,湖南建省的时间较晚,雍正初年才正式设立湖南巡抚,省的规制才最终定型。就地理环境而言,湘西、湘南主要是高山、丘陵,民族成分复杂,是汉、苗、土、瑶、侗等族的聚居地。
以文化而言,湖南历来被视为“落后地区”,就连康熙皇帝也将湖南视为“化外之地”。清初时期,很多人都不愿意到湖南去做官,认为“无半人堪对语”。

文化落后也反映在科举考试上,康熙朝湖广分省后,湖北的乡试中额是湖南的三倍。乾隆一朝开了28科,湖南籍读书人只考中了39个进士,平均下来每科只有1.4人,远远低于每省11人的平均值。
科举功名少做官的自然就少,做官的少当大官的概率肯定也不高。据不完全统计,从顺治朝到乾隆朝凡一百五十余年,湖南籍官至巡抚侍郎以上的只有8人,这个账面数字十分拉胯。
后来曾国藩由四品骤升二品侍郎时,就颇为得意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王闿运等学者也不讳言,承认“湖南人物、罕见史传,自唐、宋至明,诗人万家,湘不得一二”,这也能看出湖南这块土地,历史上确实不盛产文人、高官。

经济方面,湖南从崇祯八年至康熙十九年的45年时间中,湖南大部都处在战乱之中,时人描述为“数百里人烟俱绝,历二十年陆续得归者十仅二三”,直到乾隆末年,湖南的经济才逐渐起色。
经济、文化的发展提升了地主阶级的凝聚力自嘉庆以后,湖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有句话叫做“湖广熟天下足”,实际上湖北并不是产粮大省,粮食供应还得靠临近的湖南、四川接济。所谓的湖广熟,只是单指湖南。
除了农业以外,各行各业也都迅速发力,凭借得天独厚的水路交通优势,北可出长江,南可至广州,至道光晚年,长沙、常德、衡阳等地的商业已十分繁荣。

经济与文化是相连的,借助岳麓书院文化堡垒的辐射作用,湖南大力发展文化,一大批文人士子跻身官场。前面说到,嘉庆以前湖南官至二品以上的不到10人,而道光三十年时,官至督抚者已有7人之多,科举中式人数也比此前提高了一倍。
道光朝,湖南出现了一大批杰出官僚和学者,如唐鉴、贺长龄、陶澍、魏源、曾国藩、李星沅、曾国藩,等等。
经济取得发展,财富也在增加,这就增强了湖南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封建时代,地主与农民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湖南几十年来的经济红利,主要落在了地主阶级手里,而农民的生活却越来越困苦,两者的矛盾也就越尖锐。

清代民间最活跃的几个反清组织在湖南一直很有市场,如天地会、白莲教,以及苗族、瑶族与汉族的争斗更是接连不断。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湖南地主与农民之间爆发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几乎每年都有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如此激烈的阶级对抗,在全国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长期的争斗,让湖南的地主阶级养成了勇武好斗的性格,他们在民间组织力量对抗各种农民武装,几乎在各府各县,这类非正式的武装力量,已经取代了地方官府。所以后来曾国藩组建湘军时就有现成的队伍,拉来就能打仗。
 湖南官僚大多属于理工类实用人才
湖南官僚大多属于理工类实用人才乾嘉时期汉学在全国风靡一时,但湖南读书人推崇的却是程朱理学。就拿同时代的左宗棠和李鸿章对比,就会发现他们的知识结构是完全不同的。
左宗棠17岁之前读的是四书五经和先秦儒学,这些都是科举考试的法定内容。17岁以后,左宗棠在云贵总督贺长龄、城南书院山长贺熙龄两位恩师的指导下,系统读完了《皇朝经世文编》和魏源的《圣武记》、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等等。
这些著作是科举之外的实用性内容,也就是说,左宗棠在少年阶段接受了系统的儒学训练,打好了扎实的文化根基,青少年时代又接受了系统的理工类训练。

李鸿章是安徽人,他和江南省份的读书人一样,完全是冲着功名而去的,他的青少年时代都在规规矩矩攻读“时文”。
用现在的话说左宗棠是清华理工类毕业生,而李鸿章就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生。这种知识结构的不同,在日后的仕途和作为上,也会体现出巨大的差异。
嘉道时期,湖湘派传承的儒学是将修身和实践相结合,目标是引导读书人追求“内圣外王”,所谓的“内圣”是将自我言行修炼到无限接近圣人的境界;所谓的“外王”是将学问和实践结合,按照孟子的“王道”去教化群众,以建立人民满意的大同之世。
社会承平时期,像左宗棠这样的实践型人才未必有大出路,但是到了乱世,经世致用之学就有了广阔的天地。要不然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幕下,也干不出那么大的动静,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他学以致用,在军事、地理等方面有独到的见解。

经济文化得到发展,地主阶级勇武好斗,加上读书人学以致用,种种因素组合在一起,就给湖南人注入无穷的力量。后来曾国藩将这些力量聚拢起来为己所用,尽管有时势造英雄的成分在里头,但湖南的崛起非曾国藩一人之功,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