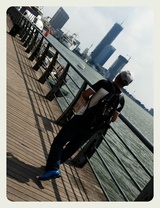藏北羌塘的“无人区”是一个充满禁忌的词汇——它意味着稀薄的氧气、诡谲的天气,以及地图上大片的空白。在这片面积堪比浙江省的荒野中,每6平方公里才能遇见一个人影。而我们此行的目标,是藏北文布荒原上那座被遗忘的圣湖:当惹雍措。它与达果神山相依,位列藏地“四大圣湖”之一,却因偏居羌塘腹地,成了最神秘的存在。当地人提起它时,语气中总带着一丝敬畏:“那是苯教的神灵栖居之地,连风里都飘着古老的咒语。”


在十几年前的尼 玛,我们问当地的人都说不清楚去当惹雍措该怎么走,只知道是往西南方向。出尼 玛我们问了好几个司机,才有一辆白色的2020客货车正好走那个方向,于是我们跟着这辆车走,去探寻苯教的圣湖当惹雍措。当惹雍措距尼 玛县一百多公里,距离不远,但路极为难走,还要翻过一座5000多米的高山,路的坡度很大,但风景秀丽,与大北线上其它地方又有不同。


怪不得在尼 玛县问询时,对去当惹雍措连藏族司机都摇头:“去当惹雍措的路,是牦牛的蹄子踩出来的。走上这条路我们才理解,”所谓的“路”,不过是车辙在碎石滩上碾出的模糊痕迹。越野车像醉汉般颠簸,车窗外的景色却愈发魔幻:赭红色的山崖如巨兽脊骨般耸立,蓝得发黑的云层压向地平线,成群的藏野驴在远处倏忽掠过,仿佛荒野的哨兵。


关于达果神山与当惹雍措的传说,在文布地区的牧人口中代代相传。远古时,藏北寸草不生,山神达果冒险潜入堆龙河谷盗取青稞种子。归途中,他遭到众神围剿,最终只护住几十粒种子。妻子当惹雍措以乳汁浇灌,竟在荒原种出第一片青稞。牧民们围着金色的麦田欢呼时,这对夫妻化作神山圣湖,从此守护着文布的土地。


记得在文布村我们拍村民求雨的仪式时,一个村民递给我一块糌粑用生硬的普通话说:这是用当惹雍措的水和的面,糌粑的味道很甜,会甜进骨头里。我嚼一口,还真是的,粗粝的口感中确有淡淡的奶香。这里的玛尼石堆也和别的地方有所不同,刻满经文的玛尼石,图案却不是常见的佛塔莲花,而是一顶白色尖帽——那是苯教“尔莫泽杰”法帽的象征。


在这儿简单说几句关于苯教。苯教是雪域高原最古老的信仰,远比佛教更早扎根于此。它的历史可追溯至象雄王朝,那时的巫师“苯波”通过吟唱咒语与天地对话,用白色石英堆砌祭坛,在煨桑的烟雾中窥见神谕。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引入佛教,苯教逐渐退居藏地边缘。后世史书轻描淡写地将它定义为“杀牲祭祀的巫术”,却鲜少提及:第一位藏王聂赤赞普是由苯教僧团加冕,藏文的雏形源自象雄文字,甚至转山、挂经幡等习俗,都流淌着苯教的血液。


曾经在拉萨时有一位专门研究苯教的学者告诉我:“很多藏族年轻人以为,佛教到来前西藏是一片野蛮之地。但当你站在当惹雍措边,听着风声里那些未被佛经覆盖的古祷词,就会明白——西藏有两副面孔,一副属于佛陀,另一副属于更古老的神灵。”这段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让我在心中产生了对远藏于羌塘腹地圣湖当惹雍措的想往,现在我终于有机会目睹并亲近她,这种感觉不断地激动着我。



一路上星星点点的湖泊很多,面积都不大,但景色极为秀美。沿途还经过了一处政府为游牧家庭修建的藏式民居整齐排列,却大半空置,窗框上积满灰尘。问遇到的牧民说“房子很好,但我们的牦牛没地方住啊!”这话确实是道出愿望与现实的矛盾。来过西藏的人都知道,定居的藏式房屋基本上是一层牲畜、二层住人。而对于逐水草而居的牧民而言,定居意味着切断与神灵、自然的古老契约。那些新建的房屋,如同一个个现代文明的问号,叩击着传统与变迁的边界。当然,我期盼着牧民们能安定下来,不知现今如何了?


感谢诸位友人拨冗莅临狼窝,诚望不吝批评指导。欢迎各位留言点评、转发、分享、收藏并关注本号,您的支持实乃老狼创作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