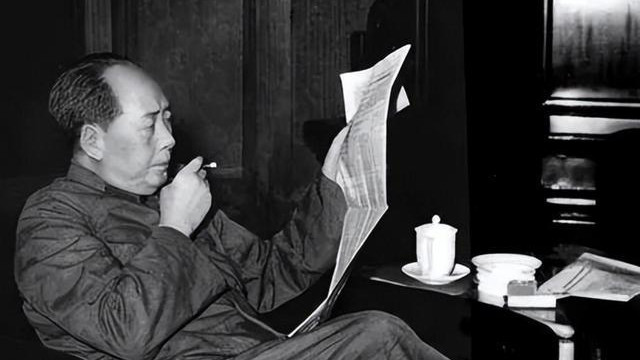张治中,一位终其一生奔走于中国和平道路的将军。
周恩来说他“既复杂又简单”,这话其实精准得很。
复杂在他的身份,国民党高层、军界重臣;简单在他的信仰,始终如一地认定一件事:国家不能乱,百姓不能苦。
他为和平奔波不止,解放前后皆如此。
周恩来与他,一个是共产党顶梁柱,一个是国民党大员。本该势同水火,偏偏惺惺相惜。
张治中与周恩来结识最早,合作最深。
许多后来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都藏在他们的对话中。
早年相识,一见如故1925年,广州黄埔岛,时局风云激荡,黄埔军校应运而生。
一所军校,却不仅训练枪炮,更孕育信仰与理想。
就在这所军校里,周恩来与张治中初次相识。

一个是政治部主任,思维敏锐,谈吐儒雅,学识广博,处事果断;一个是教育长,心胸坦荡,性格爽朗,军政兼修,稳重沉毅。
表面分属两党,实则志同道合。一见如故,不过如此。
他们常在课余长谈,言辞犀利,观点交锋,却从无隔阂。
谈教育,也谈国家;论战术,更议未来。
周恩来的气度、才华与人格魅力,令张治中钦佩不已。
多年后,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坦言:“他谈吐风雅,风度翩然,学识渊博,实乃罕见。”
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对中国命运的判断几近一致。
国家向何处去?民族如何崛起?两人多次交谈,竟无根本分歧。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在他们身上,竟真实得令人惊叹。

张治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保守军人。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接受革命思想,坚定支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这种政治认同,为他与周恩来的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周恩来在黄埔讲课,张治中总是静坐一隅,悉心旁听。
耳濡目染,日积月累,张治中渐渐走近共产党。
他最终主动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没有立即答应。他理解张治中的热忱,却更清楚时局的复杂。
国共虽合作,但暗涌已生。共产党曾与国民党约定,不吸收其高级将领入党。张治中身份特殊,贸然接纳,势必引发不测。
于是,周恩来郑重其事地上报中央。
不久后,答复来了:婉拒入党请求,但表明支持态度。
周恩来将这决定原原本本地转述给张治中。
张沉思良久,终释然开口:“中共的意见有道理、有远见,我就继续干国民党吧。”

张治中虽然未能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却从未因此疏远周恩来,反倒情谊愈加深厚。不是泛泛之交,不是普通朋友,而是真正的知己。
他们彼此信任、互扶互助,哪怕风雨如晦,立场对立,也从未动摇这份情感。
那是黄埔军校最热闹的一段日子。
周恩来和邓颖超要结婚了。革命年代,生活清贫,事务缠身,两人原本打算一切从简。
但张治中得知后,当即皱起眉头。
他一句话:“成亲是人生大事,岂能如此草率?”说完,转身便开始张罗。
他四处通知黄埔同僚,还自掏腰包,办下两桌体面酒席。
菜肴虽不奢华,却热气腾腾、分量十足,桌上摆着的,是朋友间最真挚的祝福。
那天张治中破天荒开怀畅饮,笑声不断,亲自上阵灌酒,把新郎官周恩来灌了个东倒西歪。
场面喜气洋洋,气氛热烈得很。

没有豪华礼堂,没有盛装宾客,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彼此拼过命的兄弟。
这就是他们的婚礼,简朴却不简单。
多年以后,邓颖超谈起往事,依旧感慨万分。
营救我党同志1945年,重庆。
国共谈判如火如荼,尘埃落定之际,《双十协定》终于签署,一纸协议,写下和平承诺,却也写下无尽博弈的序章。
协议甫成,蒋介石即派张治中赴新疆,处理伊犁、塔城的紧急事务。

消息传至周恩来耳中,他心头一紧——那里,还关押着一批我党同志,命运未卜,生死不明。
于是,在张治中动身前,周恩来专程嘱托。
他没有套话,没有绕弯子,只一句话:“我们有同志被盛世才扣押,至今下落不明。现在《双十协定》明确写入释放政治犯,你到新疆后,务必设法营救,并安全送回延安。”
张治中没有犹豫,答应得干脆。
他不是那种喜欢空话的人,承诺一出口,就意味着责任扛上肩。
几个月后,他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
一到任,他立刻着手执行营救任务。
他先派人秘密探监,确认我党同志的真实状况,随后亲自批示改善伙食,准许活动自由。
接着,三封电报接连飞往南京,全部直指核心——执行协定,释放被关押人员。
蒋介石起初迟疑,但张治中的坚持,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最终让他不得不点头放人。
张治中拿到批准的当天,立刻行动。

他亲自制定详细护送方案,每一环节都安排得一丝不苟。
他严令护送人员注意分寸,“这是护送,不是押解”,不仅要保障安全,还要展现应有的尊重。
全程电报汇报,层层请示,凡事“只要按我指示做,责任我担”。
从乌鲁木齐到兰州,几千里路,局势紧张,交通混乱。
他特地发电甘肃、陕西、山西沿线三省的主要官员,说明情况,通报身份,强调——这批人员是经蒋委员长亲自批准释放的,请务必配合放行,不得出差错。
他甚至提前通知了周恩来,安排延安方面接应。
一切井然有序,一丝不苟,只为兑现一句承诺。
1946年7月8日,131位被囚同志安全抵达延安。
而这背后,张治中顶住压力、力排万难,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在那个火药味愈浓的年代,国共双方早已剑拔弩张。若非张治中敢作敢为,后果不堪设想。
晚年肝胆相照1949年4月1日清晨,北平南苑机场格外安静。
一架从南京起飞的飞机缓缓降落,舱门打开,一行身着便装、神色凝重的国民党谈判代表鱼贯而出。
领头者正是张治中。此刻的他,虽仍代表国民政府,却早已将“和平”二字视作比官位更重要的担当。

这是一次特殊的飞行,飞越的是长江,也是国共之间最后的政治缝隙。
当天,周恩来亲自前来探望老友。
两人谈了很久,不绕弯,也不寒暄。
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渡江准备已就,局势正在急转,或许仍有转圜之机。但你若返回南京,国民党特务不会放过你。”
接着话锋一转,语气陡然沉重:“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如今不能再对不起你。”
这是掏心窝子的话。张治中听完,沉默良久,点头。
他,留下了。
不久之后,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张治中一家也悄然从上海秘密转移至北平。
这次行动极为敏感。

周恩来反复交代各环节细节,连飞机停靠位置都亲自确认——“不要停在候机楼前,必须远离人群,以防混进特务。”
他命令北平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王拓守守在电台旁,昼夜联系地下党,务必找到张家人。
每一处线索、每一次移动,都要向他报告。
地下党终于在上海找到张夫人和孩子。
转移路线、接送车辆、登机时间,全部由周恩来一一审核。最终,张家人安全抵达北平,躲过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暗杀。
当天晚上,六国饭店,周恩来设宴款待张治中一家。氛围平和,不见政治紧张,更像是一场久别重逢的家宴。张治中脸上久违地浮现笑容。他坦言,自从投身军政以来,从未如此轻松,三十年第一次放下担子。
三个月间,他几乎过上了“北平观光客”的生活:游览名胜古迹,听大鼓书,赏四大名旦的京戏。日子慢了,脚步也轻了。
但快乐之余,张治中心里其实并不轻松。

他曾私下坦陈:“我是国民党的干部,又是蒋介石的旧部。在别人眼中,我是他身边的心腹。但他反共,我却主张联共;他主战,我却坚持和平。如今一来北平就不走,别人会不会说,我这个干部叛变了领袖?”
这个问题,他没法回避。
更现实的问题也在逼近——经济拮据。
张家入北平后,一度陷入困顿。他只好让儿子张一纯去找傅作义借钱。
傅作义开门见山:“借多少?”张家人不好意思,只说250元。
傅作义二话不说,挥手让人取来500银元。
消息传到周恩那里。不到一周,他派人送来一封亲笔信。
开头就是道歉,然后写道:“不知你们经济上如此困难,特拨款6000元,供你们使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百废待兴。周恩来身为总理,日理万机,每日行程排得密不透风。但即便如此,他仍时常抽出时间,悄然造访老友张治中。在忙乱的政务与纷繁的国事之间,他始终没有忘记那个曾并肩奔走、肝胆相照的朋友。
他们常在家中促膝长谈,不谈权势,不谈利益,只谈往昔的岁月与共同走过的路。周恩来对张家人的关怀,早已超越普通友情的范畴。
生活琐事、家庭变故、子女成长,哪怕是再小的事,他也会亲自过问,事无巨细。
张治中晚年饱受神经性腿疾折磨,反复发作,行走困难,身心俱疲。
周恩来得知后,每次出国访问,都会悄悄带回适用药物。药到人到,从未间断。他不曾亲自出面,而是让邓颖超带去。
在张治中去世后,机要秘书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封邓颖超的亲笔信,墨迹清晰,字字情真。
信中写道:“恩来告我,你需要虎骨胶治病,现将尚存的两盒送上,以供应用……另送你燕窝一个,请哂收。”
这是一位国家领导人对老友病痛的挂念,对生活细节的体察。
而这份挂念,还延续到了下一代。

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曾向周恩来表达过想学电力技术的愿望。
周恩来没有立即表态,也没有敷衍,而是悄悄记下。
数日后,在一次家庭小聚中,他突然问起张一纯的学业进展。
话音刚落,便转头对陈云说:“文白的二儿子想搞电力,就让他去吧。”
几天之后,北京一所新创办的电力学校就送来了入学通知。
这就是周恩来。他不轻许诺,但一旦记在心里,必定办到。
张治中逝世后,周恩来依然将张家挂在心头。
哪怕到了1975年底,他自己已卧病在床,身心俱疲,却仍托秘书和总理办公室主任前去看望张家亲属,转达问候,仔细询问是否尚有困难需他帮忙解决。
更令人动容的是,临终前,周恩来还将自己的全部稿费与省吃俭用存下的工资,共计五万余元,亲自嘱托送往张治中家中。
那已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岁月,他仍念念不忘的,是一位故人。
回望二人一生的交往,从黄埔军校相识的青春少年,到政见不同时的对立对手,再到年华将暮、惺惺相惜的忘年知己。
他们不是一路人,却走了一段最珍贵的路;他们不是同一党,却成了最真诚的朋友。
这段友情,没有张扬的誓言,却有岁月为证。
最终,留下的,是一段足以写入史册的情义,也是一种最深层、最动人的信任。
这或许就是“知己”二字,最本真的模样。
参考资料:亦敌亦友真兄弟周恩来与张治中的交往
许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