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吏部经铨选程序后,郑重开列各州、县等官职的任命名录。彼时,恩监生郑庆,获外放任职,其履职之地为山东东平州,职位乃州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进士崔映辰,则被委任为四川荣昌县知县。

从常规制度逻辑审视,吏部此番安排似有悖于既定规制。依据传统铨选原则,于初次授官环节,进士出身者所获官职,通常较举人及贡监生出身者更为优渥。
在此,不禁引发思考:此类问题缘何产生?是否意味着,在官阶体系中,正七品的知县在实际职权或地位等方面,确实逊色于从六品的州同?
【州同、州判的性质比较特殊】
在清代的行政区划体系中,州这一行政建制细分为直隶州与散州两类。与之相应,执掌州务的知州,其品秩存在差异,直隶州知州为正五品,散州知州则为从五品。
州同与州判作为知州的佐贰官员,为与知府的佐贰——同知、通判相区分,故而简称为州同、州判。就清代的职官设置状况而言,州同与州判的设置并非广泛普及。事实上,在同一州内,这两种职务通常不会同时并存。其设置情形大致分为三类:或设州同,或设州判,抑或两者皆不设置。

在清代官制体系里,州同这一官职品级恒定,无论直隶州或散州,皆为从六品。关于州同的任命,清代官制确立了一项重要准则,即初次授任此职之人,依例需从举人、贡监生群体中选拔。
州判一职亦复如是,其品级为从七品。依制,初授此官职者,仅限于贡生与监生经选拔后担任。
在雍正统治时期,针对贡监生考职事宜,朝廷实施了一系列限定措施。其中明确规定,于考职评定中获一等者,仅能被授予州同之职;而评定为二等、三等的贡监生,则分别以县丞、教谕之职任用。
乾隆元年,相关制度正式确立并成为定制。每逢正科乡试举行之际,针对贡生与监生,亦会同步开展考职活动。依据考职成绩,划分等级并予以相应任用:考列一等者,委以州同之职;考列二等者,授以州判之任;考列三等者,则选用为县丞或主簿。

实际上,自乾隆时期起,州同与州判这两个职位已明确成为贡监生所专司之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拥有进士出身的士人,往往对此类职位持有轻视态度,并不屑于就任。
其理甚明,贡监生本质上仍归属于“高级秀才”这一类别,实则尚不及举人阶层。反观进士出身者,皆为天子门生,属极为稀缺之人才。鉴于此,朝廷断不会委派此类人才出任佐贰之职。
在清代的官场生态中,存在着基于出身划分的阶层体系。其中,翰林与进士位列上层,举人地位稍逊,荫生和贡监生则处于更次层级。这种阶层差异显著体现在官员的授职安排上,以正印官与佐贰官的区分作为具体表征。
在仕途晋升体系中,州同与州判皆具备凭借自身砥砺奋进,跻身正印官之列的可能性。以州同为例,依循既定规制,若获升迁,其可擢升至京县知县、散州知州之位;亦有可能调往京城,出任各部主事之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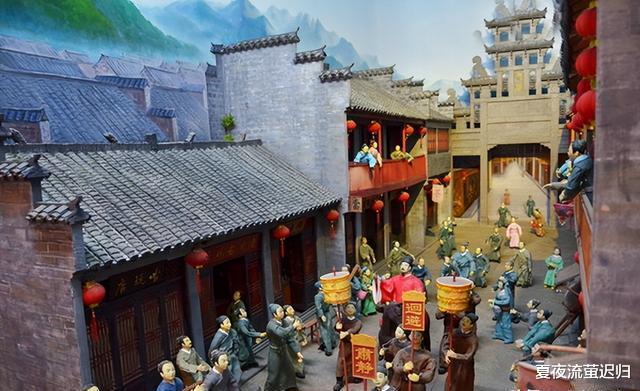
依据相关制度,州判晋升时,通常会擢升至知县、京县县丞、国子监典籍或典簿等职位。然而,就初次授官而言,贡监生面临着颇为严苛的限制条件。不仅如此,在仕途升迁进程中,贡监生相较进士,明显处于劣势地位。
【从六品州同不及正七品知县】
在清代官僚体系中,官员虽以品级作为等级划分的基本依据。然而,当官员品级差距处于相对微小的区间时,具体职掌便成为衡量其实际地位与权力的关键要素。
在封建官僚体系中,知县虽官职品阶相对较低,却作为执掌地方印信之官员,肩负着治理一方黎庶的重任,其职责至关重要。清代官制呈现出一种独特态势,无论是知府、知州,抑或知县,均施行“长官负责制”。此制度与明代正印官、佐贰官相互制衡的机制存在显著差异。

以知县这一官职而言,其肩负着一县治理之重任。于县域之内,无论是诉讼案件的审理裁决、田赋等各类政务的操持管理,还是缉捕盗匪、肃清奸佞,乃至文教事业的推进、农桑生产的督导,皆在其职责范畴。因知县直接与百姓接触,处理诸多基层事务,故而素有“亲民之官”的称谓。
在古代地方行政架构中,县丞虽为知县之佐贰属官,却并无独立施政之权。即便出现知县职位空缺,或因公差离境等情形,县丞亦无权代行知县之政务。此时,督抚衙门通常会遴选合适人员,委派其临时署理知县之职,以确保县域政务的正常运转。
与之类似,州同作为知州的辅助官员,其职能与县丞并无本质差异。一般而言,州同在知州的统筹指导下,负责特定领域的事务管理,诸如钱粮征收、治安巡捕、马政运营、水利兴修、海防巩固以及河防维护等工作。
以一种非比附的方式阐述,知县与州同的职掌,在行政职能体系中有如当代县委书记与负责相对边缘领域事务的副市长之关系。尽管州同在行政层级上略高于知县,然而,从实际权力范畴而言,知县所握有的实权,相较州同更为显著。

在清代职官体系中,州同与知县不仅在职掌方面存在差异,于经济待遇层面亦有显著落差。自雍正朝起,清朝推行养廉银制度,此制度下,官员养廉银数额依职务而定。具体而言,作为正印官的知县,相较于佐贰官的州同,所获养廉银数量数倍于后者。
据非详尽统计,知县所获养廉银数额,约处于800两至2000两区间;相较之下,州同的养廉银仅为200两至600两,二者之间存在数倍的差距。
若论合法收入,其间差距尚处于可接受范畴;而涉及陋规收入,则呈现出霄壤之别。州同,作为佐贰之职,在获取陋规钱财方面机会稀缺。即便偶有情形,所获亦不过是知州在分配过程中,如牙缝中挤出般,给予的些许零星碎银而已。
与其他官职有所差异的是,即便是秉持清正廉洁操守的知县,在其整个任期内,通过各类途径获取的财物,保守估计亦可达数万两白银之巨。
再者,吏部于地方官员考核体系中,尤为侧重掌印官的擢升。以散州知州职位出现空缺为例,在此情形下,知县通常被列为首选继任人员。仅当知县候补人员匮乏时,才会转而将州同视为替补人选。

故而,在清代职官体系中,从六品的州同,于职权范围、政务处置重要性等诸多层面,均难以与正七品的知县相提并论。此情形堪称清代官制中品级与职务配置存在差异的典型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