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时候,300多亿那真是多得吓人,想想看,咱们国家那会儿一年的军费开支才251亿呢。
有个人被指控卷入了这起巨额款项的贪污事件,出乎意料的是,这人竟是小平同志的大儿子邓朴方。
对于那些尖锐的质疑声,邓朴方面带正气地回应:“谁能帮我找出那300多亿存款,说是我的?我其实只要1%就足够了,剩下的全都打算捐给国家。”

心胸开阔的人行事光明磊落,心胸狭窄的人则总是忧心忡忡。邓朴方是怎么做到能这么从容不迫地应对那些指责和批评的呢?
【刘伯承:不能跟我儿子撞名,赶紧换一个】
1944年4月16号,那时候抗日战争虽说已经到了咱们反攻的时候,可八路军在根据地里头,日子还是过得挺不容易。
在一个响亮的哭声回荡在天际的时刻,邓朴方来到了这个世界,地点是山西省左权县的麻田村。他出生时白白胖胖的模样,就像是给那些日子过得挺苦的抗日战士们送上了一份短暂的欢愉。
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困难日子里,宝宝要是长得白白壮壮的,那就预示着以后日子能过得美满。心里装着让以后的中国老百姓都能过上安稳日子的愿望,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小平同志,特别喜欢大家伙儿叫他的儿子胖胖。

不过,“胖胖”的妈妈卓琳同志因为奶水不够,没法亲自喂他,所以就把他送到了麻田镇云头底村的郭金梅家里,让他当寄养的孩子,还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奶云”,就是说他是云头底村吃奶长大的娃。
但对小平同志而言,这背后含义更深。“奶”嘛,就是咱老百姓最开始吃的口粮,“云”呢,就像藏着雨水,能给所有东西带来滋养。尽管这只是个小名儿,可也显露出小平同志想让全中国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的坚定心思。
在我党的历史长河中,将亲生骨肉托付给普通百姓,这一举动实乃屡见不鲜。尤其是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面对严峻的形式和压力,众多党的高级领导人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把子女暂时留在路过的乡亲家中,这其中甚至包括了毛主席这样的伟大领袖。

但这说到底是亲骨肉分开,要不是实在没办法,天底下哪有父母乐意让孩子去别人家,特别是那些被寄养的孩子,大多因为那时候的情况,最后都没能跟父母再见面。
好在郭金梅住的村子离一二九师师部挺近,邓小平夫妇常能抽空去看看“胖胖”,缓解一下思念之情。不过每次都是匆匆见上一面,来不及多享受一会儿温馨就得赶紧走。
郭金梅后来讲起往事说:“他们老来,但每次都是匆匆看一下就走,连水都没空喝一口。有时候多待会儿,也就说说老百姓日常需要啥。”

郭金梅完全担起了小平同志夫妇交给她的重任,对小“奶云”照顾得无微不至,就连她14岁的女儿秀叶也主动放弃学业来搭把手。夫妻俩心里头既感激又舍不得,但转眼间,离别的时刻就到了。
1945年那会儿,小“奶云”还只是个牙牙学语的小家伙。小平同志接到党中央的任务,得赶紧去河北那边。于是,他和夫人跟郭金梅母女俩说了声再见,就带上小“奶云”,离开了他们奋斗了好多年的抗日根据地。
现在小“奶云”眼看就要满两周岁了,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小平同志两口子这才恍然大悟,小家伙的大名还没给取呢!
尽管夫妻俩都是满腹经纶,但在给宝贝起名字这事儿上,他俩却卡壳了。夜幕降临,小平同志瞅着夜色里模模糊糊的太行山,脑子突然灵光一闪:孩子是在太行山脚下诞生的,干脆直接叫邓太行算了。
“邓太行,邓太行。”邓小平同志心里反复琢磨,感觉这名字真不错,可就在这时,有个人突然站出来说不行。

不成,我儿子名字已经定了叫太行,你儿子可不能也叫太行,赶紧另起个名儿吧。
那时候,在一二九师里头,能跟邓小平同志这样直接对话的,就那么一位,他就是那时候的一二九师师长,同时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司令员刘伯承。就连以勇猛著称的李云龙,见了刘伯承司令员也是不敢随便大声嚷嚷的。
没错,你儿子跟我儿子撞名了,要不刘伯承司令员来给想个新名字吧。卓林同志半开玩笑地把起名的难题丢给了司令员。
小平同志一听,怕刘伯承司令员不答应,连忙又说:“对呀,大家都知道刘邓是一家,不如您来给孩子起个名儿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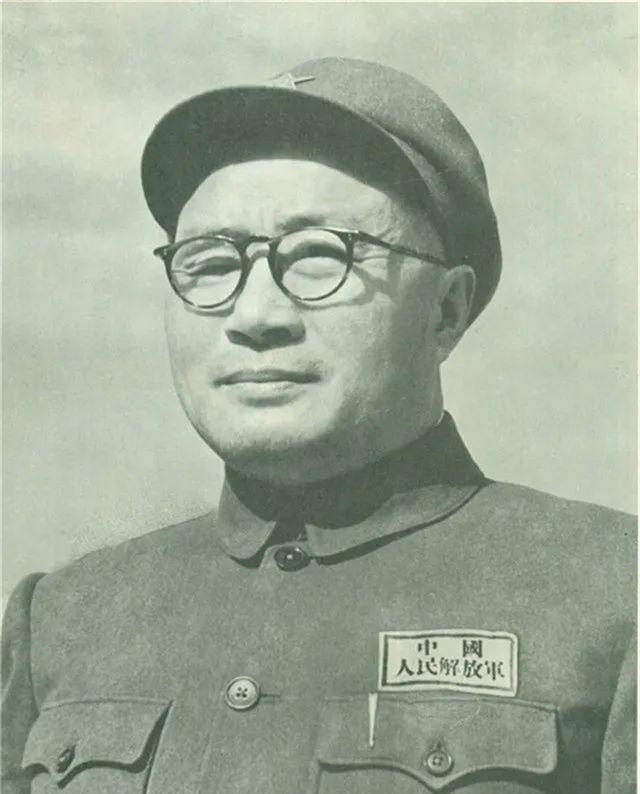
刘伯承司令见夫妻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就没再客气,稍微想了想,然后就回“那你们觉得‘朴实方正’这四个字咋样?”他声音洪亮地说出了这四个字。
“简单正直?”小平同志和他夫人反复念了几句。“行,这名字不错,就要他简简单单、堂堂正正,就叫邓朴方吧。”
【用生命做最后抗争,血染未名湖畔】
解放后,邓朴方来到了北京,开始上小学。那时候,北京城里有钱人遍地,当官的也是数不胜数。小孩子嘛,啥都不懂,就开始互相攀比,看谁家的老爹官职更高,还觉得挺骄傲自豪的。
有小孩会好奇地问邓朴方:“你老爸是当啥大领导的啊?”这时,邓朴方常常会默默低下头,不回答,因为他心里头其实也不清楚爸爸具体是干啥的官。
他老爸从来不跟那些开小车接送娃的官老爷一样,一点不像个大官。他回家问老妈老爸是干啥的,老妈也从没提过他老爸的职位是啥。

邓朴方一直牢记爸妈的教诲,觉得不管当多大的官,都得给老百姓办事。因此,他从来没主动跟别人说过自家的背景。
等他上了中学,在写入团申请时,才不得不说出自己老爸是谁。但就算这样,邓朴方也没觉得自己应该被另眼相看。他老爸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也想跟老爸一样,做个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人。
1962年那会儿,邓朴方进了北京大学,学的是物理系里的核物理专业。他选这行可不是因为自己喜欢,主要是那时候咱们国家正全力以赴地搞核研究呢。邓朴方心里就想着,得给咱祖国、给咱老百姓出点力,就这么简单。

就在邓朴方觉得未来充满希望之际,他突然被卷进了一个复杂的状况里。他爸妈被调到了江西去上班,走得急,连跟邓朴方说一声都没顾上。
邓朴方那时不知道爸妈在哪,被锁在了北大四楼的物理实验室里头,自己反省呢。那实验室里可有不少对身体有害的放射性东西,人要是长时间待在那被辐射照着,后果可严重了,想想都吓人。
邓朴方完全不清楚自己究竟被关了多少时间,不管那些人怎么恐吓诱惑,他就是坚决不承认那些无端的指责,说自己和父母被抹黑的事情。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邓朴方实在是受够了,最后写了一封告别信,打开四楼窗户,一下子就跳了下去。
那天,在北大,未名湖边发生了件大事,就像老舍先生那时一样,又有热血在这儿洒下。不过还好,邓朴方福大命大,掉下来时被三楼的一根铁丝钩住了,他在半空中转了个圈,这样一缓冲,才安全落了地。
但糟糕的是,邓朴方的第一节脊椎和倒数第二节胸椎完全断裂了。有人看见后,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可医生一听他的情况,居然狠心不管,任由他自生自灭。

没办法,大家只能把邓朴方送到别的医院去,可那些医院都不敢给他做手术。这事儿后来传到了周总理的耳朵里,他一听就急了,心里特别难受,马上下令医院得赶紧给邓朴方安排手术。
然而,在接连不断的医院转移里,邓朴遗憾地错过了能够得到最好治疗的关键时刻,结果导致他下半身永久瘫痪,往后余生都只能依靠轮椅生活。
之后,邓朴方常常回想起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他总是会难过地说道:“我感觉那时候,如果有人经历了那样的事,就是心死了也不会觉得有多难受。”
长时间瘫痪已是极大的折磨,但邓朴方还得遭受极为残忍的对待。

1969年,有个四人小组故意捣乱,停了邓朴方的治疗,直接把他送到了北京城外的一个福利院,还不让任何人去管他,意思就是让他自己想办法活下去。
那段时间对邓朴方来说,简直难熬到极点,但他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让他没被击垮。平日里,他就动手做点简单的手工活,比如拿铁丝编些纸篓,之后带到镇上去卖,靠这个维持日常生活。
【父子团聚,重建人生。】
毛主席知道邓朴方的事儿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立马吩咐人把邓朴方送到小平同志那儿。父子俩这才见上面,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啥也没说,但心里头那个难受劲儿,就跟流泪似的。

邓朴方之后讲起往事时说:“老爷子话不多,但他给我帮忙时,每件事都处理得特别到位,一丝不苟。有时候,想想这些,我心里头就挺不是滋味的。”
邓朴方生活完全没法自己照顾,卓林同志身体状况也挺差。这样一来,给邓朴方擦洗身体的事儿,就只能靠小平同志自己动手了。小平同志先是用凉水给儿子擦一遍身子,然后再打上肥皂擦一遍,最后再仔仔细细擦洗干净。卓琳呢,就在旁边帮忙递水、送毛巾。
尽管环境挺不容易,夫妻俩还是对邓朴方关怀备至,照顾得特别周到。

1976年,小平同志又被请回中央挑大梁。可那时候,邓朴方因为下半身瘫痪,没法再搞物理研究了。但即便如此,他心里那股为人民服务的热乎劲儿,一点没变。
谁最需要伸出援手呢?邓朴方瞅瞅自己坐的轮椅,琢磨着这些年走过的路,心里很快就有了底,那就是尽自己所能去帮扶残疾人,为咱中国的残疾人事业拼上一辈子。
邓朴方受到名医陈晋云教授的点拨,心里头下定了决心,要建立咱们国家头一个残疾人康复的地方。说干就干,他找来了王树声大将的公子王鲁光,俩人一合计,只用了短短五年,就把一座挺洋气的康复中心给建起来了。

后来,他找到崔乃夫寻求帮助,打算把这项工程推广到全国。到了1984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了,没多久它就和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合并在了一起,变成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邓朴方当上了这个联合会的主席,而且一干就是四届。
邓朴方出了不少力,让残疾人的康复、教育、就业和文化宣传计划都搞了起来,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和工作体系也都搭建完善了。
有人讲,邓朴方如今的成就全靠他老爸。对此,邓朴方直白地回应:“不承认这个,谁能信?但重点是,咱们都做了啥?是不是真的帮到了残疾人?”

他行事坦荡,跟他老爸一个样。因为自己吃过淋雨的苦头,所以他总想给别人撑把伞。要不是邓朴方自己经历过那些,他可能也不会给众多残疾人带来这么大的帮助。
但话说回来,要是邓朴方身体没毛病,新中国说不定就能多个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呢,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