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是一个女孩的时候,我说我不想做女人。为什么要这么痛苦?这么不开心?但现在我长大成人 了,我为自己感到自豪,为了大家,让我们致力于改变这命运,作为女人的命运。”
说出这句话的是世界名模华莉丝·迪里。
在非洲,女孩在3到10岁时会进行割礼仪式。她们从不去医院,而是由民间巫医或亲友操持手术,没有麻醉没有消毒,只用简单的刀片和树枝就摧残了全球1亿3,000万名女性的身体,而这一历史竟然持续了3000年。
华莉丝·迪里在3岁那年也遭受的割礼习俗的迫害。她记得在割礼前的那天晚上,她分到比平时多的米饭。但第二天就被母亲带着去一个荒凉的地方完成割礼仪式。
割礼期间,她的呼喊声震天动地,但没有人会因此可怜她。
12岁那年,家里人为了5头骆驼的礼金,强迫她嫁给60岁老头,成为老头的第四任妻子。
她不断对妈妈说:“妈妈,我不要嫁给那个老头,你帮帮我!”

她的哀求声打动了母亲。她在母亲的掩护下连夜离开了家乡。她赤脚奔跑在沙漠中,没有水也没有食物,即便双脚已经被磨破了,但她依旧不敢停下前进的脚步。因为一旦被抓回去,就是死路一条。
华莉丝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英国,在亲戚家做女佣。原以为能过上安稳的生活,随着战争的来临,她成了流浪的难民。
在超市,华莉丝被误认为小偷。营业员玛丽莲大喊着要报警,华莉丝听到后落荒而逃。随后她们又在卫生间碰见,玛丽莲再次警告她不要跟着自己。但华莉丝觉得眼前的“陌生人”特别亲切。
后来,在营业员玛丽莲的帮助下开始了新生活,又在工作中遇见了著名摄影师唐纳森。
但没过多久,巨大的文化差异,让她对玛丽莲产生了厌恶的心理。某一天华莉丝下班回家,撞见玛丽莲和男友在挑战底线,她立刻退出了房间。等男人离开后,她开始质问玛丽莲:“好的女人不会干这事的。”
玛丽莲则认为自己也需要享受,指责华莉丝过于保守。
华莉丝接下来的话让她大吃一惊:“只有受过割礼的女人才是好女人。”
玛丽莲不明白华莉丝说的“割礼”是什么意思。
华莉丝说这是女孩保持处女的方法,到洞房那晚,妈妈才能替女孩打开。她以为任何一个女性都这样的。

玛丽莲听完华莉丝的话,依旧一脸懵逼,再次问她什么是割礼。
这时,华莉丝撩起自己的裙子,给玛丽莲看自己接受过割礼的地方。
玛丽莲这才明白华莉丝为什么每次上厕所都要超过半个小时,才知道她曾经遭受过的痛苦。
玛丽莲心疼眼前这个单纯的女孩,于是,也像她展示了自己的身体,用事实告诉她这才是一个健康女人本来的样子。
华莉丝哭了,这时她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其他女人不用进行割礼。
后来在玛丽莲的帮助下,华莉丝慢慢找回自信。在著名摄影师唐纳森的镜头里,她是名震四海的世界名模。
但是童年经历,一直是她挥之不去的阴影。她想念她的家乡和亲人,同时又对那里的生活又爱又恨。
终于在一次专访中,华莉丝说出了压抑在心中已久的伤痛,“我不想再谈这种牧羊女,变成世界顶级女模的故事。”
人们说,她遇到唐纳森的那天,就是改变命运的一天。可是对华莉丝来说,3岁那年进行割礼仪式的那天才是改变命运的一天。
1998年,华莉丝·迪里是第一位公开讨论和反对割礼习俗的女士。她为此遭受了暴力威胁,甚至在她的家乡非洲,她被视为背叛民族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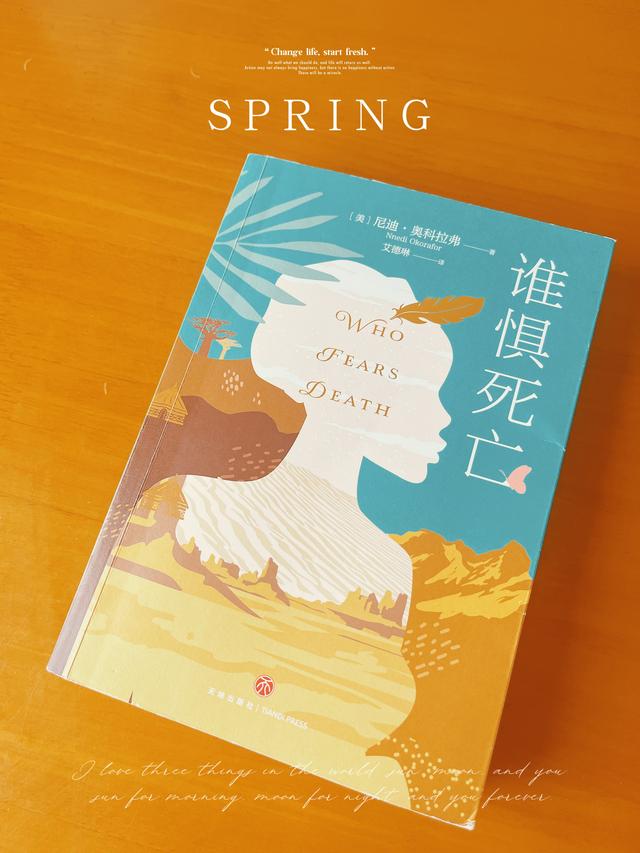
看完华莉丝·迪里的故事,我不禁想起最近读过的一本书《谁惧死亡》。
《谁惧死亡》的作者是尼迪·奥科拉佛。他是一位非裔美籍科幻作家,也是全球著名科幻大咖。更是一位高学历者,他拥有文学博士学位以及新闻、文学双硕士学位。
她在书中探讨了不同肤色种族存在的歧视、性别权力、女性割礼、暴力和权力是否具备正当性、政治和道德责任等内容。
就像《出版人周刊》中所说的,在这个毛骨悚然的写实故事中,奥科拉弗审视了一系列邪恶的事实——其中性别与种族不平等是首要因素。伴随着女性生殖器官的残缺与面对破坏性传统时的自卖把这些不同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共同融入天马行空,异彩纷呈的绝妙叙事中。
女主欧尼桑乌,意为“何惧死亡”。奥科拉佛将其定义为书名,一语双关,既寓意着女主的顽强和勇敢,为了自己的信念,一往无前,也暗示人类为了平等和谐,为了追求真理和幸福,不惧死亡,付出一切。
阅读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一个人的命运不是注定的,我们不应该带着标签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