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平六年(189年),董卓率军入洛阳,随后局势急转直下,东汉末年的乱局从黄巾起义的“初级形态”转变为军阀混战的“终极模式”。
历史有时惊人地相似,北魏王朝的崩溃也是从一场起义(六镇起义)开始的,也有一个人带兵进入洛阳掀起血雨腥风,让旧秩序加速崩解,这个人的名字叫尔朱荣。
由于尔朱荣的历史使命与董卓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武人带兵夺权;都是落后地区军阀带兵进入京师;都对“文明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戮,所以后世之人经常拿这二人进行对比,或称尔朱荣为北魏版董卓。
但事实上,尔朱荣与董卓之间的差异同样不小,一方面,二者军事水平不在同一水平线上,董卓军事水平在同时期只能算中上,而尔朱荣的军事水平在同一时期几乎无人能出其右。
另外,董卓与尔朱荣的家族能量亦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董卓家族世居凉州,其父董君雅有过短暂的颍川任职经历,但显然董君雅并未挤进核心权力圈,要不然出生于繁华之地颍川的董卓和其弟弟董旻也不会被“赶回”凉州这种边疆地带度过童年了。
董卓的夺权更像是“穷小子”靠着自己能力一路逆袭获得权势,并在一次意外中发现有一个天大的机会摆在自己面前,于是决定放手赌上一把。

而尔朱荣的崛起却并非如此,其崛起过程是一个极为有耐心的家族五代权势积累的结果,要想弄清楚这位横空出世的北魏杀神的全部行为逻辑,就得从尔朱荣的家族说起,捋清了尔朱荣家族一以贯之的行为逻辑后,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位北魏版“董卓”看似不合常理的行为,其实无比合理。
取舍尔朱荣的故事,要从其高祖尔朱羽健说起。
尔朱氏家族世居尔朱川,由此而得姓氏。
尔朱荣的高祖尔朱羽健,是北秀容地区的契胡族首领,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王朝时率麾下1700余名契胡骑兵追随,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算作开国元老。
提到北魏开国,就不得不说一说道武帝拓跋珪推行的一项重要国策:离散诸部,分土定居。
宏观上讲,“离散诸部,分土定居”政策的核心是将原本游牧部落的组织形式打散,变为中原农耕地区的编户齐民模式。
但在具体执行时,在各个部落间的执行情况是有明显差异的。
道武帝拓跋珪“创业”之初,集团内部最重要的两个部落是贺兰部和独孤部,而在北魏政权建立之初,最常反叛的两个部落也是贺兰部和独孤部。
对于贺兰和独孤这两个大部落,道武帝拓跋珪有巨大的动力去对他们进行“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因为这两个部落人数众多,如果把他们原本组织形式打散,变成直接由拓跋珪控制的编户齐民,则这两个部落的众多部众可以成为北魏帝国统治的基石,而如果让他们保留原本的组织形式,则这两个大部落就是随时可能一刀将道武帝拓跋珪捅死的巨大隐患。

基于以上原因,道武帝拓跋珪花了大力气来离散贺兰、独孤两个大部落,但对于一些不足以威胁其统治,又比较听话的小部落,拓跋珪将其部落打散的动力并不是那么强。
显然,尔朱羽健率领的契胡部落并不是道武帝拓跋珪重点离散对象。
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朝廷曾经想把尔朱羽健的驻地从相对贫瘠的北秀容地区迁到相对富庶的南秀荣地区。
“人往高处走”是人之常情,但比较神奇的是,面对这个看似很诱人的建议,尔朱羽健竟然拒绝了。
对于拒绝前往富庶的南秀荣这件事,尔朱羽健给出的理由是:我们家族世代在北秀容侍奉国家,怎么能因为南秀荣更富庶就轻易迁走呢?
从尔朱羽健给出的“世代奉国”的说法我们可以推测,尔朱家族率领的契胡部落可能在更早的代王拓跋什翼健时代就追随拓跋家族了,但关于他给出的理由,看看就好,什么为了方便“侍奉国家”都是骗三岁小孩的鬼话,尔朱羽健放弃前往富庶的南秀荣而选择继续留在贫瘠的北秀容的真实原因是:他不想被离散部众。
如果驻地发生改变,太武帝拓跋焘很容易顺势要求其打散原来的部落形式,改为编户齐民模式。
区别一块土地是贫瘠还是富庶的标准是其适不适合农耕,越富庶的地方越适合农耕,而适合农耕的地区容易搞编户齐民;越贫瘠的地方越不适合农耕,不适合农耕的地方只能搞部落联盟,所以如果尔朱羽健不离开贫瘠的北秀容,太武帝拓跋焘很难在当地离散其部众。

对这件事的处理上,尔朱氏先祖尔朱羽健的性格便表现地非常清晰了:他宁愿放弃南秀荣的财富和舒适的生活,也要保证自己对手中武装的绝对控制力,这是一匹沉稳而坚韧的草原狼王,别人赐予的财宝、美女和舒服的生活都打动不了他,他最看重的永远是自己的爪牙,这样的人,这样的家族,不动则已,一动必定惊天动地。
洛阳的老朋友由于尔朱荣的高祖尔朱羽健在关键问题上没有把兵权交出去,其曾祖尔朱郁德、祖父尔朱代勤都继续在北秀容当契胡部落的领民酋长。
其祖父尔朱代勤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皇后贺氏之舅,因为有这样一层姻亲关系,再加上尔朱代勤追随太武帝拓跋焘征战屡立战功,其所在的尔朱氏家族获得了免税的特权,只需在国家有战事时向朝廷提供战马和牛羊。
免税的特权让尔朱家族实现了更高效地财富积累,到尔朱荣父亲尔朱新兴时,尔朱家族牛羊成群,不可胜数,谷物堆积如山。
尔朱新兴时期,北魏王朝出了一件大事:孝文帝迁都。
孝文帝拓跋宏将北魏帝国的国都从北方的平城迁往洛阳这件事对于大多数北魏建国之初的军事贵族来说都是一种灾难,因为国都的迁移意味着资源投入的减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方六镇,六镇在建立之初由于靠近国都军事意义重大,能不断获得资源倾斜,胡、汉贵族子弟都愿意前往六镇为将以换取进入晋升的快速通道,而等到都城迁到洛阳后,六镇获得的资源投入便逐渐减少,六镇最终沦为谁都不愿意去的“发配之地”。
但世间万物都有两面性,随着都城迁往洛阳,北魏朝廷对北方的投入确实是少了,但与此同时,其对北方的控制力也减弱了。
北方六镇之所以对迁都这件事感到无比痛苦,是因为他们是依赖国家资源投入过活的,而如果一个势力有稳定的财富来源,以及独立的人事和军事权力,那么伴随都城迁走而来的控制力减少,他们则会有更多的空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迁都洛阳后,尔朱家族靠着免税的特权,在朝廷控制力减弱的背景下,日子不但过得不苦,反而越来越滋润。
而也是在这个时间段,一道类似先祖尔朱羽生当年面对的选择题出现在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面前。
当时的胡人贵族中,有一部分跟随孝文帝一同前往洛阳生活,在度过短暂的不适应后,他们马上被洛阳纸醉金迷的生活所吸引,一头扎进温柔乡,多年艰苦的草原游牧生活所磨炼的坚韧性格被迅速消磨殆尽。
在当时那个“汉化”是主流,融入“文明”是大趋势的时代叙事下,尔朱新兴也面临着是否要前往洛阳生活的抉择。
面对洛阳的花花世界,尔朱新兴这位领民酋长表现出了近乎恐怖的理性。
尔朱新兴经常带着自己的儿子尔朱荣来洛阳给权贵子弟送马,但并不一直在洛阳定居,而是“东居洛阳,夏归部落”。
他们父子两个在见识了洛阳的繁华后并未迷失自我,他们来洛阳送马的目的十分清晰,就是要结交权贵,以此谋取更多家族利益,尔朱氏父子从一开始就明白,他们的根基在秀荣,至于那繁华的洛阳,只是他们谋取权势的工具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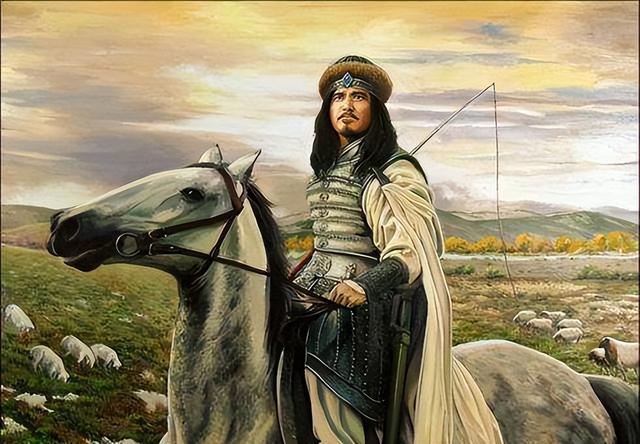
尔朱荣并非一个从天而降的“野蛮人”,相反,他在自己的青年时代有着不短的混迹于洛阳的经历,这有点反常识,就如同董卓这个被后世描述为“头上长角,脚下流脓”的野蛮人其实出生在帝国文化中心的颍川一样。
尔朱荣的早年经历已经清晰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他日后屠戮洛阳权贵的举动并非一个莽夫的临时起意,而是一个十分熟悉洛阳的人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
好,现在该回答那个核心的问题了:既然尔朱荣对于洛阳十分熟悉,他为什么不选择与洛阳贵族合作?而是要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与洛阳的权贵决裂呢?
起义?兵变?让我们先来看看当时发生了什么吧:
六镇起义后,整个帝国的北方乱成一团,腐朽的北魏朝廷反应迟钝,派出镇压的军队战斗力感人,各州县各自为战,无法实现相互救援,六镇及周边局势岌岌可危。
在这里要先把一个问题说清楚:对于六镇起义的性质,史学界历来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六镇起义”的说法并不准确,应该叫六镇兵变,或六镇动乱更准确。
认为发生于北魏末年的六镇暴动不能称之为“起义”者给出的原因是:六镇武装的战斗力太强了,不像一直农民起义军。
但持这种观点者有混淆了“起义”与“农民起义”之嫌,似乎只有扛着锄头的农民武装暴动才能被称为起义。
定义一场武装暴动是否能被称为“起义”的根本原则是看暴动的参与者大多来自于哪个社会阶级。
拉开六镇起义序幕的破六韩拔陵身份是沃野镇普通镇民,他反抗的最直接对象是其顶头上司领民酋长。
随后的起事者大多也是这个身份,六镇起义的最直接矛盾是:六镇上层的镇将联合中层的豪帅、酋长对底层的镇民压迫太过。

之所以要费如此笔墨去讨论六镇起义的性质,是为了让大家能更清晰地了解这场发生于北魏帝国北方军镇的起义到底给尔朱荣带来了什么。
六镇的底层镇民们发动起义后,作为原本六镇权力系统中层的汉人豪帅和胡人领民酋长大多是站在北魏统治者一方的,他们才是第一股镇压起义的力量。
但豪帅和领民酋长在人数上是劣势,在朝廷救援不利的背景下,在与人数众多的起义镇民的对抗中,他们逐渐落入下风,于是出现了大量豪帅、酋长逃亡的现象。
在北境遍地狼烟的背景下,尔朱荣以铁血手段稳住了他统治的秀荣地区,于是秀荣就成为这乱世的避风港,大量逃亡的六镇豪帅、酋长投奔尔朱荣。
这些逃亡的六镇豪帅、酋长才是原本六镇的中流砥柱,他们有经验、有能力,他们的大量到来为尔朱荣提供了一个天然中下层军官团,有了这些人助力,尔朱荣只要大规模招兵队伍规模就会迅速扩大。
《魏书》称天下大乱后,尔朱荣卖掉牛羊,招募人马,扩充军队。
即便不招兵,尔朱荣手上也是有兵的,尔朱家祖孙五代人尝试各种努力,就是为了保证对自己率领的契胡骑兵的绝对控制权。
在六镇起义爆发前,这支契胡骑兵便被尔朱荣训练成了一支天下劲旅,史载尔朱荣练兵纪律严明,打猎时都行军打仗般排兵布阵,虎豹从谁的方向逃出重围,失职者斩首。

这支契胡骑兵作为尔朱荣的基本盘,战斗力没的说,问题是数量太少,其高祖尔朱羽健追随道武帝拓跋焘时兵力规模是1700骑兵,随着尔朱家族对秀荣地区的经营,到尔朱荣时期,这支契胡骑兵队伍应该有所扩大,但应该也不会超过万人,因为秀荣就那么大,是养活不了太多骑兵的。
尔朱荣此番变卖牛羊扩充军队,是因为此时的他手上已经拥有了六镇豪帅组成的中下级军官团,但即便加上新招募的军队,尔朱荣手上的军队就规模而言应该也不会太大,这一点从尔朱荣后面操作就能得到证明。
河阴之变尔朱荣起事时,庙堂与江湖各发生了一件大事:
庙堂之上,把持朝政的灵太后在发现儿子孝明帝元诩欲拿回权力后,竟竟孝明帝毒死,毒死孝明帝后,灵太后搞了一系列神操作,包括把一个女婴谎称孝明帝之子推上皇位,为了把持朝政,灵太后已经无所不用其极。

江湖之远,六镇起义在多方联合绞杀下被镇压了下来,北魏朝廷讨论后将六镇降兵安置到河北就食,但这帮六镇降兵到河北再次起事,最终形成了拥众10余万的葛荣起义军集团,河北州县大多落入葛荣之手。
面对如此局势,兵强马壮的尔朱荣听从高欢等人建议,决定“入关”,去争一争这天下。
尔朱荣以为孝明帝报仇为由向洛阳进发,灵太后为首的洛阳势力开始还试图阻止,但他们手上那点战斗力感人的军队怎么去跟尔朱荣手上那支虎狼之师较量,尔朱荣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地进入洛阳,于是,洛阳历史上现象级名场面河阴之变即将上演。
控制洛阳后,尔朱荣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并命文武百官前往黄河边参与新皇帝主持的祭天仪式,灵太后与文武百官来到黄河边时,尔朱荣突然命事先埋伏好的刀斧手大开杀戒,2000余名高官尽数命丧于此,灵太后本人则被尔朱荣推下黄河淹死。
尔朱荣刚刚来到洛阳就大开杀戒,这是后世史官称之为野蛮人的主要原因,但通过上文对于尔朱荣家族的介绍,我们已经能很清晰地看到野蛮这个词不足以形容尔朱荣,他以河阴之变这种极端的方式给了洛阳权贵一个“惊喜”是因为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来看看尔朱荣大肆屠戮洛阳贵族后做了什么吧:
发动河阴之变后,尔朱荣给了在黄河边被杀死的2000余名各级官员的家属赏赐作为安抚,安抚完洛阳权贵后,尔朱荣立刻北上晋阳,准备去镇压河北的葛荣起义军。
葛荣起义军拥众10余万,号称百万,面对如此规模的起义军,尔朱荣率领多少军队迎战呢?七千人。
尔朱荣对葛荣起义军的讨伐堪称古代战争史中以少胜多的典范。
葛荣听说尔朱荣兵少喜出望外,命部队摆出分散阵型以防止尔朱荣逃跑,尔朱荣则命精锐骑兵兵分三路,两路为疑兵吸引葛荣军注意力,让葛荣军本已分散的军阵更为松散,而后由侯景率精锐骑兵突然杀出,直接打崩葛荣军军阵,葛荣被侯景生擒。

擒获葛荣后,尔朱荣收编了大量六镇军,随后将葛荣押回洛阳,当着皇帝和文武百官的面斩首。
尔朱荣以七千精锐骑兵击溃葛荣10余万众的战例固然漂亮,但也体现了尔朱荣面临的困境:兵少。
发动河阴之变时,尔朱荣的军队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世代追随尔朱家族的秀荣契胡骑兵,其二是六镇起义中投奔尔朱荣的六镇豪帅以及尔朱荣决定起事后招募的新兵。
六镇豪帅加新兵的组合战斗力尚未经过战场检验,尔朱荣绝对信得过还是一直追随他的契胡骑兵。
契胡骑兵虽然精锐,但数量太少,而这就是进入洛阳的尔朱荣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尔朱荣入洛阳时,河北的葛荣起义军已经成气候,必须迅速解决,尔朱荣必须以少量兵力,同时完成两个任务:
第一是干掉葛荣的起义军,第二是保证洛阳旧贵族不在其与葛荣起义军作战的时候捣乱。
此时的尔朱荣兵力有限,无法分兵一边镇住洛阳旧贵族,一边出兵对抗实力不俗的葛荣起义军,所以只能以一些非常手段让洛阳旧贵族印象深刻,不敢在尔朱荣出兵对付葛荣起义军时捣乱。
有人可能会问,尔朱荣难道就不怕适得其反,洛阳旧贵族因为尔朱荣大开杀戒而更加不跟他合作吗?
其实这件事能够看出尔朱荣对洛阳旧贵族的基本态度是蔑视:曾经混迹于洛阳的尔朱荣非常瞧不起那些被洛阳的花花世界阉割了血性的权贵们,在他的认知里,这帮权贵只敢在背后搞搞小动作,根本就没有放手一搏的勇气,只要给他们上点强度,他们立刻就会跪地求饶。
事实证明,尔朱荣对洛阳权贵的认识基本正确,但有时候过于自信也不是一件好事,尔朱荣算漏了他扶持的傀儡皇帝元子攸,这是洛阳权贵中少数敢于鱼死网破的主,而这最终要了他的命。
如果将视线拉长,尔朱荣是孝文帝南迁后,被冷落的军事贵族的总代言人,他们以一种决绝的方式对前往洛阳的权贵来了一波反攻倒算,随着尔朱荣平定天下叛乱,新的国家治理模式雏形已经显现:国家政治中心重新回到北方的晋阳,北方军事贵族重新成为国家的第一等贵族。
但历史又岂会简单重复?尔朱荣的计划随着他的意外被杀而草草收场,天下再次大乱,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总矛盾:胡汉矛盾也将在尔朱荣死后找到更加完美的解决方案,所有终结乱世的命运碎片都已聚齐,只等天命之子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