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可在当今这个时代,不是生病的人太难伺候,而是伺候的人心思太复杂。这不,就让我说说我们沙河镇发生的一件事。
我叫老刘,今年67岁,在沙河镇住了大半辈子。镇上人都叫我老刘头,以前在供销社干了三十多年会计,小日子过得还算滋润。前年老伴走了,留下我和三个儿子。
说起我这三个儿子,在镇上也算有头有脸。大儿子老大开了家超市,一年能挣个十来万;二儿子在镇上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红火得很;最小的在市里做些小生意,天南海北地跑。
老伴在世的时候,一直操心着儿子们的婚事。三个儿媳妇,说实在的,也都是她一手把关相中的。大儿媳妇麦秀,是隔壁清水村的,家里开农机店;二儿媳妇英子是镇上卖布的,嘴甜会来事;小儿媳妇小芳,城里人,大专毕业,在银行上班。
记得老伴生病那会儿,前前后后拖了三年。刚开始还能下地,后来连床都下不了。三个儿子轮流照顾,一个月一倒班。麦秀总说超市忙,来得少;英子倒是来得勤快,就是总叨叨着农家乐的事;小芳因为在城里,一个月也就来那么一两趟。
老伴临走那天,非要跟我单独说话。她拉着我的手,声音虚弱地说:"老刘啊,你要记住,我走了以后,千万别去儿子家住。"我当时还纳闷,问她为啥,她就摇摇头,说:"你记住就行。"

说来也怪,老伴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从来不讲没来由的话。她在世时对这三个儿媳妇那叫一个好,买衣服要买六件一样的,就怕她们心里不平衡;做月子的时候,一天要去三趟,给她们炖汤熬粥;带孙子的时候,更是一碗水端得平平的。
可临走前这句话,着实让我琢磨了好些日子。
老伴走后,三个儿子都劝我去他们家住。大儿子说:"爸,你一个人在家多不方便,搬我家来住吧,超市什么都现成。"二儿子说:"爸,我这农家乐天天热闹,你住我这儿解闷。"小儿子倒是实在:"爸,你要是愿意,就搬城里来,我给你买个跑步机,天天锻炼身体。"
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没准主意。老伴的话一直萦绕在心头,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就这样,我在自己家里住了下来。
这一住,可真把儿媳妇们给"愁"坏了。

麦秀隔三差五就来说:"爸,你看你一个人在家,万一有个闪失可咋整?"英子更直接:"爸,你这么大岁数了,总不能老是自己照顾自己吧?"小芳到好,一个月打个电话,问问身体就完事。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直到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收拾老伴的遗物时,在墙缝里发现了一张发黄的纸条......
那张纸条上写着:"老刘,这墙后头有个暗格,里面有我给你留的东西。"我认得,这是老伴的字迹。
看到这儿,我手都有点抖。记得老伴在世时,总爱念叨这老房子是她的嫁妆房,说这房子虽然破,但是有些东西是要传家的。我一直以为她是在感怀往事,没想到还真给我留了东西。

我哆嗦着手,用铁丝在墙缝里摸索。果然,在离地两尺高的地方,有一块活动的砖。我小心翼翼地把砖抽出来,里面露出一个黑乎乎的洞。
伸手进去一摸,是个铁盒子。那是老伴陪嫁时带来的首饰盒,平日里一直放在柜子最上层。打开铁盒,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一叠存单,还有一本发黄的笔记本。
翻开第一页,是老伴歪歪扭扭的字迹:"老刘,如果你看到这本子,那说明我已经不在了。别难过,听我慢慢给你说......"
原来,这是老伴这些年偷偷记下的日记。
"今天是大儿媳来照顾,一进门就嫌家里味大。我装睡,听见她在打电话,说伺候我像伺候祖宗似的,还说要是分家,一定要先把好东西分走......"

"二儿媳嘴上甜,背地里不是东西。我住院那会儿,她偷偷拿走了我的金项链,说是怕我丢。后来我问她,她说不知道,怕是我记错了......"
"小儿媳最绝,趁我神志不清的时候,让我按了手印。还好我留了个心眼,那份文件被我藏起来了......"
看着这些字迹,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原来,老伴早就看透了这一切,她是在保护我啊!
再往下翻,我发现了那叠存单。足足一百二十万!这么多年,老伴竟然攒下了这么多钱。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这些钱,是我这些年省吃俭用存下的。我知道儿媳妇们都盯着这笔钱,所以才瞒着所有人。老刘,你要记住,这钱千万不能给儿子们,否则他们会为了钱反目成仇......"
就在这时,院子里传来脚步声。我赶紧把存单和笔记本塞回铁盒,正要藏起来,二儿子推门进来了。

"爸,你在翻什么呢?"二儿子狐疑地问。
"没啥,就是你妈的些老物件。"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
"爸,我跟你说个事。"二儿子搓着手说,"我这农家乐准备扩建,缺点钱,你看......"
我心里一沉,原来是为了钱来的。难怪这段时间,他隔三差五地往我这跑。
"你妈走得早,我这还真没剩多少钱。"我故意叹了口气。

二儿子脸色一变,嘟囔着:"那您老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这天晚上,我彻夜未眠。想起老伴生前的种种叮嘱,再看看这些触目惊心的日记,我终于明白了她的良苦用心。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趟敬老院。院长老张是我以前的老同事,这些年一直在张罗着建新院区。
"老张啊,我这有笔钱,想捐给敬老院。"我把存单递给他,"就当是替我老伴尽最后一点心。"
老张看到存单数额时,惊得说不出话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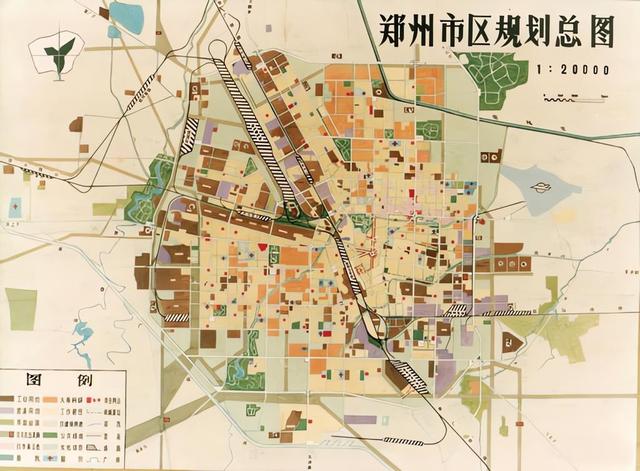
这事很快传遍了镇上。三个儿媳妇像是商量好似的,一个接一个找上门来。
麦秀哭诉说:"爸,您怎么能把钱捐出去呢?那可是我们一家的血汗钱啊!"
英子更是拍着大腿喊:"这不是打我们的脸吗?镇上人会怎么看我们?"
小芳倒是文明些,只是冷冷地说:"爸,您这么做,是不是太偏激了?"
我笑笑,没有说话。晚上,我又翻出了老伴的日记,上面写着:"人心都是肉长的,有时候太明白了,反而不好。老刘,你要学会稀里糊涂地过日子,但千万别糊涂地过完这一生......"

日子还在继续。敬老院的新院区很快就要完工了,听说他们要给老伴立一块纪念碑。儿媳妇们的态度也有了微妙的变化,虽然不似从前那般殷勤,但也不再总是打我的主意。
最让我感动的是,镇上的老姐妹们知道这事后,都夸老伴有先见之明。王婶子还专门来看我,说:"你老伴是个明白人啊,这钱花到刀刃上了。"
有时候我坐在院子里,看着老伴种的月季开花,就觉得她其实从未走远。她只是用另一种方式,继续保护着这个家,保护着我。
老伴常说:"人这一辈子,不在乎活得多久,关键是明白些什么。"现在我终于明白,有些事,看透不说透,是最大的智慧;有些钱,不该留的,一分都不能留。
这不,昨天老张打电话说,敬老院的新院区命名为"福寿园",说是取我老伴的名字里那个"寿"字。听到这个消息,我在院子里坐了很久,看着月季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突然想起老伴临终前的那句话:"老刘啊,你要记住,我走了以后,千万别去儿子家住。"现在我终于完全明白了她的用意,她不是不让我去儿子家住,而是在告诉我:有些路,还是得自己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