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中国的本土现代主义
文 | 吴晓东
如果不把“现代主义”仅仅理解为以“西方性”为主体的文学思潮,可以说在20世纪的文学史进程中,现代主义是一场席卷世界的国际主义文学运动,因此具有一种全球性或者世界性,具体表现在,除了欧洲与北美,亚非拉作家也同样加入到“现代主义”的阵营,并且贡献了与西方迥然有异的现代主义作品。而西方之外的现代主义者们在借镜先发的西方“现代派”的过程中,差不多都会面临一个如何创造本土化的现代主义的历史性议题。

1947年5月,汪曾祺在上海
中国的现代主义在40年代迎来成熟期,标志之一是现代主义的在地化和本土化程度的增强。而在40年代崭露头角的一批新生代作家中,汪曾祺尤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在他的手中,或许一种中国式的或者说本土化的“现代主义”显露出诗学意义上的独特性,进而在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之后,使本土的现代主义实践更趋自觉和“纯熟”。
关于汪曾祺身上所体现出的“纯熟”性的判断来自于现代诗人兼批评家唐湜,也正是唐湜较早在汪曾祺的创作中触及了这种“现代主义”的本土化面向,他写于1948年的《虔诚的纳蕤思——谈汪曾祺的小说》[1](以下简称《虔诚的纳蕤思》)一文,尽管依旧显露出沿用西方影响模式来讨论汪曾祺小说中的现代派技巧的痕迹,但同时也独具慧眼地洞察到了汪曾祺40年代一批具有现代派风格的小说对中国古典诗学资源的内化与融汇,从而开启了本土现代主义的论题。

唐湜著《新意度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虔诚的纳蕤思——谈汪曾祺的小说》一文收录其中
《虔诚的纳蕤思》由此或许可以进入中国现代主义诗学批评史上的经典文献行列。唐湜40年代后期一系列给人横空出世之感的批评文字往往被学界赞誉为有李健吾式印象主义之遗风,但也因此容易忽略他的批评视野中所体现出的奠立现代主义诗学的自觉性和系统性。唐湜在这些文章中表现出沟通古今和中西的努力,主张对东西方诗学传统进行中和,一方面要“继承传统的中国气派与精神,一方面又要设法接受进步的世界新传统”,[2] 并且在微观诗学层面有所建构,其具体维度是熔铸西方的象征论与中国传统的意象论。唐湜借助对后期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思索,把意象理解为对存在本质的揭示,意象在里尔克那里具有一种古典主义的充实与凝定。而这种里尔克式古典主义相对来说更容易与中国传统诗学相契合,如果说这种契合论的中国现代体现者在诗歌领域是以穆旦、杜运燮、郑敏、陈敬容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而在小说领域,汪曾祺“通过纯粹中国的气派与风格来表现”“现代主义的小说理想”,在西方的意象化象征和意识流形式中注入“东方式的参悟与澄澈的思索”,这种融会贯通的境界最契合于唐湜的诗学理想。
《虔诚的纳蕤思》一文的意义由此就表现在通过对汪曾祺小说的阐释,把西方的象征论与意识流融入中国化的现代主义小说诗学的努力。唐湜首先认为“现代欧洲文学,特别是‘意识流’与心理分析派的小说对汪有过很大影响”,据此,唐湜断言:“他主要的是该归入现代主义者群(Modernists)里的,他的小说的理想,随处是象征而没有一点象征‘意味’,正是现代主义的小说理想。”而接下来唐湜作出的另一个判断也许更为重要:“然而这一切是通过纯粹中国的气派与风格来表现的。”称这段论述是唐湜关于中国本土现代主义的历史宣言书,或许毫不夸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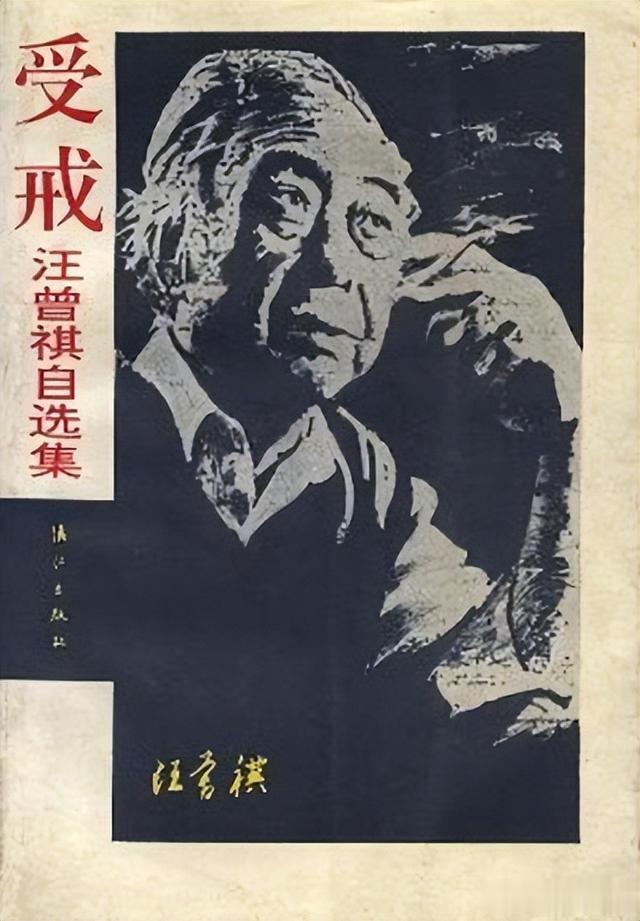
汪曾祺《受戒》,漓江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
可以说,唐湜洞见的是在汪曾祺这里一种真正具有“中国的气派与风格”的本土现代主义得以成形的可能性。其实早在鲁迅创作的中国现代文学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那里,就堪称同时创生了本土现代主义的微观诗学机制,到了30年代,施蛰存通常被归入“新感觉派”实践的一些现代派小说更显露了鲜明的本土化诉求,而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则称得上是第一篇真正具有本土性的现代主义小说,只可惜她的小说创作数量太少。而在唐湜眼里,汪曾祺则“有溶和一切传统而别创新意的心胸”:

奇怪的是我们的新文学却少有中国气派与中国精神,少有人们所喜闻乐见的风格。汪曾祺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正是新文学中的一个奇迹:他的中国风格;正如黄永玉的童话风的木刻杂在纯西洋风的作品中能给人一个流云似的生动亲切的印象,他的作品也在在显示了中国传统的思想风格对他的感染力。不过黄是清新的,有年轻的幻想力与单纯的色调;而汪则是纯熟的,对人事世故有过东方式的参悟与澄澈的思索。

黄永玉木刻作品《风车和我的瞌睡》,1947年
这段论述揭示的是汪曾祺集中国风和成熟度于一身的创作特征,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或许是“奇迹”和“纯熟”两个词语。或许找不到别的字眼儿比“奇迹”和“纯熟”更能表达唐湜的欣喜感,“奇迹”主要体现为汪曾祺创作中的“中国气派与中国精神”以及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风格”,而“纯熟”则是在对人情世故的书写中注入了东方式的颖悟的结果。
或许正是这种东方式的传统因素的植入,使得汪曾祺的创作标志着40年代的现代主义真正实践了本土性,而且在唐湜看来,汪曾祺是“早熟地超越”了学步阶段,“趋向于可喜的成熟”。而借助唐湜的眼光从头再来解读汪曾祺40年代的小说以及散文创作,的确会感受到这是一种唐湜所谓“一个艺术家该有溶和一切传统而别创新意”的“成熟”乃至“纯熟”。这种“纯熟”或许表现在,即使在汪曾祺早期创作中,也很难发现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技巧的刻意模仿痕迹,很难辨别出哪些具体因素是西方的,哪些又是本土的,或许汪曾祺40 年代的小说尚未臻于诗学意义上的化境,但至少他走出的是一条融会贯通的现代主义本土化的道路。


汪曾祺《异禀》脱胎于1941年的《灯下》,原载于《国文月刊》1941年第1卷第10期(图左),后来更名为《异秉》,发表于《文学杂志》1948年第2卷第10期(图右)
就汪曾祺小说中现代主义的具体诗学因素而言,唐湜除了从“圆到融汇的象征”的角度进行总结之外,也侧重强调其中的“意识流”小说思维和技巧。然而,汪曾祺的小说中如果只有对卡夫卡的“随处是象征而没有一点象征‘意味’”的境界以及对伍尔夫的意识流风范的追慕,那么他的中国化的现代主义又从何显现?这就涉及了汪曾祺的微观诗学创造这一层面,而唐湜最核心的聚焦点当在于“意象论”。
“意象论”是唐湜这一时期集中思考的诗学问题,相关论文有《论意象》以及《凝定的意象》[3]等。《虔诚的纳蕤思》也集中思考了汪曾祺的创作在意象性方面的特质,称汪曾祺“也许正以音符般透明的意象作他艺术的最高理想”,“在广阔而众多的意象里自如地遨游”,从中可以见出唐湜从汪曾祺现代主义式小说中总结一种本土化意象诗学的努力。但就笔者的感受,倘若只停留在意象性的层面,似乎还不足以说清汪曾祺本土现代主义之核心和精髓所在。而结合汪曾祺所受西方意识流小说技巧的具体影响,再结合唐湜对汪曾祺小说意象诗学的概括和提升,我们或许可以借用唐湜在评论“中国新诗派”的辛笛时所运用过的一个范畴——“意象流”——来描述汪曾祺式的本土现代主义的小说诗学特征。
唐湜曾经这样评论辛笛创作上的不足:

一句话,诗人没有非常虔心的诚挚与十分矫健的生命力来支持他的思想流,使全蜕化为意象流。[4]

辛笛《手掌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
在唐湜这里,“意象流”是思想流的载体,以意象的流动的方式呈现思想变动不居的存在形态,堪称是一种具有微观诗学意义的范畴。“意象流”概念的创造,与唐湜受到意识流理论的影响进而注重人的意识的流动性有直接的关联性。在《论意象》一文中,唐湜指出:

意象则是潜意识通往意识流的桥梁,潜意识的力量通过了意象的媒介而奔涌前去,意识的理性的光也照耀了潜意识的深沉,给予它以解放的欢欣。[5]。
潜意识由此具有了与意识等同的流动性。而既然潜意识是“通过了意象的媒介而奔涌前去”,那么潜意识的流动就有赖于一个个意象本身的流动性,甚至可以说其表现形态正是一种“意象流”,从而也赋予了“意象流”以诗学理论范畴的可能性意义。
唐湜推出的“意象流”范畴天然就具有某种创造性,堪称是把西方现代主义的意识流诗学与本土意象性文论相结合的产物。可惜“意象流”的概念似乎并未流行开来,仅见有研究者从美学的角度进行阐发,也偶见于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阐释。[6] 本文则尝试挪用来阐释汪曾祺的创作中所呈现出的小说诗学图景。

1948年,汪曾祺与夫人施松卿在北京
汪曾祺曾经在初登文坛不久的1940 年,创作了一篇题为《复仇》的小说,此后又两度改写。在发表于1946 年的版本中,有这样一段奇妙的文字:

白沫上飞旋一只鸟,仅仅一只。太阳落下去。
黄昏的光映在多少人额头上,涂了一半金。
多少人向三角洲尖上逼,又转身,散开去。生命如同:
一车子蛋,一个一个打破,倒出来,击碎了。
击碎又凝合。人看远处如烟,
自在烟里,看帆篷远去。
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
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
一船鸟,一船百合花。
深巷卖杏花。[7]
论者多依据这一段讨论汪曾祺小说中的意识流因素。但也正是这段文字,体现出汪曾祺的小说诗学与以伍尔夫为代表的经典西方意识流的差异。与其说它是意识流,不如说是“意象流”,或者说,作者的意识乃凭借于一个个意象在流动,汪曾祺仿佛推倒了由“意象”组接而成的多米诺骨牌,从而使小说诗学技巧表现出鲜明的意象的延宕性。从“太阳”到“黄昏的光”,从“光映在多少人额头”,再经过“多少人”的疑似顶真格的修辞,引出“多少人”向三角洲逼近、转身、再散开去的动作;进而以“蛋”的打破、击碎又凝合来拟喻“多少人”的“生命”;再由“人”的观看引发“烟”的意象,继而从“自在烟里”所见的“帆篷”,到“船”;从船中的“瓜”和“石头”联想到“鸟”和“百合花”,再联想到一句古诗“深巷卖杏花”,作者的联想轨迹大体上是可以捕捉到的,呈现出从一个意象到下一个意象的延宕性与流动性。汪曾祺状写的也的确是意识的流程,但在前引桥段中,意象的延宕与生成构成的既是小说文本中的诗化语境,也就同时具有了小说诗学的属性。


汪曾祺著《复仇》,刊于《文艺复兴》1946年5月第4期
尽管在《虔诚的纳蕤思》一文中未见唐湜具体分析《复仇》中的这段文字,但他却正是从《复仇》中抽绎出了文本中“爬山”的象征性,进而从意象性的角度概括出了小说所内含的诗学特征:

爬山是人生的象征,蜂蜜、和尚,随处是象征,随处有诗的火花,有佩环叮当响过去,一串键子。
这种佩环的叮当响过去,以及“一串键子”般的音符,不正可以隐喻小说的意象流的诗学特征吗?唐湜称“《复仇》是一串意识流的隐现”,然而就他对小说文本诗学特征的具体分析,或许援用他自己用过的“意象流”范畴,更贴近于唐湜对小说语境的具体感受。
唐湜似乎更看重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的成熟度:

当然,老树的钟又敲起来了。风很大,船晃得厉害,每个教室里有一块黑板,黑板上写许多字,字与字之间产生一种依约可辨的朦胧的意义,钟声作为接引。我不知道在船上还是在水上,我是怎么活下来的。有时我不免稍微有点疯,先是人家说起,后来是我自己想起,钟!……

1961年,汪曾祺与沈从文在北京中山公园
按唐湜的分析,“这些文字正是音符,钟声是接引或拍子,我想作者也许正以音符般透明的意象作他艺术的最高理想吧”。唐湜依然以意象性诗学来分析这段文字,但孤立的意象性似乎不足以道出汪曾祺的独异性。汪曾祺摹写的是“我”的似真似幻的心理流程,幻觉中的“我”不知道是在船上还是在水上,而现实中黑板上的字迹仅仅依稀可辨,因此意义也就显得朦胧。而这一切,都以“钟声作为接引”,钟声激荡出意象的流动的音符,使得文本语境同样表现出“意象流”的特征。因此灌注其间的更关键的诗学因素或许不是意象的透明,而是意象的流动。
前引《复仇》以及《小学校的钟声》中的文字乍看上去难免给人以模仿伍尔夫的意识流技巧的印象,但仔细辨识,会觉得还是以唐湜的“意象流”范畴进行阐释显得更为熨帖。而汪曾祺40年代更成熟的小说,或许是那些不那么“意识流”化的作品,却生成了唐湜所谓的更为“冲和、恬淡”的诗学风格。唐湜认为在汪曾祺的《老鲁》《囚犯》《戴车匠》与《落魄》等小说中,“由于作者的高度的自觉与高度的克制”,“如此的情感的调节,趋向于中和,也正如中国传统的为人态度。如此虚心虚己,意象才能自由运行,无障无碍”。意象的“自由运行”,背后是以中国传统的人生境界为底蕴,这种“中和”美学的精髓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姿态与古典哲学精神,“可见出一种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趣味”。诗学形态由此获得了古典生命境界和传统哲学精神的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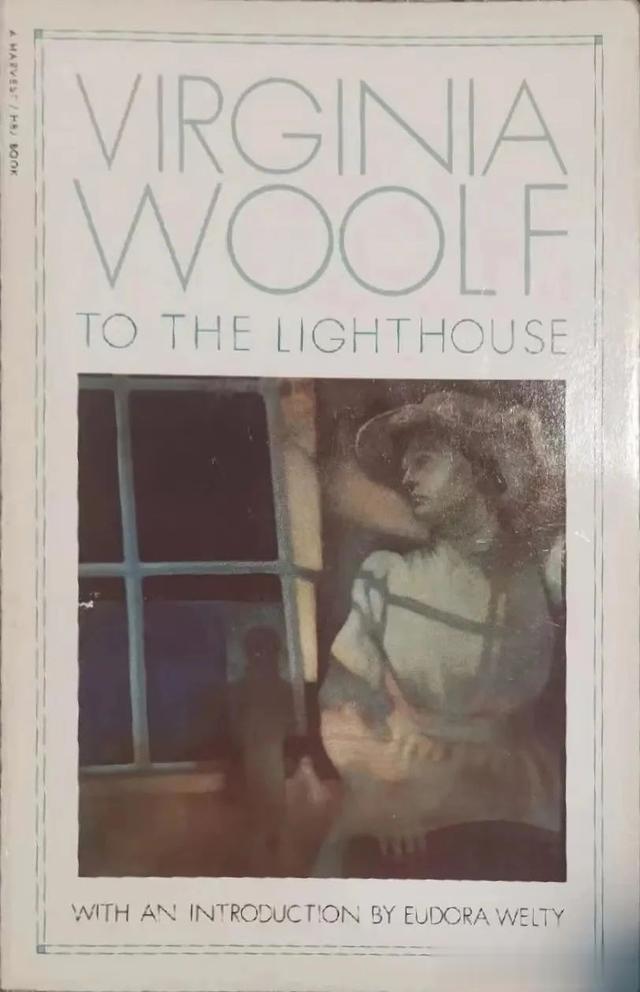
《到灯塔去》弗吉尼亚•伍尔夫,harcourt brace,1927
在这个意义上,唐湜非常看重汪曾祺给他的私人信件中所表露出的关于“形式”的理想:

我要形式,不是文字或故事的形式,是人生,人生本身的形式,或者说与人的心理恰巧相合的形式。(吴尔芙,詹姆士,远一点的如契诃夫,我相信他们努力的是这个。)也许我读了些中国诗,特别是唐诗,特别是绝句,不知觉中学了“得鱼忘荃;得意忘言”方法……司空表圣的“风色入牛羊”我颇喜欢,风色是最飘渺,然而其实是最具体实在的。
“风色”一词被汪曾祺敏锐凸显并加以提升,也具有一些诗学范畴的韵致了。飘渺的难以捕捉的“风色”落地于“具体实在”的意象流中,或许构成的就是汪曾祺本土现代主义的理想形式。

汪曾祺画作
也正是从诸如“风色”的范畴,可以看出汪曾祺把西方意识流的影响加以中国化的努力。[8]汪曾祺所追慕的伍尔夫等西方作家对于“形式”的现代主义式的理解被汪曾祺转换为“风色”,可以说是与中国传统诗学互渗的结果。那么该如何理解汪曾祺所谓“风色是最飘渺,然而其实是最具体实在的”这句表述?不妨再看看唐湜在《虔诚的纳蕤思》中对汪曾祺的《蝴蝶》的引述:

那篇《蝴蝶》里有他对生活的沉缅的抒写,他仿佛庄生梦着蝴蝶:“蝴蝶,蝴蝶在同蒿花田上飞,同蒿花灿烂的金色。同蒿花的金色,风吹同蒿花,风搂抱花,温柔的摸着花,狂泼的穿透到花里面,脸贴着它的脸,在花的发里埋进它的头,沉醉的阖起它的太不疲倦的眼睛。……”
唐湜进而从“肉感”的角度评价汪曾祺对蝴蝶与同蒿花的铺排,但笔者更想结合“风色论”谈谈这段文字中“风”的意象。可以说,文本语境中的“风”在汪曾祺的“意象流”中染上了真切的“色”,“风”是在一系列关于同蒿花的排比句中得以具象化的,从而使“最飘渺”的风色随着风吹花朵而变为最具体实在的“意象流”。
从汪曾祺对“风色”的执著中或可见出,他对西方意识流的借鉴或许不在于试图抵达潜意识的深处,探究人的心灵的黑暗域的秘密,而在于捕捉活色生香朦胧幻变的“人生本身的形式”。

《汪曾祺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而“意象流”的小说形式,或许恰与汪曾祺的“人生形式”若合符节,背后是汪曾祺对生命对万物对生活的热爱与耽溺,恰如唐湜所总结的那样:“汪曾祺的大爱则收缩于物象之内,一举手一投足之间,不任意泛滥,如溪流潺潺,不事挥霍。”[9] 而“意象流”的诗学特质或许正是如潺潺的溪流,虽然不若大江大河浩浩汤汤,却恰如个体生命以及万物、生活本身的流动的形式。
唐湜与汪曾祺都倾向于把意象的流动性比拟为生活形式本身,因此诗学形式构成了人生形式在小说中的具现。还是唐湜在《虔诚的纳蕤思》一文中说得好:

汪曾祺是虔诚的,他频频向生活之流映照,沉缅而唯恐自觉迷失,虚我而让我为意象充实,无我而我无所不在,终于意识风流云散地漂游,而意象无所不在地环生,完成了艺术或诗的真,映照了真纯的清澈见底的人生。
注释
[1] 唐湜:《虔诚的纳蕤思——谈汪曾祺的小说》,《新意度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 年。以下所引用的《虔诚的纳蕤思》一文中的论述均来自于此书,不再一一注明。
[2] 唐湜:《〈手掌集〉》,《诗创造》1948 年3 月第9 辑。
[3] 唐湜:《凝定的意象》,载《大公报》(天津),1948 年10 月24 日。此文被作者收入《新意度集》时改名为《论意象的凝定》。
[4] 唐湜:《〈手掌集〉》,《诗创造》1948 年3 月第9 辑。
[5] 唐湜:《论意象》,《春秋》1948 年11 月第5 卷第6 期。
[6] 笔者利用“知网”搜索,所见运用过“意象流”范畴的相关文章有卢燕平《论“三李”诗的意象流》,《唐代文学研究》第10 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王芳在讨论唐湜的诗评以及辛笛的诗歌时也援引了唐湜的“意象流”概念,参见王芳《透视唐湜“九叶”诗评文字的诗学思考》(《诗探索》理论卷,2020 年第3 辑)以及《辛笛“节奏说”之于现代诗体及语言探索的意义》(《诗探索》理论卷,2021 年第3 辑)。
[7] 汪曾祺:《复仇》,《文艺复兴》1946 年5 月第4 期。
[8] 晚年的汪曾祺对建构本土化理论更加自觉。如他的《两栖杂述》:“正如中国画讲‘血脉流通’、‘气韵生动’。我以为‘文气’是比‘结构’更为内在,更精微的概念,和内容、思想更有有机联系。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先进的概念,比许多西方现代美学的概念还要现代的概念。文气是思想的直接的形式。我希望评论家能把‘文气论’引进小说批评中来,并且用它来评论外国小说。”(《汪曾祺全集》第3 卷,第198 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再如《〈晚饭花集〉自序》:“我是更有意识地吸收民族传统的,在叙述方法上有时简直有点像旧小说,但是有时忽然来一点现代派的手法,意象、比喻,都是从外国移来的。……但是,我追求的是和谐。我希望溶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能把它们揉在一起。奇和洋为了‘醒脾’,但不能瞧着扎眼,‘硌生’。”(《汪曾祺全集》,第3 卷,第326 页)
[9] 秦雅萌在《“物象之内”:论40 年代汪曾祺的故乡书写》一文中也试图借助唐湜提出的概念,从“物象”的角度出发,解读汪曾祺作于40 年代的故乡题材小说,指出“物象”也承载着小说叙事的功能,构成了汪曾祺观察乡土社会的一种别样的视角,随之而产生的则是小说风格与审美意趣的独特性,该文也是从诗学生成的角度讨论汪曾祺的“物象”范畴。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 年第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