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自古推崇隐逸之士,比如许由宁可放弃即位天子的机会也要选择自由的生活。到了东汉初年,刘秀大力鼓励隐逸之风来抵销王莽时代文人之无耻即“上书颂莽德者四十万余”之状,更以放归老同学严光为留名青史的典故,成语“狂奴故态”即源于此典。所以,有否隐士也成了时代道德精神高低的标志。不过,唐朝也出过卢臧用装隐士以谋官的笑话儿,以致历史上留下了“终南捷径”的成语。

欧阳修老先生遍检五代旧事,找到五位合乎他的道德标准的言行一致者,列入《一行传》,也就是说欧阳老先生首推隐士为言行一致者,其他义行者则列于其后。
在《一行传》的小序中,老先生慷慨陈词,他说:
“自古材贤有韫于中而不见于外者,穷居陋巷,委身草莽,虽颜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变多故,而君子之道消之时乎!吾又谓必有负材能,修节义,而沉沦于下,泯没而无闻者。求之传记,而乱世崩离,文字残缺,不可复得,然仅得者四五人而已。”
实际上,老先生已近苛刻,既不闻有风尘女子义助宋齐丘之事,又不闻江为之为友而殒命时凛然作诗之行?

老先生在发完以上概论式的感慨后,给出了所选人物的简要理由(今译):
“生活在深山丛林之中,与麋鹿相伴,虽然不足以成其为中庸之道,但这种状况不比食人俸禄、低头受辱更好吗?不食别人的俸禄,无愧于自己的心意,不是本身自由而行的好事吗?
对于这种自由而行的人士,我考证到两个人,分别是郑遨和张荐明。面对权势,不违个人心意,或从仕或出走,但不违背义理大节,我考证到一人,叫石昂。对君主有利而自己的忠心不被赏识而获了罪,并不申冤诉苦,至死也不抗争,这样的人是古代义士的现世版本。我考证到这样的人,有一位,叫程福赟。五代时,天下混乱,君主不像君主,臣下不像臣下,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至于说到兄弟、夫妻之间的伦理也没有不崩溃的,天理几乎被灭绝。在当时,能以孝道守义之行节著名于一乡,并且行节为天下人所赏识,也有其人,但是大多数人的事迹已失传,故而没有相应记录。可也有名字没有湮灭或者被地方史志记录的人,对此,我也不敢擅自删去。这样的孝义之人,我发现了一个,叫李自伦。”
关于李自伦,也可以视为隐士之一,只是没有如郑遨那样遁入山中而已。
更为有趣的是,这五位杰出人物全在后唐与石晋时期即胡人统治时期,而没在梁特别是被欧阳老先生大加推赞的后周时期,岂不怪也!而其中郑遨与张荐明事迹跨唐晋两朝且主要在晋,也成了一个不小的悖论:此五人皆与石晋一朝有关,且后来人行节全在石晋,莫非欧阳老先生未置一词评论的晋太祖石敬瑭时代与其极力贬斥的出帝石重贵时代,还算不错的道德黄金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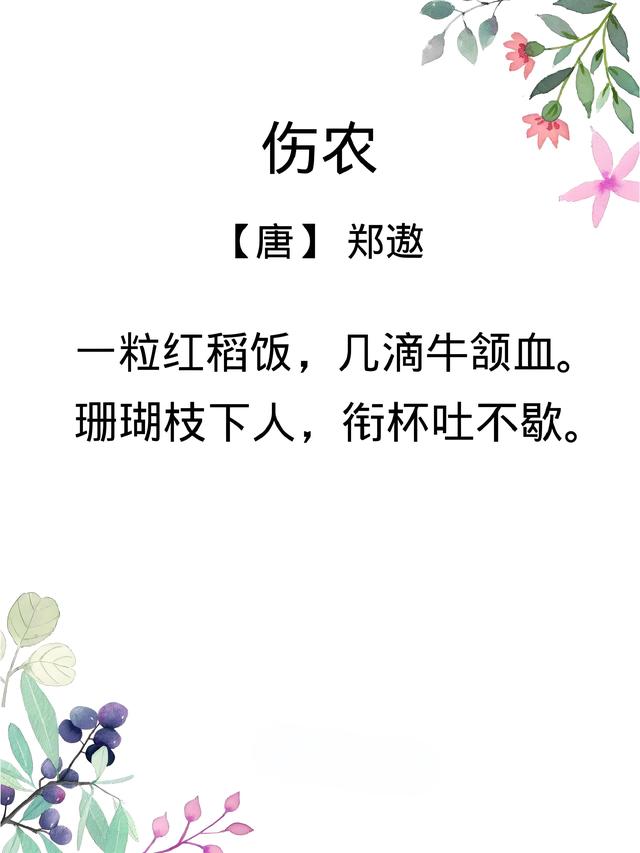
大隐士郑遨字云叟,是滑州白马县人,生于唐懿宗咸通七年(866),经历过唐末后梁、后唐以及后晋初年。唐昭宗时举进士不第,又天下已乱,就到离家不远的少室山作了道士。
当初他离家时,曾劝说老婆孩子与之同行,老婆孩子留恋世俗,不肯随从。后来,他老婆屡次写信劝他回家,他坚持己意,将书信投之火中,看也不看。
既然不能相从隐逸,那就说明志趣迥异,夫妻之情早成陈年谷糠,等到他听到老婆孩子的死讯(估计是为乱军所杀或因灾而死),“一恸而止”即哭了一声就了事了。
云叟先生性格淡爽,从与唐末后梁初权臣李振的交往中可看得出:作为好朋友,李振想拉困苦中的郑遨一把,给他个混俸禄的官位,但郑遨一口回绝,反弄得李振不好意思了;后来,李振犯了罪,遭贬黜,郑遨徒步而行千里,去看望旧友。“由是闻者亦高其行”。

云叟先生由原来的关心政治(如参加科举)彻底转型为关心生命,甚至到了听信传闻的程度。传说华山有一种叫五粒松的松树,其松脂渗入地皮以下,经过千年的时间“化为药,能去三尸”,所以他就从老家附近的少室山移居到华阴,以便求药。
是否求到了千年松脂,无从考证,但这“三尸”还是很吓人的东西,据南朝丹阳人陶弘景(456-536)在《真灵位业图》中说:上尸寄居脑后玉枕穴,为蓝绿色蠕虫,长约二寸,可致人头风病;中尸居夹脊穴一带,一旦中尸离穴,人就驼背;下尸在尾闾穴,定人生死,状如胎儿;人之死,上中二尸随之消散;唯有下尸形迹不灭,并且逐渐聚拢死者的魂魄,变成与生前没分别的幽魂。
陶弘景虽然早在云叟先生时代已经仙逝四百年,但可以肯定地说,对他们那些入道求长生的人有着无可替代的影响。
在寻求长生的欲望中,云叟先生逍遥地活着,他与另两位道士结成一个小团体,其中一个叫李道殷的道士不但善钓鱼而且还能点石成金。云叟先生当场让李道士试验过点石成金术,果然不假,但是他没兴趣积攒大量的黄金,还是坚持种地以维持三人的口粮。另一位叫罗隐之的道士,则不点金亦不种田,采了药,下山去卖。

也许只有罗道士从山间到人间的往来,使他们能够获取俗世的信息,并且也向俗世传播了他们凡人不可及的美妙生活方式。否则,怎么会有“世目以为三高士”的社会效果呢?
当然,云叟先生的诗才也由于隐居生活大有提高,时时喝酒又时时作诗。诗稿落到俗世,人们就多加抄写,裱成条幅,互相赠送,以为传世之宝。其实,他的诗真正水平并不高,只不过是由于他的生活方式的烘托而被追捧而已。而在那个时代留下不同凡响诗篇的“世外高人”是两个僧人,一个叫贯休,一个叫齐己。
无论后唐庄宗李存勖还是后晋高祖石敬瑭,都听世俗煽呼,甚信其才,或召授左拾遗或召授谏议大夫,他都不接受。石敬瑭赐其号为“逍遥先生”,以了结权力对隐士的渴慕情结。还好,逍遥先生在晋天福四年(939)辞世,活了七十四岁,没看到晋出帝石重贵的灭亡悲剧。

不惟郑遨得“逍遥先生”之号,当时与他齐名的还有一位被石敬瑭赐为“通玄先生”的道士。他叫张荐明,只知道是燕地人,生卒均不详。少年时代即以儒家学者的身份在河朔(今山西境内)游学,后来几乎也同郑遨一样,见以儒术改变社会地位无望,就改为学道术。凭着儒学的功底,弄通老子、庄周的学问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成为一方名人自然也不在话下。
以武力夺取皇权且汉化程度较深的石敬瑭愿意请大师指教,就派人把张荐明接入宫中,问以“道家可以治国乎”的政治哲学或曰国家战略问题。
张荐明答道:“这道嘛,与万物妙通,无法尽用言语表达。如果一个人能悟得它的精髓,躺在床上、坐在席上就可以把天地之事治理得秩序井然。”
石敬瑭听此玄理,大为感悟,赶紧安排大师到内殿去,给自己讲《道德经》,并正式拜师。
如果不是由儒改道,张荐明作为一个落魄文人断然不会成为帝师的。至于稍后皇帝给老师的“通玄先生”的赐号,也成了皇权与知识进行交换的一个经典案例。

大约与以上二位道教大师同时代而又坚守儒学的大师级人物,叫石昂,生卒年如通玄先生一样不详。只知道是青州临淄人,还做过县令。据欧史所记载的他初期资料看,他不是科举出身,更像是个自学成才的富家子弟。缘于家财丰厚,他才可以不事劳作,又可招纳四方之士前来交流学问,且充分利用家族藏书数千卷的有利条件。
石儒士是位谦恭有礼的人,对于那些无处去就在他这里混饭吃好几年的学者,他不曾流露出一点厌倦的神情。这样一位人格完美的人却因不得已当了县令,受辱 而回。
起初他是决心不走仕途的,只是节度使符习慕其名,强请其为临淄县令,他才不得已而仕。然而,作为文人,他几乎不了解军阀们的专横程度。时当符习入朝办事,由监军杨彦朗行留后职权,石昂到节度府上觐见。彦朗是该监军的名,其字为“石”,即名彦朗字石,管通报的小吏都像讳避皇帝的名字那样,不敢用“石”字,于是高叫:“临淄县令右昂入见留后大人。”

石昂不会责备门吏,全然没有待士的礼貌,怒气冲冲地走到节度使办公室,怒目直视杨彦朗,厉声斥责:“监军大人,你凭什么假公权行私弊?我姓石不姓右!”狂妄的杨彦朗本来理亏,再遭此一问,顿时难堪万分。彦朗大怒,拂衣而去。公事是谈不成了。
你不办公,我还不当这县令了呢!回到县衙,石昂将公务交割一清,回到家里。万幸,万幸,军阀杨彦朗没带兵上门找他麻烦,大概是他名气太大又为节度使符习敬重的缘故吧。回到家,石昂怒气未消,对儿子说:“吾本不欲仕乱世,果为刑人所辱,子孙其以我为戒!”
作为一个儒学的坚定守望者,他的意识形态高度纯洁。他父亲,一位生前也是纯粹儒士的人,老人家死了,有人建议请佛家来超度亡灵,他一口拒绝,并声称他不可能以“佛事污先人”。随后,石昂立于棺材前,高声诵读儒家经典《尚书》。
朗读完,他对众人说:“这才是我父亲乐意听闻的!”养士人、辞县令、治父丧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后唐一朝,等迎来石敬瑭时代,又有众多高官推荐石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姓氏与晋朝皇帝一样,又为当世名流,可为皇室增光。

其实,石敬瑭的“石”来自突厥的月支氏,是标准的少数民族,而石昂的“石”应是汉人如汉代名相石奋的“石”。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刚好晋高祖愿意把自己的血统挂靠在汉代名相石奋的名下,有了当世名流石昂不就更贴切了!
晋高祖以家人的礼节在便殿接见同宗石昂,以营造宗亲的亲密气氛。谈话完后,任命石昂为宗正丞,即在负责皇族事务的宗正卿石光赞手下具体办事。不久,又迁为宗正少卿,算是官升一级,成了石光赞的副手。
晋出帝石重贵即位后,石晋政治大坏,石昂以特殊身份屡次上书劝谏,石重贵不理他这套,每次都当耳旁风。石昂不能再像斥责杨彦朗那样找石重贵发脾气了,无可奈何,“乃称疾东归”。
你不听,我还不伺候你了呢!
在石昂之后,为败坏不堪的石晋政治再添光彩的是程福赟。作为亡国前的最后忠臣,他的贤者不辩的行为大大地打动后来的历史学家欧阳修,所以给他在裁减十分苛刻的《新五代史》上留了一席之地。

后晋出帝的政治已然混乱不堪,乃至于在最后关头众叛亲离,后晋出帝率军队北上抵抗契丹时,有奉国军士趁夜间放火烧军营,要发动军事政变。程福赟将军职任奉国右厢都指挥使,治下生乱,自然要奋力扑火,可是火灭了,他也受了伤,令人尴尬的是没能查到放火之人。既然政变未遂,皇帝又在军中,程福赟将军就压下此事,不再上报。这个隐瞒行为让早有代他之心的部下李殷抓住了机会,奏报说:福赟欲谋乱,不然何以发生变乱而不报。
后晋出帝急令逮捕程将军问罪,明白人都知道这是冤案,但程将军“终不自辩,见杀”。
天下不为自己喊冤的人太少了,像朱梁时代的朱友恭、氏叔琮那样的重臣,还临刑前高叫呢,程将军竟然一不自辩,二不喊冤,真乃天下奇人。
皇帝杀了程将军似乎也得到虚荣上的满足,“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嘛!可是,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发问:为什么程将军竟没有任何一个同案犯呢?

欧史还记载了一位叫李自伦的好人,他既不是文化精英也不是忠心将军,而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
这位深州农民没有任何惊人的业绩,只是因为六世同居而赢得了崇高的国家荣誉。晋高祖于天福四年(939)九月,敕令给李自伦家族建造专门住宅区,其中一项就是在住宅区门口建了两个高台作为标志性建筑:用白色的灰膏给高台勾抹砖缝,而台上的四个角都漆成红色的,以期达到“使不孝不义者见之,可悛心而易行焉”。
这个举措在战事稀少、政治相对清明的石晋初期是件大事。天福四年,石晋政治的外部收益也有得有失,其得自然是表彰李自伦的六世同堂,战乱年代有六世同堂之奇迹也算是本朝的人瑞了,其失者乃是逍遥先生郑遨的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