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时期,司马光、文彦博等旧党首脑相继退居洛中,汴京朝堂反对拓边的呼声大减。在拓边派武将的推动下,神宗组织了两次对夏战争,但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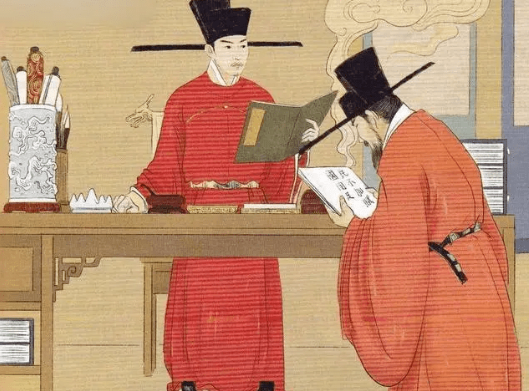
元丰四年(1081)四月,种谔上奏西夏国内发生内乱,希望朝廷“大兴王师,以问其罪”。
他的建议与早有吞并西夏之心的神宗一拍即合。随后,神宗御笔亲书伐夏之命,调动五路军队直指西夏腹地灵州、兴州,准备一举扫灭西夏。
五路伐夏——元丰时期的第一次宋夏战争在东部,河东路、鄜延路虽然一度占领银州、夏州、宥州,终因粮草不济而被迫撤军。在西部,李宪指挥的熙河路军队与吐蕃军虽然攻占兰州,但始终没有到达灵州主战场。

唯有泾原、环庆路的军队成功会师灵州城下,但由于久攻不下,再加上粮道不通、夏军掘黄河水淹宋军,这两路也被迫撤回宋境,是为“五路伐夏”之战。五路伐夏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武将与宦官之间的纷争。元丰四年(1081)四月,种谔、沈括、俞充等拓边派主张乘西夏内乱,发兵直捣兴灵。神宗知道后,让王中正去鄜延、环庆路经制体量边事。
六月,神宗决心要讨伐西夏后,对陕西路边帅进行了一番人事调动。以种谔为鄜延路经略安抚副使,“本路及麟府事悉听谔节制”;以王中正为同签书泾原路经略总管司公事,主管泾原路兵马;高遵裕主持环庆路进兵事宜。

八月,西北诸路边帅人事却出现变故,种谔不仅失去了节制河东兵马,而且自己统率的鄜延军队还要受王中正节制。官方说法是种谔擅自率领军队出界招纳蕃部,“遂命谔听王中正节制”。
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此时王中正刚刚返回汴京,他是否可能在神宗面前诋毁种谔等人,希望自己身领其事?答案是必然的。王中正此人有揽权的欲望。
神宗本意是让王中正出兵之前节制鄜延、环庆与泾原路,一起商讨出兵日期与行军路线,但是王中正出兵之后仍然想节制其他两路,引起高遵裕等人不满,故而神宗要他明确责任,不得侵权。

九月二十三日,陕西、河东军队正式出兵。二十八日,种谔攻破米脂寨并大败西夏援军,凭借此军功,他得以率领鄜延军队单独行动,不再受王中正节制。
王中正原本打算在夏州与鄜延军队汇合后,征用鄜延的军粮为己用,但是现在他不得不面临军队粮食短缺的问题。
随后,种谔、王中正两军在横山下的神堆驿汇合。神宗期望种谔、王中正能够“进讨事和同商量,择利而往”,但现实是种谔并没同王中正见面,也没有发鄜延的军粮救济河东军队,而是引兵往夏州而去。

同时,鄜延帅种谔、环庆帅高遵裕与熙河帅李宪的关系也是不睦。种谔与李宪的矛盾大概要追溯到熙宁四年(1071)第二次进取横山时,当时种谔力主筑啰兀城,而李宪却大加反对。
随后,种谔知岷州,与措置熙河的李宪成为上下级,但是他们的关系也不见好转,两人互相不喜对方,短暂共事后就分开了。
究其根本,两人是在伐夏的路线上出现了分歧。李宪主要在熙河路、泾原路用事,他主张从泾原路筑堡,直抵鸣沙城,进而扫平西夏;而种谔的势力主要在鄜延路,他认为应该先占据横山,居高临下威胁兴灵。

而高遵裕与李宪的嫌隙启于熙河拓边之时。熙宁六年(1073),宋军夺取熙州之后,围绕是否出兵河州,拓边派发生了争论。
李宪主张应该即刻出兵,而高遵裕却不同意熙州防务未固,兵粮未足时便进攻河州。李宪因高遵裕与他意见相左,便留下高遵裕守熙州,他与王韶率军取河州。
此外,在环庆、泾原路兵困灵州之时,神宗让熙河路苗授率军救援,军中宦官乐士宣向神宗报告苗授消极对待,苗授反奏乐士宣“倚诏作威,望风旨以固宠,不能以实上闻。”希望自己被调往别路。

其次是武将与漕臣之间的纷争。一场军事行动,军队与后勤补给是最重要的两端。故而,军队统帅与后勤统帅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一场战争的胜负。
而元丰四年(1081)的宋夏之战,各路都或多或少的面临军队后勤不继,统帅与漕帅关系不佳的境地。
从鄜延路来看,作战统帅种谔与转运使李稷在进兵之初就发生龃龉。李稷作为后勤指挥官,本应该身处后勤军队,就近照管军粮,却置帐在种谔的作战部队中,严重削弱种谔在军中的地位,受到种谔的恐吓与弹劾。
其后,种谔从夏州向灵州进军时,后勤补给出现问题,种谔想杀李稷以自解,幸赖吕大钧的救护,再加上李稷自请“身督漕运”,才免于一死。

五路出师失败后,种谔上奏朝廷,认为是李稷没有做好后勤保障,从而导致灭夏的大功不就,李稷也因此而被贬官。从环庆路来看,军队统帅高遵裕与转运副使李察、转运判官范纯粹也是矛盾重重。
高遵裕强调转运司不仅后勤运输的方式有问题,而且这些官员贪生怕死,没有照管好军队的粮草。
可见,环庆路的军队统帅和后勤指挥官之间关系的不协。此外,以宦官李宪、王中正为统帅的熙河路、河东路,军队统帅与漕臣之间的矛盾比上述两路更大,这直接导致了两路军队因军粮不继而退出战场,而河东统帅王中正、两路漕臣也相继被贬谪。

最后是武将与武将之间的内斗。五路伐夏之战,除了宦官统率的熙河路、河东路,其他三路的统帅均为武将。分别为鄜延帅种谔、环庆帅高遵裕和泾原帅刘昌祚。
他们都是久经战阵的骁将,原本应该懂得分路进讨下相互协作的重要性,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又使这种协作愿景成为空中楼阁。
进兵之前,神宗让高遵裕节制刘昌祚,因为神宗对刘昌祚不信任,认为他“奏请多不中理,虑难当一道帅领”,并让知环州张守约去替代他。
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神宗在给高遵裕的诏书中仍然强调“昌祚所言迂阔,必若不堪其任者”,这也间接导致高遵裕对刘昌祚的轻视与颐指气使。
考虑到泾原路“川原宽阔,易得水草”,是西夏防守的重点区域,所以泾原路一开始就是作为牵制西夏军力的偏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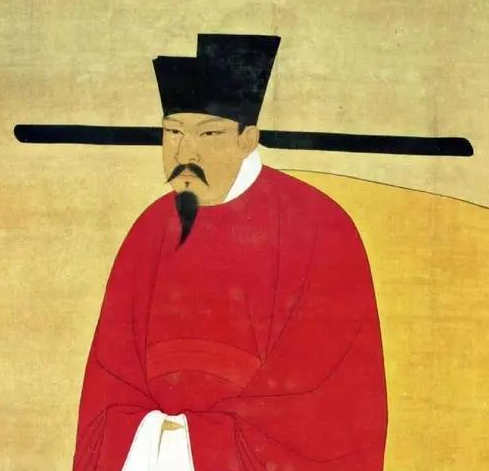
但恰恰就是这一支偏师,居然是五路之中最快抵达灵州城下的。
高遵裕怕刘昌祚先行攻打灵州会夺去自己的功劳,便命令刘昌祚按兵不动,等待自己的到来。刘昌祚也怕朝廷治他两道争功之罪,于是就按兵不动。
高遵裕到达灵州城之后,又责怪刘昌祚面见他太晚,于是“坐帐外移时不见”,对刘昌祚来了一个下马威。随后,两人又在用兵方略上产生分歧。
刘昌祚主张先攻击灵州城外东关镇的驻军,以切断灵州外援,而高遵裕属意直接攻打灵州城。两人争论不休,高遵裕欲解除刘昌祚的兵权,交付给姚麟,姚麟不敢接收。
此后,高遵裕让刘昌祚率泾原军队巡逻营寨,而派自己统率的环庆军攻打灵州,希望本路独揽大功,引起泾原军与环庆军的对立,两路也就“各自为计”,无法并力协同作战。

五路伐夏失败后,刘昌祚与高遵裕又指责对方用兵乖方。此外,种谔与高遵裕也是存在矛盾。
高遵裕被贬后,在上书中揭露治平四年(1067)绥州之战,是种谔自己“暴举,遂误事机”,而实际上种谔是奉神宗旨意出兵收复绥州,而传旨之人正是高遵裕。
相应地,高遵裕、刘昌祚的军队在灵州被西夏掘黄河水淹之时,种谔也“拥兵不救”。
